只需一字不动搬上舞台,《萨勒姆的女巫》即是永恒
去年,英国国家剧院重排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萨勒姆的女巫》。同年9月,该戏以剧院现场(NTLive)的形式登陆英国院线,今年由“新现场”引入国内。中国观众对这部剧作应该并不陌生,早在2014年底,英国老维克剧院的版本就曾在中国放映。从不到十年反复重排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萨勒姆的女巫》早已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作品,蕴含着常看常新的时代价值。
自身失去制动的可能
《萨勒姆的女巫》于1953年在美国首演,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美国第二次“红色恐怖”时期)最盛行的阶段,大量美国文艺界人士遭到莫名指控和诬陷。而在此之前几年,犹太裔德国流亡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已成为美国当局怀疑的目标之一,并因其早年的旅苏经历和为“大清洗”辩护的言论被认定为“亲苏知识分子”。1947年,福伊希特万格以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萨勒姆女巫案”为基础创作了德语戏剧《欺骗,或波士顿的恶魔》,两年之后该戏登上了德国舞台。正是在福伊希特万格的改编和当时时代背景的共同作用之下,阿瑟·米勒对原事件进行了又一次虚构和改编,创作出了《萨勒姆的女巫》这一脍炙人口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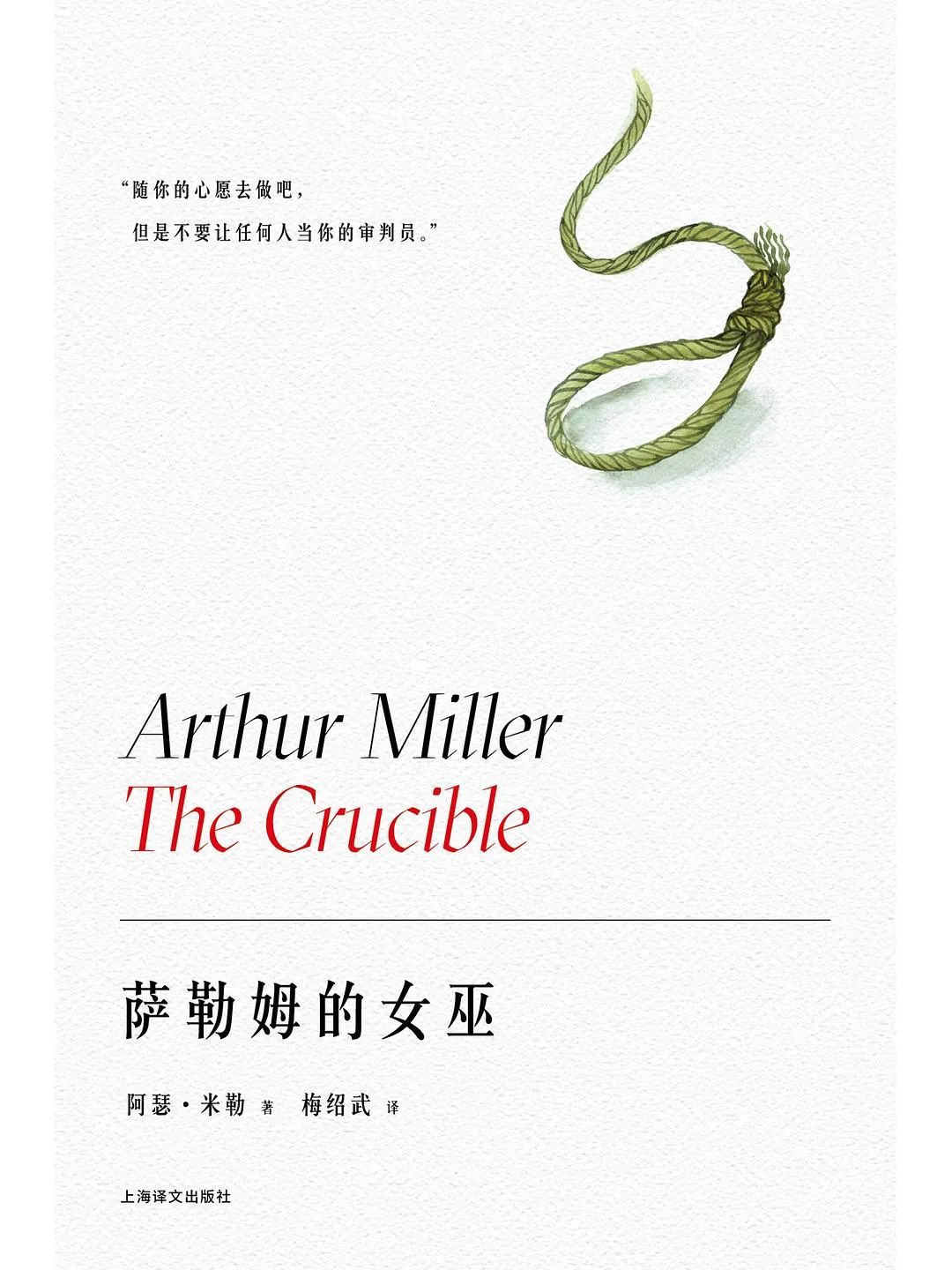
在剧中,阿比盖尔等多名证人指认当地民众为魔鬼的仆从,且在指控过程中权力无限扩大,神父和法官不仅未能制止恶行反而助纣为虐,使得审判走向彻底失控,最终导致当地十数个无辜民众被处绞刑。与福伊希特万格类似,阿瑟·米勒并不直接对抗麦卡锡主义,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讽喻上世纪50年代残酷的政治迫害,从历史事件当中寻找素材进行虚构创作并进行类比。这样的创作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为剧作赋予了一种寓言色彩,使之不再是单纯的现代政治制度批判,更多地展现了人性之恶如何寓于制度之中,并通过不完善的制度被放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荒诞程度。

《萨勒姆的女巫》剧照
全剧甫一开始,阿比盖尔和神父塞缪尔·帕利斯的对话就预示了政治迫害的成因:几乎完全出于个人私利。随着剧作的发展,几个角色都展现出幽深的心理动机:有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情感目标,有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所有这些先是一层层叠加,然后在审判逐渐失控之后一层层剥离。被这些个人私利所带动的宗教裁判的车轮越转越快,巨大的惯性让自身失去了制动的可能。直到结尾,阿瑟·米勒预言了政治迫害一定会抵达的衰落和终结:各地掀起叛乱,主犯畏罪潜逃,留下一个没人收拾得了的烂摊子。在那里,只有正义和尊严成为永恒,其他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化为尘土。
现实中,在该戏上演四五年之后,麦卡锡主义就逐渐在美国社会黯然退场,其主谋约瑟夫·麦卡锡一命呜呼。而有趣的是,阿瑟·米勒也与自己剧中的主角有着相似的命运:《萨勒姆的女巫》首演之后第三年,米勒受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CUA)的质询,并因拒绝指认之前曾与自己共同参加某些会议的人士,被指控犯有“蔑视国会”罪——这与该剧第四幕发生的情况如出一辙,主人公约翰·普罗克特拒绝指认剧中的大善人丽贝卡·讷斯出现在魔鬼撒旦周围。区别只在于普罗克特的确因此丢掉了性命,米勒则没有。可以想见,米勒自己笔下的人物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他本人的道德准则,使之经受住了现实中的道德考验。
与“奥本海默”的巧合
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很多指涉麦卡锡主义的文艺作品,而且直到现在这种反思性的作品仍在不时涌现。比如,西德尼·吕美特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也是从司法角度抨击定罪的随意性,并在片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公正的美国司法体系——依据事实和证据而非证人单方面的口供执行的司法权力呼之欲出。除了像《萨勒姆的女巫》这样70年来复排从未间断过的作品,也有一些新的作品不断产出,比如正在院线上映的《奥本海默》就与美国这一“红色恐怖”的背景密切相关。《奥本海默》和《萨勒姆的女巫》也确实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早在1964年,“奥本海默案”就已经像“萨勒姆女巫案”一样,被西德文献剧代表剧作家海纳·基普哈特改编成了《关于奥本海默案》并搬上了德国舞台,而该作正是根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公布的逐字稿卷宗改编的。

电影《奥本海默》
从冷战背景看,二者“内销转出口”的路径也许并非全然巧合;情节上,两部作品相似之处更多。它们都是关于“猎巫”这个举动本身,而且两个主角同样都在生活中与他人积累了矛盾,埋下了足以让人公报私仇的种子。最重要的是,二人都有道德问题,尽管二者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对诺兰的奥本海默来说,婚外情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谅解的、不得已产生的“瑕疵”,其程度完全无碍于奥本海默伟大的科学成果,也是一条绝不会影响观众对其人格判断的支线;而普罗克特的婚外情则是整个剧目的关键所在,不仅纽结了一组最重要的人物关系,也牢牢地与当时的宗教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偷情”意味着对第七诫“不可奸淫”的违逆,在信仰的天平上加增了一个重量巨大的负面砝码。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普罗克特在主动曝露自身道德缺陷时更有抉择的意味,对邪恶迫害的抗辩也更有分量。普罗克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鲜活的戏剧人物,应该说是内外两个方向的冲突共同造就的:内部看,他关于婚姻的负罪感和他无法出卖他人的底线原则之间有着巨大矛盾;外部看,他的道德底线并不是一直那么鲜明的,甚至是本不存在的,而是在第四幕中被法官利刃一样的话语一刀刀剥出来的。这种残酷性让他的“就义”更有了一种人情味,让普罗克特成为了一个被历史造就的、不那么情愿的戏剧英雄。
寓言比传记更拟真
与此同时,阿瑟·米勒并不满足于给出一个复杂人物,而是给出了一系列复杂人物——譬如人生中第一次说谎、拒绝劝说丈夫苟且偷生的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对裁判制度极其不满但又无能为力的神父约翰·黑尔——并将这些角色安放在一个所谓的“正面人物”谱系之中。如果说丽贝卡·讷斯是绝对的、坚定不移的善和神圣,普罗克特则代表着权衡的、摇摆的善和公义,另一位受害的村民吉尔斯·科里完全出于保护自身或后嗣利益的目的而缄口不言。同样地,米勒也给出了一个颇具纵深感的“反面人物”谱系,甚至为观众铺平了一条通往萨勒姆年轻女性心灵的道路:她们对谎言的极端渴望,恰恰源自于整个社群和权力体系对她们长时间的漠视甚至压迫。这种“报复”无疑可恨,但也令人怜悯。
如此这般,米勒为整个故事赋予了非常多的层次,构建出巨大的探讨空间,显然也比理应更加接近现实、素材更加丰富的“传记电影”作品还要拟真。
客观地说,此次英国国家剧院的版本在录制水平较老维克版有了很大提高,几个经典的机位设置能够很好捕捉舞台上发生的种种情况,剪辑手法更加老练,尤其是在几个冲突激烈的时刻,每个演员的面部和调度都得到了更加完整的呈现。舞台美术设计简洁、现代而有整体性,白色梯形天顶覆盖在舞台上方,营造出一种棱角分明的、强硬的压抑氛围;开头和幕间的雨墙则把观众瞬间带入到凄冷的萨勒姆小镇上。这一版本的声音设计也颇具匠心:多声部的吟咏一方面营造出宗教神圣感,另一方面也予人杀机四伏的悬念。这些歌声从不结束,而是融入到起伏的声音场景之中,仿佛指控从未停止,悲剧也从未中断。
当然,对《萨勒姆的女巫》这样一出戏,怎么排、谁来演、在何地,似乎都是极次要的问题。只需一个字不动地把阿瑟·米勒的文本搬到舞台上,“暂时”就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