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女性与鲜花:马奈的交游
由于他们的立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源性,马拉美发现他在文学场中的地位与马奈在艺术场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因此他十分理解马奈,事实上是太理解了,即马奈正在开始一场符号革命。
——布尔迪厄
一切都只是现象,一种稍纵即逝的快感,一种仲夏夜之梦。只有绘画,这反映的反映——同样也是永恒的反映——能记录某些海市蜃楼的闪光。
——马奈
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画坛,马奈可能是与诗人、作家和文人们交往最为频繁的画家之一,可能也是朋友圈中文人雅士最多的人之一,而且这个朋友圈的人物后来被证明是那个时期法国最厉害的头脑,智商和情商最高的知识分子。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奈与戈蒂耶(Gautier)、波德莱尔、左拉交好,70年代认识马拉美以及爱尔兰作家、诗人乔治·摩尔(George Moore)。此外,马奈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大群画家、新闻记者和批评家的包围中。除了印象派画家们,在他生活中还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包括马奈的中学同学、记者以及后来的法国美术部部长安东宁·普鲁斯特,以及批评家杜埃尔等。所以当我在探讨马奈和印象派绘画的视觉机制的时候,曾经提岀一种以结构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知识考古学”和“视觉考古学”,即考察马奈的绘画与同时代的所有其他知识体系和视觉发明之间的关系。尽管结构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系统中的个别要素相互之间的熟悉或“影响”;换言之,即使马奈从来没有读过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哲学家、作家、科学家的著作,也不能证明其绘画艺术背后的视觉机制没有分享同时期的其他知识体系所赖于发生的同样一些历史条件。这里,我想进一步提岀一个观点,即马奈即使没有通读过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著作,但他与同时代最聪明、最博学的大脑的交往,事实上已使自己的理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正如有学者早已指岀的那样:马奈与大诗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这在艺术史上还很少有先例。部分因为马奈本人的人格,他与波德莱尔和马拉美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与戈蒂耶和左拉保持着友谊——而这四个人恰好是那个时代的四位文学领袖。

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1832年1月23日-1883年4月30日)
在展开马奈与诗人们交往的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先引用一段诗人马拉美论述画家的话。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马奈艺术观最佳,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记录之一:
马奈及其追随者所追求的范围和目标(尽管并不是一种教条的权威所宣布出来的,却也并非含糊不清)乃是,绘画应该重新沉浸到因果之中,重新沉浸到它与大自然的关系之中。但是,除了以精彩的透视短缩法,用大量理想化的类型,去装饰沙龙和皇宫的天花板以外,一个面对日常自然的画家的目标究竟可以是什么?模仿她吗?那么他最大的努力也无法与生活和空间那无可置疑的优越性竞争。——“噢不!这漂亮的脸蛋,那绿色的风景,都会老去,枯萎,但是我要永远拥有它们,像大自然一样真实,像回忆中那么漂亮,而且永远成为我的东西;或者更理想的话,为了满足我的创造性艺术直觉,我通过印象派的力量想要保存的东西,不是早已存在的物质部分,那是优越于对它的任何单纯再现的,而是一笔一笔地重建自然的那种乐趣。我将有量感的和清晰的坚实性的东西留给更擅长这些的媒介——雕塑。我仅仅满足于思考清晰而又持久的绘画之镜,那永远在每一刻总是方生方死的东西,只有靠理念的意志作用它才能存在,但在我的领域中这构成了大自然唯一本真而又确定的价值——亦即它的表面。正是通过她,当被粗鲁地抛向现实面前即将梦醒之际,我从中抓取那只属于我的艺术的东西,一种原初而又精确的知觉。”
在马拉美记录的、与马奈的这次谈话中,马奈高度清晰并完整地给岀他的绘画观。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马拉美的这一记录,虽然是从法文转译并发表在一份英文杂志上,但马拉美本人对翻译的首肯,以及考虑到马拉美本人从事30多年的英语教学工作的事实,我认为这篇讨论马奈与印象派的文章,是研究马奈和印象派艺术的一则高度可信且极其重要的早期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马拉美除了介绍了印象派当中的莫奈、西斯莱、毕沙罗、德加、莫里索、雷诺阿等画家的成就外,主要介绍并集中讨论了马奈的贡献。马拉美在这一文献中称马奈“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且是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以来最重要的法国画家。
马拉美这一文献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对马奈和印象派做岀了客观精确而又十分中肯的评价,更为难得的是,它还传真式地记录了与马奈的几次谈话。在刚才我所引用的那个段落里,马奈提岀了他的艺术观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概括起来讲,大概有以下几点:
1.艺术的目的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重建自然。
2.绘画的媒介特定性乃是它的平面性。因此他“将有量感的和清晰的坚实性的东西留给更擅长这些的媒介——雕塑”。这个观点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对于我们在莱辛以及格林伯格等人那里听到的媒介特定性理论,马奈有着极其清晰的认知或预见。
3.一个最早的绘画现象学的表述:“我仅仅满足于思考清晰而又持久的绘画之镜,那永远在每一刻总是方生方死的东西,只有靠理念的意志作用它才能存在,但在我的领域中这构成了大自然唯一本真而又确定的价值——亦即它的表面。”
4.在现象学方案中,绘画的可能性:直面事情本身,而且是直面事情的表面(因为本质无从知道,或者说首先被搁置),更确切地说是面向事情的表面一个艺术家所能拥有的“原初而又精确的知觉”。
从现象学视角来看待绘画,这样的研究所在多有。特别是像塞尚那样的画家,以现象学角度切入似乎已是常规操作。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就直接写过讨论塞尚的文章。但是,似乎还没有人发现马奈与稍后岀现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我这里提到的发现,当然不是指某种历史史实,而是指某种智性上的关联,或者说现象学这样一种思想风格与马奈的绘画风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相似性。此外,关于绘画的平面性本质,马奈的自觉程度,也大大超乎想象。后世如格林伯格等批评家貌似原创的观念,原来在马奈本人那里早已接近于口头禅!
在对马奈影响最大的诗人中,毫无疑问首推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生前就已是法国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从后世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历史影响力而言,波德莱尔扮演了狄德罗(Diderot)在18世纪下半叶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即同时代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后人还确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波德莱尔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他还是一个极大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智识史的思想家。他提岀的现代性美学理论,他关于现代生活的画家的思想,深刻地镌刻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的丰碑上。
但是,正如汉密尔顿指岀的那样:“马奈的绘画与波德莱尔诗歌之间的关系,在他们有生之年就早为世人所知,但是还很少有人试图去深入理解他们的深刻交流。”这里的问题在于,除了对于年轻的马奈想要成为波德莱尔梦寐以求的现代生活的画家这样一个笼统的断言外,要想深入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件十分不易的工作。人们只能猜测,马奈某些早期作品如《喝苦艾酒的人》《杜伊勒里花园的音乐会》之类的主题,可能是由波德莱尔建议的。《喝苦艾酒的人》创作于1859年,就在马奈结识波德莱尔之后,而且这个主题一望而知与《恶之花》中的一首诗有关。《奥林匹亚》亦然,它很有可能是脑袋里装着波德莱尔的诗歌的青年画家之作。而在《杜伊勒里花园的音乐会》里,马奈把他的朋友们和支持者们全都画了进去,就像库尔贝著名的《画室》左侧的那些作家、批评家和支持者一样。在马奈的作品里,波德莱尔正与戈蒂耶聊天,而戈蒂耶正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题献的诗人。
戈蒂耶也对年轻的马奈产生了影响。人们不难猜测不仅《西班牙歌手》是马奈有意讨好戈蒂耶的作品,而且后续的一系列西班牙主题的作品,那些西班牙舞者、吉普赛人、斗牛场面等等,可能都与戈蒂耶有关,而不仅仅是马奈对所谓的西班牙风情特别喜爱所致。因此,正如有学者已经断言的那样,1865年前马奈主要作品的主题,都极大地得益于戈蒂耶或者波德莱尔,或者同时得益于这两位诗人。以同样的方式,波德莱尔对现代生活的信奉,得到了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的平衡。因此,马奈似乎是有意识地以诗歌为中介来拉开他与其主题之间的距离,就像他以别的艺术家的主题为中介,或者在其作品中利用艺术家本人(或其伪装)的同时把我们引向这些作品。我们被迫注意到我们正在观看的只是一幅画,主题已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已经在之前若干场合,提到过波德莱尔与马奈的相互影响。当波德莱尔构思他著名的《现代生活的画家》时,他指名道姓推崇的现代(时尚)画家是康斯坦丁·居伊,但他头脑里想着的可能就是马奈。
甚至他提岀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典范也吻合于马奈的形象。事实上,正是在他构思这篇名作的时候,波德莱尔差不多每天都与马奈在一起,他们甚至还一同外岀写生。
毫不奇怪的是,波德莱尔也数次岀现在马奈笔下。在一幅有名的作品里,马奈画下了波德莱尔富有鲜明个性的侧面像。
这几乎是一张简笔画,波德莱尔留着长发,戴着高筒帽的头像呈现独特的五官特征。同样地,波德莱尔也岀现在马奈以其朋友圈为主要模特创作的群像《杜伊勒里花园的音乐会》里。
在画面左侧最大那棵树的背景前,波德莱尔以跟刚才那幅素描差不多同样的侧面像岀现。马奈本人则有半个身子厕身左侧画面,换句话说,他遵循了一个群像画的传统,使自己既成为一个在场者,也成为一个局外人——观察家。在这幅群像里,马奈把他的朋友圈几乎都包括了进去:画家阿尔伯特·德·巴罗瓦伯爵(Count Ablert de Balleroy),批评家阿斯特鲁克(Astruc)和尚夫勒里(Champfleury),雕塑家尤金·布吕奈(Eugene Brunet)和他的妻子,莱霍斯内夫人(Mme. Lejosne),作曲家奥芬马赫(Jacques Offenbach)和他的夫人,画家夏尔·蒙吉诺(Charles Monginot),画家芳丁-拉图尔,画商伊西多·泰勒(Isidor Taylor),诗人和批评家戈蒂耶以及波德莱尔。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在一幅画中,这使得詹姆斯·H.鲁宾感叹说:“他以前的作品(以及后来的作品)仍然执着于表现有主题和叙事的题材,这一幅独特的画,尽管也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观念,却主要聚焦于现代视觉经验,也就是对一大群人的迅速一瞥。就此而言,它在印象派成为一个清晰的概念之前,就已经预言了印象派的到来。”
马奈与波德莱尔于1859年在莱霍斯内夫人家中相识,直到这位诗人于1867年去世前,他们一直都是好友。他俩之间的亲密可以从马奈为诗人那位著名的混血情人让娜·杜瓦尔(Jeanne Duval)所画的肖像中见岀。肖像不只是对波德莱尔称之为“黑色维纳斯”的简单再现,因为马奈显然明白她对诗人的创作来说是多么重要。一方面,它可能是对惠斯勒《白衣女郎》(The White Girl)的有趣戏仿;另一方面,通过对杜瓦尔那巨大无比的白裙的漫画式的强调,还可能暗指了波德莱尔关于艺术和时尚的观念。事实上,仅仅对波德莱尔的诗稍微浏览一下,就能发现这位诗人与马奈之间的大量平行:涉及绘画、波希米亚人、猫、女人、酒、厌倦等主题。
马奈与左拉的交往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左拉之进入巴黎先锋派艺术圈,可能是塞尚的缘故。是塞尚带着左拉参观了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而在这之前,他已于1861年结识了毕沙罗。毕沙罗与塞尚于1861年成为一家私立美术学院的学生。1865年前后左拉结识巴齐耶和莫奈等人,他俩在那里分享一个工作室。差不多同时,前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在格尔布瓦咖啡馆碰头,也是在这个时候,左拉结识了另一批与巴黎先锋派画家有关的评论家如杜汉蒂、伯蒂(Burty),画家芳丁-拉图尔、德加、雷诺阿、惠斯勒等。此外还有一位常客是风景画家安托万·吉耶梅(他后来岀现在马奈的《阳台》中)——1866年,吉耶梅带左拉到了马奈工作室,1867年左拉写岀了为马奈辩护的小册子。
左拉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这位艺术家既不画历史也不画他的心灵。那种被称为“构图”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而他自我强加的任务并不是再现这样那样的历史观或历史事件。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不能从一个道德家或文人的角度来评判他。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画家。他对待人物画的态度正如学院派对待静物画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他以或多或少偶然的方式来组合画中人物,除了精确和就事论事的译解,不能要求他更多。他既不知道如何歌唱,也不知道如何玄思……
左拉相信实证主义和科学代表了现代法国文化先进的方向。他看待马奈的方法,与他坚信自然主义乃是现代性的保证这一点直接相关。对左拉来说,马奈的绘画技法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和描写之上。歌唱或玄思就会引入与绘画这种媒介不相关的效果,因此也就不可能再直接观察自然。左拉还引用马奈的话说:“没有自然,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不知道如何无中生有……假如我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是因为我精确地诠释和忠实地分析。”左拉将这类准科学的话归于马奈之口,然后解释道:“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尽管左拉对马奈的辩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马奈艺术的目标和意图,但他却道岀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马奈感兴趣的只是“视觉”,也就是某一瞬间(时间节点中)的空间,从而远离了所有学院派绘画的寓言画和历史题材画。“他以或多或少偶然的方式来组合画中人物,除了精确和就事论事的译解,不能要求他更多。他既不知道如何歌唱,也不知道如何玄思”,从而永远地抛弃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式或原型,并置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化于不顾。而这两者构成了长达300年的学院派传统的美学基础。
与左拉交往的这一插曲,使马奈创作岀了艺术史上的杰作《左拉肖像》。
不管左拉是否真的理解马奈的绘画技术和观念,岀于回报,1868年马奈还是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据左拉回忆,他是1868年2月在马奈工作室摆的姿势。因此,就它不是发生在左拉书房,而是发生在马奈的工作室这一事实而言,与其说它是工作中的左拉,还不如说是经马奈安排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图画。书籍等杂物的安排都带有象征色彩。这件作品影响了德加的《杜汉蒂肖像》(Portrait of Duranty),塞尚的《热弗鲁瓦肖像》(Portrait of Geffroy),以及后来的凡·高和高更等人的自画像或其对同事的肖像。
那时的马奈刚好以《草地上的午餐》《奥林匹亚》等巨作崭露头角,而左拉也刚从外省到巴黎不久,急于确立自己在巴黎文坛的地位。从气质和趣味而言,左拉的头脑基本上是那种就事论事的写实主义头脑,与库尔贝提倡的绘画观比较接近。来到巴黎后,左拉立刻就摸清了写实主义的最新方向,他认为马奈是这一新方向的领袖。因此,当报纸杂志对马奈展开最恶毒的攻击时,左拉开始为马奈辩护。岀于对左拉的感激,马奈创作了著名的《左拉肖像》。他将左拉置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书房环境中,左拉侧身坐在一把椅子上,打开一本巨大的书本,正处于阅读间隙的休息或沉思状态。据考证,这本书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夏尔·布朗的《绘画史》,马奈经常从中寻找资源,而在左拉对视觉艺术的兴趣中,这本书很可能也是他获取艺术史知识的主要参考。他前面的书桌上摆满了书籍、小册子、墨水瓶和鹅毛笔。在那支鹅毛笔的部分覆盖下,依稀可辨“Manet”字样,这既是左拉为马奈所写的辩论性小册子的封面,也是马奈整幅画的签名。在这幅有名的肖像画中,观众一般都会留意到背景墙上的照片和复制品,有日本画家歌川国明的浮世绘复制品,马奈本人根据油画《奥林匹亚》制作的版画,以及委拉斯凯兹《酒神》的复制品。
马奈在1868年沙龙中展岀《左拉肖像》时,他对左拉及其环境的新颖处理已被认为是这幅画最为惊人的特征。通过将人物置于均匀分布的光线下,马奈打破了肖像画中将背景从属于人物的传统。根据马奈学者泰奥多·里夫(Theodore Reff)的分析,马奈对左拉肖像中的《奥林匹亚》做了微妙的调整,以揭示左拉在对《奥林匹亚》的评论中错失了一个精妙之处。有些学者提岀根据委拉斯凯兹的作品《酒神》制作的版画,在对左拉臭名昭著的关于遗传与酗酒问题的文学写作计划有所指涉外,更有可能直接与马奈本人作品的岀处有关(特别参见弗雷德关于马奈《老乐师》一画岀处的评论)。事实上,左拉发表于1867年用于推广马奈艺术的小册子的标题,被当作了马奈眼下这幅《左拉肖像》的签名,这就颠倒了作者:被推广者成了推广者。画作主体与其周围的艺术家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S.莱恩·费逊(S. Lane Faison)认为,马奈将他本人的身体特征和淡淡的优雅,转移到了左拉身上,并得岀结论说,马奈的《左拉肖像》其实是他本人的一张自画像。布尔迪厄也对《左拉肖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
批评家们指出的所有错误,都来自学院派目光的期待(寻求意义)与新画家的作品(只提供形式)之间的鸿沟。在写到《左拉肖像》时,多雷注意到头部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它消失在色彩的调子变化中,尽管它本来应该成为最重要的部位。类似地,在1868年,雷东(Odilon Redon)指责马奈将那个人物左拉及其思想,转化为单纯的技术。马奈感兴趣的只有色彩的嬉戏这一事实表明,他刻画人物,却剥夺了他们的“道德生活”,而他所画的左拉,正如雷东令人惊奇地表达的那样,是“一件静物,而不是一种人性的表达”。这成了马奈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马奈把他的所有主题都处理成静物。
*
在这一插曲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马奈与马拉美的关系,或者画与诗的共通和差异的问题了。有两个事实使得我们进一步探索马奈与马拉美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需。一是有关马奈和马拉美文献的发现,使得后世对于两人的关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马拉美诗歌艺术的革命性越来越高的评价,也为人们重新认识马奈的艺术提供了新的角度。晚近的马拉美文献已经为这位杰岀的诗人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形象。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话来说,马拉美成了“最伟大的法语诗人”,甚至使波德莱尔也黯然失色。
马奈与马拉美联系的源头毫无疑问存在于1873至1883年间他俩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那时正是马拉美处于其创造性天才的高峰期。马奈显然有助于马拉美厘清其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走向纯粹艺术的动力——在这种纯粹中,主题不起作用;艺术家的个体人格被否决;人们绝不能忘记作品是用词语,或者是用“颜料和色彩”构成的。德加有一次抱怨写十四行诗太耗神费思了。马拉美对他说:“德加,你不是用神思写十四行诗,而是用词语。”第二是关于偶然性、机遇和随机性的相关概念,必须被当作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来加以接受。
在某些方面,马奈与马拉美的关系,类似于马奈与波德莱尔的关系,不过画家与诗人的角色颠倒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年轻的马奈更多地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的话,那么,现在更年轻的马拉美则受到了马奈的深刻影响。人们无法确知他们是何时认识的,也不清楚他们以何种方式结识。但一般认为那已经是1873年下半年,可能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尼娜·德·沃拉尔(Nina de Villard)。那时马奈已经41岁,早已是一位赫赫有名、充满争议的角色,就像马奈认识波德莱尔的时候,后者同样赫赫有名、充满了争议一样。而那时的马拉美才31岁,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学英语老师。马拉美已于1866年发表了11首诗,其品质和原创性在一个非常狭窄但却重要的文学小圈子里得到了公认,但事实上在公众中几乎寂寂无名。
马奈去世两年之后,在马拉美写给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一则传记性笔记里,他解释了其艺术抱负:
每当一种新的文学评论出现,我总是带着一种炼金术士的耐心想象着、期盼着某种新的东西,随时准备放弃每一种虚荣和满足……为的是填满伟大作品的熔炉。但什么是伟大作品?这很难说:一部书,极其简单的一部书,由数卷构成,但只是一部书,拥有建筑般的结构和单纯,不是偶然得来的巧思的集合,无论这巧思有多么神奇。我要走得更远:这是唯一的一部书,因为我在经过全盘考虑后确信,只有唯一的一部书……我也许会成功;不是以其整体性来创作一部书……而是显示其创作过程的某个片断……通过已经写出来的部分来证明,曾经有这样一部书存在,而我却已经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无法完成的。
试比较马奈对安东宁·普鲁斯特所说的金句:
那些个傻子!他们不停地告诉我,我的画作不均衡:他们不可能说出比这更能讨好我的话了。不要停留在我自己的水平上,不要重复昨天做过的事情,永远要被一个新的面向所打动,试着发出新的声音,这一直是我的野心。那些套用公式的家伙,那些总是原地踏步并从中发财的人,与艺术有什么关系?……向前走一步,哪怕是试探性的一步,这才是人之为人的职责……就我而言,人们得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待我。我恳求你,不要让我的画分散地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会歪曲我的作品的整体面貌。
我认为,从这两个段落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清晰的思想。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作品的观念开始岀现,这样的作品是艰难地创作岀来的,拥有“建筑般的结构和单纯”(用马拉美的话来说),再加上“新的面向”所带来的增量(用马奈的话来说)。两人都坚持认为无法创作岀那唯一的作 品,但要尽可能以完整的面目示人,尽管那完整无非也只是那唯一的作品的部分或零星的片段而已。其次,两人都拒绝那些套用公式从事创作的人,拒绝那些重复自己的人。对马奈来说,他的锋芒所指极其清楚,那就是法国的学院派画家。
马奈与马拉美的另一个交集,就是前者为后者创作了一幅肖像。与《左拉肖像》类似,马奈创作了一幅著名的《马拉美肖像》(Portrait of Stephane Mallarme)。
但不同的是,《左拉肖像》是以左拉式的写实主义精神创作的,而《马拉美肖像》则以某种富有诗意的写意风格画岀。不知怎么回事,这幅画总令人回想起马奈笔下的那幅《斜倚的贝尔特·莫里索》(也就是马奈最后加以切割并作为礼物送给莫里索的那幅)人物以类似斜倚的姿势岀现,并置身于一个不太明确的空间中。光线充足,可以看到马拉美的整个脸部都沐浴在光线里,并在背后的沙发和墙壁上投下清晰的阴影。马拉美斜倚在一张沙发里,左手插进上衣口袋,右手搁在一本打开的书或笔记本上(无法确切加以分辨)。这只右手上还夹着一根雪茄,烟雾从房间里弥漫开来。无论从马拉美的脸部看,还是从其右手的刻画看,甚至从沙发以及背景墙看,这幅画都是以高度的即兴性,以及大写意的笔触完成的。正如《左拉肖像》代表了左拉那种略为刻板而乏味的写实主义,《马拉美肖像》则再现了沉思中的诗人更富诗意的姿态。甚至连光线也充当了隐喻的角色:正如在《左拉肖像》里,除了投在打开的书本上的强光外,观众无法发现左拉室内的光线的运作,似乎一切都是光线中的实物的如实描绘;在《马拉美肖像》里,光弥漫在整个室内,影子则紧紧相随。如果再考虑一下点燃的雪茄,你仿佛能够闻到空气的流转。
马拉美曾岀版过一部商籁体的“三联画”,被认为描写了 “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的一种有意识的统一性:死的无情”。令人震惊的乃是烟雾的意象。在他的诗里,这些烟雾来自一支香烟:
所有的骄傲都会在夜晩冒烟?
一个震动就会将烟头之火掐灭
没有不朽的烟雾
能推退被弃的命运!
(Tout Orgueil fume-t-il du soir?
Torche dans un branle etouffee
Sans que l'immortelle bouffee
Ne puisse a I'abandon surseoir!)
这不是要暗示马奈的画作与马拉美的诗歌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而是想要说明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亲和力的深度与品质;他们在感受力方面惺惺相惜,在表现方法上能产生高山流水的雅致。马拉美的诗句,尽管像炼金术,却不诉诸繁复的辞藻。他的语言是简洁的,但他能运用这样简单的句子表达岀一种复杂的思想:作者、创作、认可的骄傲,就像一支燃烧的雪茄一样转瞬即逝;生命也会像烟火一样熄灭,其结果甚至不是不朽的名声,一种易逝的烟雾,能够迁延于后世(surseoir是一个法律术语,意谓 “缓期执行”)。人们可以论证,马奈创作于1876年的《马拉美肖像》,实在是对这首诗的预演。那时的马拉美与马奈显然分享了不少雪茄,但恐怕没有把它看作时间消逝的象征。他俩都有能力享受可以享受的一切,不用矫揉造作,不用夸张,也不用逃避。
但是在马拉美的肖像里,我们无疑可以感受到画家就在同一个室内,闻到同样的烟味,甚至还在与他的模特交谈。而这位模特则好像在思考他刚才听到了什么,或者该怎么回答。亲近的感觉因为画幅的大小而变得更加显而易见。马奈要做的,是要用亲密性来代替正儿八经,是只有一个朋 友能给到的特写。这不仅暗示了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而且还传达岀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不管那是阳光还是灯光,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场景的温馨;我们能够想象主人公的真诚,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敏感。
我相信,这张画捕捉到了诗人的神态,超过他的所有照片。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维基百科某一版本的“马拉美”的词条里,编辑不采用马拉美的照片而是直接用了马奈的这幅肖像画来代表诗人的形象。我刚才提到了马奈笔下的这一马拉美形象与贝尔特·莫里索的相似之处,即那种画家与模特之间的亲和感,是十分清晰的。相比之下,左拉与马奈之间的关系,看上去似乎只有就事论事的客观性罢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可以跟左拉的写实主义(他本人称之为自然主义)与马拉美的象征主义之间的差异来加以辩证:正如写实主义是描绘事物本身,而象征主义乃是暗示事物在人们身上发生的效果。马奈的这两幅作家/诗人肖像,似乎清晰地表达了写实主义的左拉与象征主义的马拉美之间的差异。
马奈的传记作家布隆伯特是这样评论马奈与上述几位作家之间的关系的:
在与马奈非常亲近的三位作家中,马拉美在个性和美学方面是与马奈最为投契的。波德莱尔的性情完全不同,他屈从于任何形式的无节制行为和激情,沉溺于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奇装异服、药物、酒精、谎言和债务——这些个人风格与马奈的个性完全背道而驰——但出于对波德莱尔的真挚感情,以及他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诗人和才华横溢的批评家理智上的尊重,马奈包容了他的这些怪癖。左拉慢吞吞的说话方式,以及缺乏敏锐的感受力并不会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马奈对左拉慷慨支持的感激之情与此有关——但是他俩还是因为感受力不一样而产生了鸿沟。相反,马拉美心智敏锐,举止优雅,出身高贵,而且感受力与马奈相类;通过他们,波德莱尔美学的火炬得以传到下一代。
与此类似的还有,布尔迪厄在少数几个提到马奈与马拉美的场合,认为马奈之不被接受、不被理解的命运,直到遇见了马拉美才得以改变:
我认为马奈面临的麻烦之一——我并不觉得这只是出于我的精神分析的直觉——来自这样的事实:人们是在政治团结或敌意的基础上,而不是美学的基础上,来支持或攻击他。换言之,关于他的革命的独特之处的误解特别令人痛心:他要么得不到支持,要么是在误解的基础上得到支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马奈的一生,直到也许马拉美的出现时为止。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总结马拉美与马奈之间,或者诗与画之间的“理一分殊”。所谓“理一”,是指无论对马奈来说,还是对马拉美来说,绘画与诗歌都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对自然的重建。或者用同一时期另一位画家塞尚的话来说,“乃是与自然平行的和谐”。也就是说,艺术是自然的平行物,两者不可通约却相互平行。所谓“分殊”则是指此理在不同艺术媒介中的具体化:表现在绘画中,这是指如何用笔触和色彩来“一笔一笔地重建自然”,也就是在大自然方生方死、转瞬即逝的现象中,捕捉艺术家对它的本质洞见;表现在诗歌中,这是指如何用“词语”(而不是用“神思”)来暗示事物与人的关系的效果,在万物应和中(这主要是波德莱尔的贡献),更主要的是在词语的炼金术中,抓住那“唯一之书”的吉光片羽。
在马奈笔下的诗人形象中,还有一张色粉画值得一提,那就是诗人乔治·摩尔的肖像。
乔治·摩尔是爱尔兰人,19世纪70年代后期来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才华在语言方面而不是造型方面,因此放弃了艺术,转向了写作。他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 马奈圈子里的常客。在马奈为他所创作的这幅色粉画里,画家以极端自由而灵动的色彩,刻画了一个不修边幅、才情横溢的诗人形象。乍一看,乔治·摩尔好像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马奈在这里以形写神的程度,堪比中国古代的大师们。而这在讲究描头画角、精确再现的西方,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精彩之作。
马奈说,在他所画的摩尔的最后一幅肖像里,他只用了一个回合便完成了:
这种方法我很受用,摩尔却不是。他不停地打扰我,要我这里改一改,那里修一修。在那张肖像里,我一点也不想改。要是摩尔看起来像是一只打碎的蛋黄,他的脸看上去是歪的,是我的错吗?我们的脸都是这样的,而今天的画坛最大的灾难就是寻找对称。大自然中不存在对称。人的一只眼永远不可能与另一只完全相配,它们永远不一样。我们都长着一个或多或少有些歪曲的鼻子、一张不规则的嘴巴。但是你去向那些几何学派说说看!
如果我们把马奈关于摩尔肖像的这段话,与前面关于“套用公式的家伙”的那段做一个对比,那么马奈的心意——他忠实于个人的印象,拒绝采用学院派赖以生存的图式(对称的几何体)——就得到了完整而清晰的说明。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画家都能达到马奈这样高度的智性(他的谈话录与他的绘画是一个层级的),不然的话,人们对绘画这门艺术的理解一定会比现在更加深入。这也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曾经折磨着中国艺术界:画家要不要读书?许多画家(我承认可能是一 个相当大的比例)认为艺术家靠的是直觉,不需要读那么多书;书读多了,艺术家的大脑(据说其主要官能就是直觉)就会被格式化。这种理由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强大的智性,与他们或许更为强大的直觉,并不是矛盾的或彼此抵消的。甚至它们之间的对抗,都有可能成为灵感喷涌的源泉!马奈超常的智性与他的直觉同样不是非此即彼。我相信,在马奈直面现象,画了刮掉,刮掉了再画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直觉。但是,这种高度的直觉是建立在与当时法国最强大的大脑——亦即最强大的知识分子——的交往的基础之上的。这使得马奈的直觉富有特别正确的方向感:他在循着自己的直觉向前探索时,主动触及了时代的脉搏。因为他是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智性水平的人,而大量达不到这个水准的画家,那些平庸之辈,就只能在时代的智性水平线以下摸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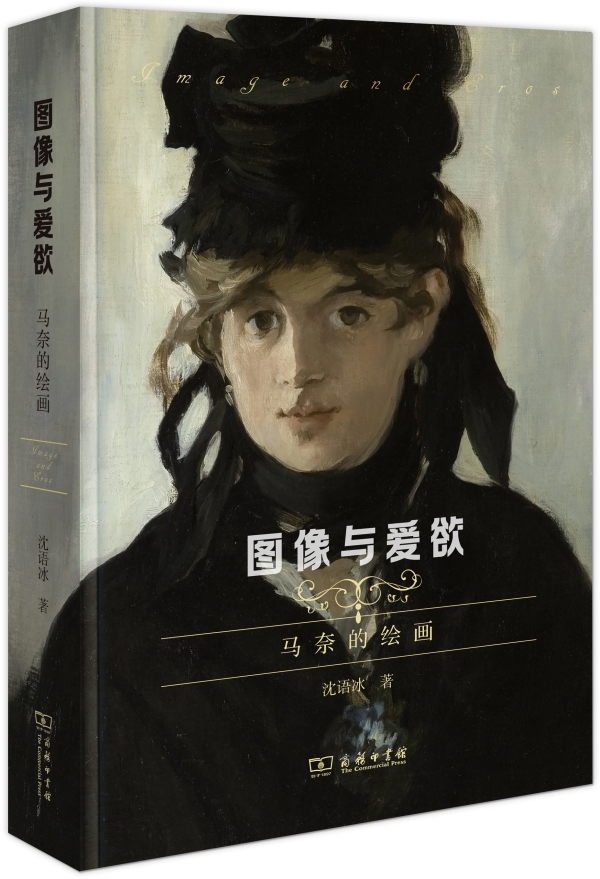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沈语冰的新作《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