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造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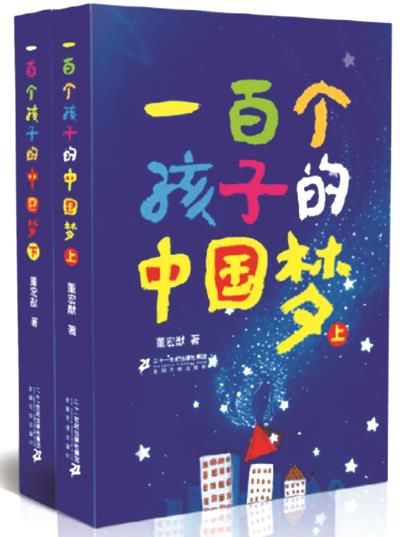
解放公园前面的那条小路,倔强又宁静,和2015年的时候不一样,也和植物园前面的那条路也不一样。在两排巨大的梧桐树荫的庇护下,我们闲散溜达着,一起走在盛夏炎热余威之下,白露刚过。我和雷磊并排在后面慢慢行走,董宏猷和陈伯安手挽手,肩并肩,有说有笑,仍如幼时玩伴一样亲密无间。
连同这段散步时光,我们从早到晚、长达八个小时的访谈,始终给我一种梦幻的美好感觉。我觉得今时今刻不仅仅是一次严肃的作家学术访谈,而是一段奇妙的心灵出窍之旅。其实也不仅仅是一段奇妙的心灵出窍之旅,更像是一次突然滑入古典诗情画意的穿越之旅,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舍不得抽身而出。
让我们把玄思拉回到访谈现场,董老师的讲述富有激情且深情,极富有感染力。他身上有一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品格,有一种吸引人、感染人、凝聚人的独特魅力,当然应该与他所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豪放性格不无关联。
董宏猷老师在访谈过程中总是自嘲“董苕”。在一般人看来,被说作苕是不免蔑视轻视的意味,但是他甘愿匍匐在文学园地做一颗“董苕”。别人不忍其苦,他却乐在其中。这实际上与他对文学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自觉密不可分。他阐述文学观时一再强调,并不羡慕别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写作,而是更喜欢扎根于现实沃土的、具有批判光芒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一位具有古代士大夫风骨的当代作家。
他的作品便是明证。30多岁创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60多岁再写《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也造就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段传奇——董宏猷与张秋林的文坛奇遇、梦与梦的相遇。正如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先生在《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的序言文章《一梦三十年》所说:“‘梦之队’的成员都亲眼见证了董宏猷一头扎进现实生活的深处,扎扎实实地深入西北的窑洞、小学、农家、黄河、高原、沙漠,亲身感受中国大地真实的变化,和孩子们的希冀与疼痛。有时,就在采风途中,灵感迸发、奇思闪现,乃至进入梦游般的忘我状态。当然,也让‘梦之队’的编辑人员体味到一个作家为了创新而呕心沥血的创作艰辛。”为了造梦而捕梦,为了捕梦而呕心沥血,这样深入文学内部,不远万里采风,行走,体验,感受,觉察,文学的尊严在此,文学的力量在彼,壮哉。人们总会感叹,作家创作时已然不是自己,在他的精神世界俨然是一位上帝。为什么是上帝呢?我想,那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体验到了,觉察到了,所以才有了他的想象世界。这种感受、体验、觉察,既是精神的世界的活动,更是对于物质现实世界的创造性投射。古人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信然。
不仅是“双百个梦”是如此,他所有的作品构筑的包罗万象的幻想世界,都不是简单地凭空的想象,而是有着扎实的土地的滋养以及艰苦卓绝的田野式调查的筚路蓝缕,而是浸染着深厚的坚实的现实底色。为了写长篇散文《三峡绝唱》,他在高悬百米之上、跨度数米之间的长江桥墩间跳跃,像一只笨拙的海燕一样掠过波涛,无惧艰辛,甚至把生命置之度外。为了写作《十四岁的森林》,他在神农架那样苦寒的山区大老岭林场,一写就是数月,与世隔绝,与动物为伍,与蚊虫为伍,乐在其中,沉浸其中。
“福克纳曾说过:‘作家唯一需要的环境就是宁静、孤独和快乐。’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一连几年贴在我的窗上。”在《十四岁的森林》的后记《独特、个性与不合时宜》里,董宏猷如是说。但是,作家诉诸文字后,力透纸背的力量也不得不冷静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烈气息就被冷凝了。我只有在现场采访中,听他的声调、语速、节奏,看他的一个眼神、才能感受到作家生命里那种一往而情深的热烈飞扬,才能感受到作家追求某种境界所上下求索的忘我情怀。他说,自己属虎,来到大老岭林场,像虎入丛林一样融为一体,他的胡子也像神农架动物一样也白化了。这是十四岁森林所赐予他永久的印记。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眼眶湿润,我屏住呼吸,聆听一位作家的心灵的呼吸,看见一个作家灵魂出窍的瞬间。
访谈结束后,我背着电脑包,提着一大袋子书,跟着他后面,走到解放公园的门口,目送他们投入到滚滚红尘中。这里的梧桐树,压根儿就没有挺直的主干,出土后便都是歪七扭八的,似有意随时准备摇摆起来,嗨起来。龚自珍先生曾在《病梅馆记》中哀泣:“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所以“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解放公园路的梧桐是美的,也是自由的,不拘一格,傲然独立,有独特个性,有本真力量。我仰望董老师的背影,更能体会到他三十多年前为孩子造梦时那种激愤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