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设计的封面与刊头
林徽因是诗人,是建筑设计师,是中国建筑史学家,是中国古建筑调查考证保护的先驱,是景泰蓝工艺再生的推动者,是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花饰的主要设计者。大家很少知道的是,她还曾设计过话剧舞台和报刊书籍的刊头封面。这里单说刊头封面,都有哪些,长什么样,且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封面
林徽因最早设计的刊头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的封面。远处一轮朝阳正从树林后升起,并将树木投影于波光粼粼的湖面,近处一座巍峨高峻的钟楼在苍松中矗立,楼顶层悬挂着一口刻着夔龙纹的古钟,在悠扬钟声中,一对和平鸽舒展着翅膀向我们飞来。对这个封面所包含的寓意,编者在编后语《感谢》中说:“全部图案可以代表四个要素:一、正义;二、光明;三、平和;四、永久。”
林徽因此图的署名为“尺棰”。在此期增刊中,她还以其笔名发表了篇翻译自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为此,编者特向她表示感谢:“尺棰女士是闺秀笃学家,美术、文学的造诣很深,封面图案和《夜莺与玫瑰》一篇译作,虽不能代表女士的全部的学识,也可以看出女士的天才几分。我们对于女士援助的厚意,不能不特别表示感谢。”
林徽因仅用过这一个笔名(其他所谓笔名都是从名中取出,或用两个字或用一个字,从一定程度上讲,仍可算是一个名)。此名取自《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此时林徽因才19岁,一开始发表作品,用此笔名,应该暗含着她永不停歇、积极探索的心志。
1920年,林徽因跟随前往欧洲考察的父亲林长民来到英国,租居伦敦阿门27号,房东是一单身女建筑师。父亲常常将其一个人留在家中,在她和房东的交往中,她了解到建筑的价值与美,开始立志献身建筑事业。此封面的主体画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钟楼,应该是这种志向的真实体现。
此封面构图上虚下实,从左至右,采用台阶状层层下跌的形式,大有黄金分割率的完美;图中元素动静适宜,朝阳似静实动,加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加上我们想像中的缭绕钟声,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光明和平美好的未来;图中事物描绘繁简恰当,朝阳白鸽树木采用简笔或图案化,钟楼描绘精细,用笔精准,你看那垂脊的小兽和大钟上的花纹,拱门上的砖饰和椽头间的布置,既看出界画的影响,又具有较强写实意味。这强烈表现出了林徽因对建筑的倾心、超人的美术天赋和扎实的绘图基本功。
此图为林徽因未来的一系列设计与古建测绘作了个惊艳的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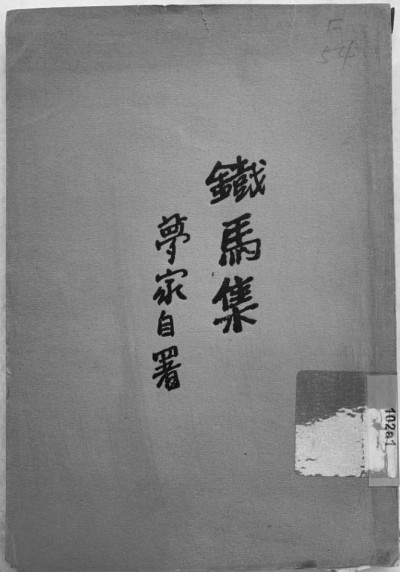
陈梦家的《铁马集》
林徽因设计的第二个封面是陈梦家的《铁马集》。
我们现在通常能看到的此诗集,是1992年上海书店再版的影印本。但它保留了原设计的封面。一看,太简单了。就是一橙黄的底,中间竖排着陈梦家自题的带有很强碑体和隶味的黑色的“铁马集”三个字和左旁稍小的“梦家自署”四个字。初看这个设计,几乎不太相信。我还微信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邹新明老师,问他有没有原版本,如有,请给我封面照片和版权页照片。他一查说有,并给我拍来了图片。对照一下,就是如此简单,只是原色似乎更厚重些深沉些,我们现在的颜色浅了些,稍显轻艳。这就是当初林徽因的设计,并得到了陈梦家认可。读此集的付印后记,开头说:“感谢林徽音女士为我画封面,但因付印时我在芜湖,不曾亲去校择颜色,也许这些颜色调配得不如原意。”(《铁马集》,开明书店1934年1月版“附录”)从这段话看出,林徽因的设计主体就是“色”,这色确实是林徽因特意选择调配,这构图确实是林徽因特意思考谋划。
1930年冬,陈梦家出版了《梦家诗集》,第二年6月再版增补了这半年多新创作的诗;1932年初,他又想把之后创作的诗歌结集以《铁马集》为名出版。此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陈梦家毅然从军抗击日寇侵略。这期间他把诗稿交给方令孺保存。战事结束后,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其助教;暑期,青岛大学发生风潮,与闻一多同时离校。秋季来到北平,由刘廷芳教授介绍入燕京大学学习。1933年初,热河事变爆发,他再度奔赴前线参加抗战。由于热河不战而失,只得悲愤返回。夏天回到上海,9月份,经刘廷芳先生介绍前往安徽芜湖广益中学任教。陈梦家到青岛时,方令孺将诗稿寄回给陈梦家。虽然之后经过三次删补,但随着他来到芜湖,“印事遂复搁置”。在燕京大学时,他得到赵萝蕤的青睐,并开始恋爱,也得到了赵萝蕤父亲赵紫宸先生的赏识与认同。从陈梦家写于芜湖的诗看来,空间的阻隔加深了这种感情与思念。秋深中这些感兴使得陈梦家“重又温习了三年前创作时的热心,因此再想到这册稿集无论如何不能再不给他出来”(同上)。于是增入在芜湖创作的诗仍以原集名交由开明书店于1934年1月出版。
1927年陈梦家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之后得以结识在该校任教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始创作新格律诗,进入了新月社的阵营。陈梦家建议徐志摩在《新月》之外再办纯诗杂志《诗刊》。1931年1月20日,《诗刊》创刊。林徽因于此刊开始发表诗作,由此成为新月社核心成员。如此两人也开始了交往。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时,就选了四首林徽因的诗,并在序中高度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陈梦家请她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诗集设计封面,林徽因能不同意并精心构思? 陈梦家此诗集中有《铁马的歌》,是作者1931年11月18日游览大悲阁时听到风吹阁檐铁铃铛声音产生的情意,“我是古庙/一个小风铃/太阳向我笑,/锈上了金。/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早在《新月诗选》“序”中,陈梦家就表示他“喜欢‘醇正’与‘纯粹’”。林徽因以不作任何装饰的纯正的“色”来应之,岂不正得陈梦家之心,而如此设计,也正好给要变成一颗星的铁马以辽阔的空间。

《学文》月刊封面
林徽因设计的第三个封面是《学文》月刊。
闻一多3月1日给还在河南大学任教的饶孟侃信中说:这个刊名出自“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在“态度上较谦虚”。(《徐志摩·新月社》,王一心、李伶伶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卞之琳则认为,“《学文》起名,使我不无顾虑,因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开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对台戏。”(《窗子内外忆徽因》,刘小沁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经过一番努力,刊物于1934年5月初正式出版。林徽因为此刊设计了封面(图案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徽”字)。关于这个封面,王一心、李伶伶认为“中间是一块汉砖图案,很朴素很典雅”;卞之琳评价说:“我在1934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做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姜德明赞美道:“取材古汉碑图案,她用流丽柔美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的人物鸟兽和花草植物。”(《余时书话》,姜德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无论是汉砖还是汉碑,但都是汉刻。刊期旁的竖状波浪形的纹饰,和下面两边菱形二方连续纹饰,都是汉砖或汉碑四边的常见纹饰;下边的图案,乍一看整饬,但细瞧则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左边,用三分之一空间画了两座笔直甚至有点伶仃的灯架,顶端又画了两株各自左右纷披的花树;另三分之二部分的上端,是一个半的菱形二方连续,但内里又有不同,采用了菱形的四方连续;右边的上半端用一半空间画了一个同样的菱形,但在它的左上角,又画了一个小菱形,既同左边的形成呼应,又再度赋予一种变化;左边另三分之二空间的下端,用其一个半格画了三个人,穿汉服,手执仪仗,两人侧身相对,另一个右向,本以为在这人的对立面她会画上一人相对,却画了一竖排小树的图案,再次破了对称;在右边的菱形纹下她同样画了三个人,但他们不再是全侧身,而是正面稍微倾侧,两人相对,一个独立微向右,其朝向又同左边三个形成了呼应完成了对应;右边上半部三棵小树图案似乎是左边最边一排小树爬了上来,刊名正中直插图案,下面是两条似乎正蓄势欲向右跃出的猛虎,与其相对的恰是两条右盘而折向左的巨龙,势均力敌,又让人觉得它们可能会搅出一场掀天揭地的局面,两龙与小树中间恰是这两龙首正面图,恰似汉刻石墓门常见的铺首,相互组合在一起,又暗合了立体主义将事物不同侧面的形象平面层叠的构图方式。由于大部分图案朝向右,因此此图极具向右行进感,似乎是一组正在运行的镜头或一幅正在展开的长卷的随意而突然的定格。
如此丰富,如此多样,是不是喻意此刊的体裁题材手法风格的不拘一格;而又把如此丰富与多样纳于一炉,是不是在说在表现上应该节制应该注重韵律注重形式上的美感。也许它就是新月派提倡的三美“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的艺术再现和落实到此刊使之复活的封面宣言。
厚植于如此丰富多样基础上的“学文”,会越长越醒目,越长越高大,越长越精彩。——遗憾的是,《学文》仅仅出了四期即停刊,辜负了林徽因的期望。

《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刊头
1935年7月31日,林徽因、梁思成二人替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绘制的刊头开始使用。
这是萧乾先生约林徽因设计的。萧乾先生曾回忆,1933年11月初,他的《蚕》在大公报发表后,很快接到沈从文先生的信,说林徽因读了此文,对此文和作者的写作态度很喜欢,要沈从文带萧乾去她家,“能见到当感到畅快”。11月4日,萧乾在沈从文带领下,第一次去林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林徽因的鼓励,“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窗子内外忆徽因》)1935年夏天,萧乾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接替杨振声、沈从文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将之定名“文艺”。配合此,也是出于对林徽因的感激,于是约请林徽因帮他新设计一幅刊头画。
那一年2月,梁、林夫妇曾带领莫宗江等人前往山东考察孔庙,帮助国民政府拟制修葺方案。回来后,林徽因肺病复发,又移居香山疗养,夏天到来后,也是为了让林徽因更快恢复,一家又赴北戴河避暑。在那儿,林徽因说:“我遇到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林徽因寻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到萧乾的邀约信,设计了这个刊头画。
刊头画寄给萧乾时,她附了一封信,对如此设计作了简短说明,“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于创作前途有点吉利”。这个过程是不是像后来二人设计国徽图案的预演。这也表明二人没有草率随意对待这个设计,而是取一种严肃认真慎重的态度,还包含着二人的良好祝愿。
所以萧乾推出这个刊头画时,在编者话中郑重给予介绍,并表示感谢,“今天这幅壮丽典雅的‘犄角’是梁思成夫妇由北戴河为我们赶制出来的。天虽是热得要命,这图案却是在一丝不苟的努力下为我们设计的。”
这个图案是什么样呢?
一棵繁茂的大树是它的背景。并将前景划分稍显整一的阁楼加以贯穿且使之充满生机。阁楼下一热闹非凡的湖面,鱼跃鸟游,一条小船,后面一船夫在划桨,前面一个正匍伏船头收网。岸边台阶上到阁楼,阁楼加顶共三层,下面两层均有护栏,也均有人在观赏湖面,底层侧面一人是不是为了逗喂鱼鸟还在向湖面撒着什么;二三两层阁檐短直,且有粗大斗栱支撑,阁顶装饰着一只巨大的展翅欲飞的凤凰——真是一派熙和小公园景象。
整个构图是一分层的纵切面,有一种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感觉,是典型的汉砖雕刻的方式。梁思成先生在描述汉代建筑时说,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汉代“重轩三阶”,“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均多有栏杆,多设于平坐之上”,“栏杆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遍”,“明器中有斗栱者甚多,每自墙壁出栱或梁以挑承栌斗”。(《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和梁林二人同时来到营造学社、且和二人一道密切配合进行大量勘测的刘敦桢先生也说:“汉阙与绝大多数明器、画像石所表示的屋面与檐口都是平直的”,“并在脊上用凤凰及其他动物做装饰,这是汉朝建筑和后代建筑在形象方面一个重要的差别”。(《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6月版)看其设计中建筑营造的样式,岂不正是如此规制。其顶上的凤凰,如果同卜千秋墓壁画、马王堆帛画那只凤凰相比,深具汉砖和汉代帛画上描绘的神韵;不重细节描绘而有些符号化,其线条似乎显得粗笨,相反加强着一种稚气乐观天真,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风采。用李泽厚先生评价汉砖雕刻的话来说,“汉代造型艺术应从这个角度去欣赏”,“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然而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沉雄”,“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却洗炼”,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版)如果说上幅横向设计有极其强烈的行进感,此幅纵向上的设计则是不同场景的事件人物在一平面时空的共时特写。
林徽因把汉刻作为“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抗战期间她在李庄开始研究汉代历史,甚至入迷到代入日常交谈,还要写汉武帝传,这固然是因为寄托着希望祖国战胜日寇入侵的心志,对汉刻的赞赏恐怕是一决然的引子与因子;穿越时空,到了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花环与花圈时,当看到学生们帮助其勾出的草图采用的是康乾时期时的线条时,她坚决地说:“你这草图怎么行? 你怎么能用康乾线条,你要去找汉朝的线条。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汉朝时期的线条。”对这话,著名散文家梁衡后来特地跑到霍去病墓前看那些线条,他写道:“线条拙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这不能不归于梁林在古建调查测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如此这般对汉刻的熟悉喜爱与认知。所以新时期后卞之琳回忆林徽因时说,从她汉刻的封面设计不由得会“欣然想起了1949年她参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还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饰纹与花圈浮雕图案的设计)”,这事实本身就具有“很多意义”。(《窗子内外忆徽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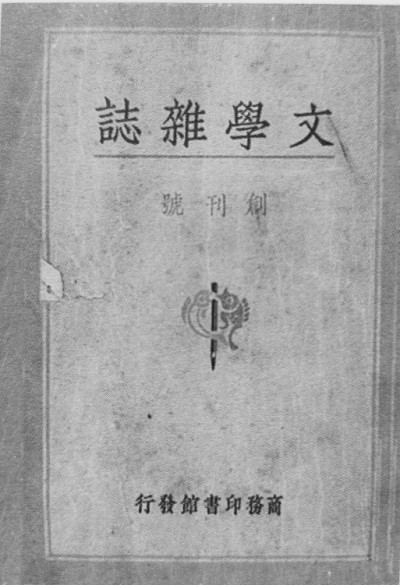
《文学杂志》创刊号封面
1937年5月1日,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先生担任主编,林徽因列为编委,并为此刊设计了封面。
杂志一出世,立即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而封面也受到了好评。刊名用的是宋体,四周用绛色绘一粗一细两条单色线框,中有大量的留白,仅在正中用二十分之一页面绘了一小幅图案,蓝、绛两色的两条小鱼一稍长一稍胖,均头朝上,双龙戏珠般抱着一支黑色下垂的墨笔,绛色同边框相应,蓝色同刊名下的蓝色装饰线和蓝色刊期相应,整个给人一种简洁大方,清新雅致、爽朗活泼的感觉。胡不归很快在《是非公论》上评论道:“宣传许久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于五月一日问世了,它的封面没有鲜艳的颜色,或刺目的花纹,只是几根大方而雅致的线条与宋体字,和内容一样,它代表着保守、认真、中庸、踏实的特色,我们看厌了那些用花花绿绿的封面来吸引读者的文艺刊物,一旦看到这清新而大方的封面,忍不住要说一句:‘谢谢天,世上居然也还有不肯乱跟着别人学时髦的编辑者。’”(《朱光潜年谱长编》)
有人说这两条小鱼用的是《庄子》“秋水”的典,林徽因以此喻文学创作要表达真实的感受,不仅自己知道创作的感受,还要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感受到。(《林徽音先生年谱》,曹汛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版)从她推崇萧乾的创作和对萧乾说的话看,这个推论有道理。但我们看朱光潜先生的发刊词和当时京派文化圈的创作主张,两条不同颜色的小鱼抱着一支笔,是不是比喻着在创作的广阔天地里,不能只准或只能“走一条路”呢?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封面1943年,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完稿,一开始定名为《中国艺术史建筑篇》。林徽因手写了封面。
1940年底,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起来到宜宾李庄。虽然此时营造学社失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时时陷入困顿,梁思成不得不拖着残躯常常前往重庆寻求帮助,但生活毕竟相对稳定安全下来了。他开始试图把自己“和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即撰写《中国建筑史》。因为过去9年,营造学社每年两次派出调查小组,遍访各地以搜求古建筑遗构,每次二到三个月不等,最终目标,就是为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迄今已踏勘了15个省二百余县,考察过建筑物已逾两千,完全具备了实证基础和历史脉络。
1923年5月7日的车祸让梁思成的腿和腰受到重创,并留下了后遗症。长时间野外勘测,抗战期间长途转移奔波,生活的艰辛,使得后遗症日益加重,特别是他的腰和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直不腰抬不起头。人也瘦到了只有47公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艰难的写作,并且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不得不熬个通宵。没有电灯,傍晚五点半便点起了那盏菜籽油灯。为了减轻背脊的重负,他身穿马甲(“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耗损”——林徽因对其马甲支架的形容),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为的是伏案作文绘图时,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画图时还得随着图画的方位调整而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1942年11月14日,老朋友费正清来看望他们。回去后记道,其艰难难以想像,为了写此书,应该是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林徽因与梁思成》,费慰梅著,成寒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林徽因在北平沦陷出走时,肺病即已复发,走到晃县就很严重了。昆明的生活曾使她病情一度平稳,但从昆明到李庄的长途劳顿,再加此地处于长江岸边,气候潮湿,到达李庄不久,病情再度爆发,而且十分危险,尽管如此,只要病情稍一减轻,在处理完家里日常杂事和营造学社有关事务后,积极乐观的她便伴随着梁思成一同进行书稿的写作。梁思成后来说,“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内子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材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中国建筑史》)。
从现存原稿来看,此书稿完成后,林徽因还抄录了五页目录和七页插图目录,还替封面书名作者题签。费正清曾说他们是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费的话虽说有些绝对,但纸张紧缺,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有,也是当地造的土纸,粗劣得很。全书稿就是用这样的纸张写就的,封面也用的是浅灰稍微厚一点的土纸。林徽因的题签并不是简单地写了书名,不仅写得精心,而且版式格式都做了些设计和装饰,因此也应算作她的一个封面设计。
靠右,竖排,字后再加一深灰色条,配上汉隶字体,简直就是一出土的汉代竹简。作者名在下,靠右,稍小。书名有较强的装饰味艺术味,舒畅大方,作者名则显得庄重坚挺,但它们都注重波磔的运用,仍是汉刻线条的再现。特别是书名“筑”“篇”二字的“竹”字头,林徽因做了特别描画,是不是很像古建筑吻脊的反卷的龙尾? 深得汉文化精髓的林徽因,将汉刻和汉建的神韵叠加到一起,投射到了夫妇二人伟大文化结晶的题签上;既然全书是中国建筑史,这样题签,自然更是对全书生命精神的浓缩。
纵观林徽因封面和刊头的设计,既能简约大方,也能繁密布置,但不管哪种方式,她都是慎重的精心的,都能从书刊内容出发,体现内容光华,让读者有一种眼睛一亮的感觉。细加分析,对报纸副刊,她重繁,意在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百花园,对书籍,她重简,意在给读者一种清新脱俗和高贵典雅的气质。从图案的角度来看,她注重汉代艺术风貌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注重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更注重民族精神的张扬。同她其他方面成就比,林徽因这方面的设计相对较少,但仍体现出她不凡的品位。并且为她后来进行国徽等设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