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文学的一座思想高地——重读肖克凡长篇小说《机器》

作者简介:张陵,文学评论家,曾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副主编。
中国工人阶级文学的一座思想高地
——重读肖克凡长篇小说《机器》
文 / 张陵
近二十年来,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处于低谷。优秀作品很少,值得重读的更少。作家肖克凡的长篇小说《机器》正是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之一。2006年这部小说问世时,曾经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相关出版社也组织过研讨会。不过,让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评论都说这部作品如何优秀,但讨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作品的前半部。这种评论策略,在以往的文学研讨中还不曾有过。多年后重读《机器》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半部比前半部重要得多、深刻得多,也出色得多。可是当时评论家们却几乎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一
肖克凡是讲故事的行家里手。他的小说故事性很强,可读性高。《机器》讲的是中国老工业城市天津的一个工人之家两代人的故事。抗战时期,十六岁的牟棉花考进日本人开的纱厂当工人,因为违反纱厂的工作制度,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她被大管事小林白赶到外面罚站,冻掉了一根脚趾。抗战胜利时,牟棉花找小林白报仇,失手把他的一只眼睛打坏了。可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护厂的关键时刻,牟棉花与白小林(即小林白)一起挺身而出。两人消除了不少敌意,牟棉花工人阶级朴素的觉悟里渗进了一丝个人的感情。
微弱的感情并没有机会得以发展。牟棉花经由领导干部李亦墩夫妇介绍,与出身三条石华昌机器厂的工人王金炳结了婚,和小林白的情愫一直留在她心灵深处。小林白是华昌机器厂老板白鸣歧的儿子,他留学日本时取名小林白,其实他的本名叫白小林。他看不上父亲的小作坊,到最先进的东洋纱厂当了高管。
产业工人牟棉花,以主人翁的姿态,意气风发地投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她不仅成了纺织技术生产能手,而且成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纺织擂台赛,就设在牟棉花所在的国棉十九厂。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技术能手云集这里。代表工厂参赛的牟棉花一心要技压群芳,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工厂留用人员白小林送来望远镜,让她看清了对手的技术细节,最终赢得胜利。她的方法被总结为“牟棉花工作法”,在全国纺织系统推广。牟棉花由此进入人生的辉煌时期,但后来被当成了反面典型。好在国家把她派到阿富汗援外,她才脱离了困境。这一去就是十三年,等她回到故乡,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她无法融入现在的工厂,只能在工人疗养院颐养天年,每天通过纳鞋底来回忆以往的荣光。
新的一代把这个工人之家的故事续写下去。当初牟棉花和王金炳结婚后,先收养了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志愿军连长勾东华之子王援朝,后生下了王莹、王凤、王建设。初中毕业后,王援朝以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为榜样,背着家里人到天津郊区农村落户,一心要当社会主义新农民。他有思想、有点子且务实,很快受到重用。但因为救跳井的女知青白瀛瀛,他腰部受伤致残,从此只能坐轮椅。就算这样,他仍然成了远近闻名的“轮椅书记”。白瀛瀛是白小林之女,她爱上了王援朝,非要跟着他来农村,终于嫁给了自己的如意郎君。
年幼的王莹带着弟弟妹妹过日子,大事小事都由她做主。她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东方制冷设备厂,很快就显示出独当一面的领导才能。不久,她就被提拔为党办副主任,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她和父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同时,她还要操心哥哥弟弟妹妹的事情。她虽然不喜欢白瀛瀛,但看到白瀛瀛爱着王援朝,就把这种不喜欢藏在心底。弟弟因受到惊吓,害怕与人交流,严重影响了他的情感生活。王莹想尽一切办法,把弟弟的病治好,让他能够正常恋爱结婚生子。为了帮助妹妹王凤回城,她伙同哥哥,用非常规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她与转业军人冯五一的婚姻,是一次失恋后的草率决定,注定后来不幸福。
王莹在这种生活状态下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工厂生产经营困难的时候,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的王莹临危受命,当上了东方制冷设备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党务生产一肩挑。她把儿子送到冯五一的老家,自己吃住在工厂里,带着工人拼命干,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千万元”利润的指标,争取拿到国家的大项目救活工厂。为了抢在国家“拨转贷”改制之前拿到项目,王莹不惜放下身段,跟管国家项目审批的前男友套磁,还要从冯五一嘴里套出竞争对手的情报,把冯五一的工厂搞垮。国家的大项目批下来了,但工厂的颓势却没有因此终止。产销不对路,市场打不开,产品大量积压。王莹努力挣扎,仍然没能改变工厂的命运。国有工厂以破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援朝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把村办企业搞得风风火火。王援朝成了农民企业家的典型、响当当的改革人物。这时候,他和白瀛瀛友好离婚,只身去国外治病。他终于站起来了,然而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去所有的职务。身心疲惫的王莹再次见到王援朝时,看见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是身边多了一个老人,那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后被送到中国台湾的勾东华。而王援朝和王莹到了这个年纪才发现,那么多年来,他们一直爱着对方。
二
故事并不难读懂,不过要读出故事的意义,却需要走出故事,走到历史进程里,走到时代现实中。作家要展现的是天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业史,重点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生态,把故事放到大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环境中去讲述。
以牟棉花、王金炳为代表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的主力军。他们从旧社会受资本家剥削的血汗工厂挣脱出来,成为工业建设的主人。尽管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任务非常重,但他们心甘情愿、忘我劳动、无私奉献。他们的艰难奋斗,开辟了生机勃勃、不断强大的工业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奇迹。中国工人阶级这种豪迈、乐观的创造精神,代表着充满活力、向上奋进的时代精神。作品通过这种精神,折射出一个时代,也向创造这个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表达深情与敬意。
作品在诗意地表现工业时代的同时,也以现实主义的冷峻让这个工人家庭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历史本意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开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然而,城市改革深化之后国有工厂大量倒闭、工人下岗失业。作为中国工业支柱的国有工厂,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改革的包袱,中国工人由主人翁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中国工人阶级经受着越来越剧烈的阵痛式的历史性严峻考验。

肖克凡
小说中的工人家庭的新一代,刚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解体。王莹考上了工人技术学校,读完后被分配在工厂上班,因为天然的工人阶级基因,根正苗红,很快就进入国家干部序列。日子一天天过着,满满的幸福感。没有人意识到,国有工厂要被私人企业所取代,大量工人将下岗待业、自谋生路。由此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随着工人群体的解散出现了解体的风险。
小说把前后两个时代摆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真实写出了工人生活的巨大落差,也由此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现实矛盾冲突的“牛鼻子”。在中国城市改革进程中,工人的命运正是时代矛盾的真实折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当中国改革进入城市改革深水区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进入一个低谷,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牺牲自己,来实现改革的顶层设计,完成中国改革的任务,但他们无法承受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很可能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性低谷遭到解构。
这个工人家庭的命运转折,正是一个时代思想剧烈碰撞的缩影。小说的思想主题,则是要通过作品直面严峻的现实关系,来呈现这个家庭的命运,具有相当高的真实性、概括性和典型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读《机器》,更能深刻认识到小说的后半部才是重点。
三
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思想碰撞,许多作品已经体现过,《机器》把这种碰撞引入作家所熟悉的工人阶级的现实境遇。多数作品虽触及了时代矛盾,但无法将其融入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值得欣慰的是,《机器》走出了这个写作怪圈儿,塑造了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
这得从牟棉花和王金炳说起。他们都有一个特点:认准了一个理儿,就坚定地跟着走,再大的力量也拉不回来。他们对新社会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非常享受,又有很高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度,是典型的产业工人。特别是王金炳,在旧社会给资本家干过,为人老实巴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厂党组织领导李亦墩特别信任。李亦墩有个奇怪的想法,认为一座工厂,仓库最重要,得让自己最信任的人管。所以李亦墩调到哪里,都带着王金炳。而王金炳就一辈子当仓库保管员,直到晚年,他为了节约仓库改造成本,过量吸食有害粉尘而得了职业病。牟棉花人称“牟大胆子”,她身上有一种不服气、不服输的拼劲儿。这是一个牺牲自己家庭生活的具有榜样力量的先进工人和劳动模范。只有等到她回到家里,瘫倒在床上,把脚放入爱人王金炳端来的洗脚水里的时候,才想到自己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家。等天一亮,她又精神焕发地走向纱厂,走向工作岗位。这两个人物,一个代表着忠诚,一个代表着力量,都是工人阶级硬骨头精神的代表,由此构成了小说所要表达的机器上的螺丝钉的品格和价值观。他们看上去并不起眼,却显示出中国产业工人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就内涵而言,王金炳身上天津三条石的老作坊文化更深厚一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朝阳文化,在牟棉花身上体现得更充足一些。所以,牟棉花这个人物形象更具有时代气息,也更丰富一些。这个女性工人看似大大咧咧,其实也有敏感细腻之处。作者专门腾出一些笔墨写她和白小林的关系。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两人悬殊的政治地位,两人的情感无法进行下去,她只好把自己的“人性”隐藏在心灵深处。牟棉花的个性中被注入一丝惆怅感,整个人物更显得丰满立体。
实际上,《机器》里的大多数人物,都有种认死理的执着劲儿。三条石的老资本家白鸣歧几十年前就想重开一家大工厂,并把它传给儿子白小林。而白小林这辈子就酷爱日本的高科技和工业技术,要用一生把日本研究透。王凤一心想和母亲一样进工厂当劳模,王建设也是立志要把工匠当到底。这么一群人,在社会转型期,显得相当背时,也显得相当笨拙,特别难转型。而更为背时的应该是王莹。这个和母亲同样执着的人,和母亲一样以厂为家,也和母亲一样,选择了一个老实厚道的人当丈夫。不过,丈夫冯五一忍受不了她的个性,最终两人离了婚。她虽然当了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但她再也创造不出母亲当年的荣光,也找不回像母亲当年那样的自信。作为工人,父母那种个性是优秀品质,但作为党员干部,那种品质如果没有进一步升华,就可能产生负面因素。王莹身上那种劳模的拼劲儿、狠劲儿,不知不觉变成了作风强硬、霸道独断、一意孤行。她拼命工作,但群众对她的评价并不高,也不满意,还一度到了冲突对立的境地。
王莹还有一个致命的短板,那就是她没有多少文化。她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也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尽管她自觉克服了“三无”干部的局限,但这个短板始终没有补上。那个年代,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大批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中央也把知识分子列入工人阶级行列,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大批知识分子被解放出来。“日本研究专家”白小林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成为工厂技术骨干的。但这种时代的变化在王莹的工厂里似乎看不到,更不可能融进她的知识结构和管理理念里。靠着落后的产能、过时的技术、陈旧的管理和传统的体制,她要完成工厂振兴的理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注定是要被时代淘汰的。
王莹的文化短板和性格弱点恰恰是她的可爱之处。也许就是她的这些局限,使她处在变革的时代,还能守着一份工人的初心、工人的质朴、工人的厚道和工人的忠诚。她从不谋私利,也不偷奸耍滑,是个信得过、靠得住的党的好干部。她试图拯救工厂和工人的生活,但实际上,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最终工厂破产了,她为工人们争取到了按法律破产,让工人们得到了应有的经济补偿。然而,工人们是不会领她的情的,她能做的只是让自己问心无愧。
在现实生活当中,王莹可以说是失败者,但在小说里,她身上迸发出一种敢于抗拒命运、冲撞现实的精神。她保持了工人阶级应有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品质,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尊严。从这个层面上说,王莹不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虽败犹荣。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立起了一个用一己之力抵抗命运必然性的悲剧性的人物形象。王莹这个人物形象的挺立,也把《机器》的主题推向时代精神的高地,使其有了一种与时代精神相称的思想力量。
四
《机器》中最有创新价值的人物,还不是王莹,而是王援朝。如果说王莹体现了一种悲剧性古典品格的话,那么王援朝身上则有一种化解悲剧的现代人气质。如果说王莹身上带着作家对时代必然性的思考的话,那么王援朝则更像是作家忠于生活的意外收获。在小说里,意外常常更有信息量,更有意思。
这个从工人家庭走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一次意外受伤使他只能长期坐在轮椅上。不过,本来就喜欢读马列主义著作的他,由此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他如饥似渴地读马列经典作品,也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当时读马列著作的知青不在少数,有些人随着时代变化不读了,但王援朝始终如一地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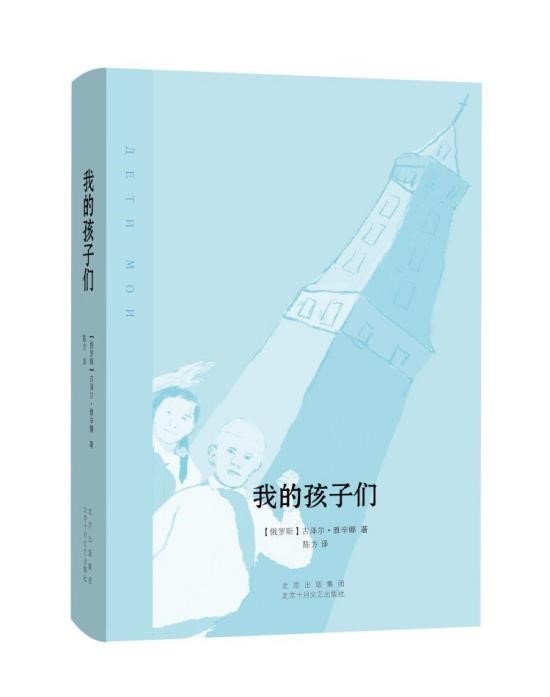
《机器》,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王援朝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读完《资本论》,就开始调研村里二十多户地主富农,研究他们是怎样发财致富的。村里的贫困家庭,想要赚点儿活钱,看他读书多,就来讨教。他就给他们出点子,虽然不能让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但让人着实喘了一口气。村支书是个务实之人,看出这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别人不一样,特别接地气。不仅介绍他入党,还把村支书的担子交给了他。
可以看出,王援朝的思想、世界观、价值观,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来的;他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那里得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帮助他认识到,老百姓如此贫穷,不是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的目的。所以,当他在路边救起老资本家、白瀛瀛的外公白鸣歧时,立刻动员老人帮着村里办起第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这在当时只能偷偷摸摸地干。这一干,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后来改革开放了,金水村在王援朝的带领下,成了一个先富起来的村子。
王援朝的聪明智慧很多时候表现在运用政策上,因地制宜,打打擦边球,甚至会行走在法律边缘。妹妹王凤调回城市无门,他就以“反走后门”之名,让对方想办法腾出一个名额,让妹妹得以回城,又能进工厂。妹妹王莹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找个理由,让企业出钱买下,堆在村子的仓库里,帮助王莹渡过难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的金水村经济发展中,他当然没少钻政策的空子,在法律还管不到的时候,他也由着农民们参与走私,偷税漏税,只是见好就收。
但王援朝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从不利用聪明的头脑把集体的财产变为私有财产。他坚持共同致富的基本原则,虽然他在支部里独断专行,但从不欺负老百姓,而是一心给老百姓谋福利。
在创作《机器》的年代,努力破解“三农”问题,塑造农村“新人”形象,而且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少之又少。作家多数写的是暴发户、“土皇帝”以及官商勾结的富人,如《羊的门》。只有《机器》注意到中国乡村变革中一种新的因素、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生成。
王援朝的形象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信息,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实现了“中国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正在不知不觉转化为中国农村的进步力量,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改革中沦为现实的弱者,却在中国农村改革中显示出工人阶级思想的强大力量。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机器》与同时期许多小说的思想格局和思想品质都不一样。
可能有人会以为这是对《机器》思想主题的人为拔高。实际上,王援朝的思想并没有止步不前。后来,他发现自己读了一辈子马列的书,也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自己再聪明、再大公无私、再有解决方案,都无法阻挡资本的强大力量,都无力改变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两极分化加速的现实。所以,他从国外治病回来后,坚决辞去金水村集团的所有职务,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对于王援朝来说,这不是看透人生,也不是意志衰退,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弱化,而是一种清醒、一种忧患意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自己这一辈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确实,只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而王援朝知道,自己是做不到了。多年以后,当年他触及的“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内容。当然,王援朝这样选择还因为负罪感:他清醒地知道,他靠打擦边球发展经济的办法,不能也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他的退出,并非逃避责任,而是静等处罚的到来。果然,新的企业领导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揭露他为了帮王莹的国有企业解困,动用集体企业资金买了许多滞销产品,至今还堆在仓库里。王援朝平静地承认了这个事实,随时准备接受处理。
这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形象的内涵,大致有四点。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抱负。无论他的性格在历史进程中变成什么样子,他的这个思想内核一直没有变。二是实事求是的品格与智慧。他读马克思主义,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想着怎样让老百姓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的日子。实际上,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生”问题联系起来。三是自我认识非常清醒深刻。他知道,自己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身上有许多历史的局限和个性方面的缺陷。尽管他守住了道德底线,不为自己谋利,不成为资本家。多数时候,他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都是为集体企业谋发展,但有时也动用权力为家人办事。四是他审时度势,看到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有危机意识,知道忍让,不贪恋权力与财富,选择了当一个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普通人。这个形象不完全是我们通常读到的党支部书记的形象,而是贯注着马克思主义精气神和文化品格的普通人形象。
五
由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组成当代文学的基本构架完全出自文学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保证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表现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这个构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农村题材基本上被乡土题材所取代,反而失去了反映“三农”问题的思想穿透力和思想深度。军事题材是当代文学最引以为傲的文学成就,但向“军旅文学”转型后,强化了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拉大了与战争文学的距离,显示出思想的短识,好在意外地突出了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性和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的中流砥柱的价值。
工业题材创作则在刚刚有可能取得成就时,就被兴起的城市文学题材所肢解,真正能和其他题材比肩的优秀作品并不多。改革开放时代,工业题材创作的复苏是从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天津开始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新时期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先声。
工业题材到底挡不住城市文学的热潮,不得不让位于方兴未艾的公司文学、老板文学、财富文学。期间,挣扎出了“打工文学”。这是城市文学中的“励志者”文学,充满生机,却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文学的思想格局和精神品质,也不可能替代工业题材创作。事实上,中国工业能够在后来破解困局、重振雄风,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并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在世界工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身就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肢解,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工业建设的主体,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断加入,比以往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先进性,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力量。只是中国文学对历史变化似乎一无所知,还沉迷在以往工人阶级的悲伤痛苦之中,还找不到工业题材创作的思考点着力、发力点。
从天津老工业城市土壤里培育起来的作家肖克凡不服气、不信邪,偏偏要抗争一下。他心中飞出一只不死鸟,就有了长篇小说《机器》。也许,想抗争的作品还有很多,但只有《机器》站上了思想的高地。还残存着中国工人阶级文化底蕴的天津作家,再次承担起拯救中国工业题材创作的重任。这么多年来,多少同类题材的创作只能绕过这座思想的高地。多少年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发现,《机器》仍然是一座思想的高地。
本文刊登于《文学艺术周刊》2022年第10期,因篇幅原因有所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