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中的家与国 ——关于陈敬黎长篇小说《茶道通漠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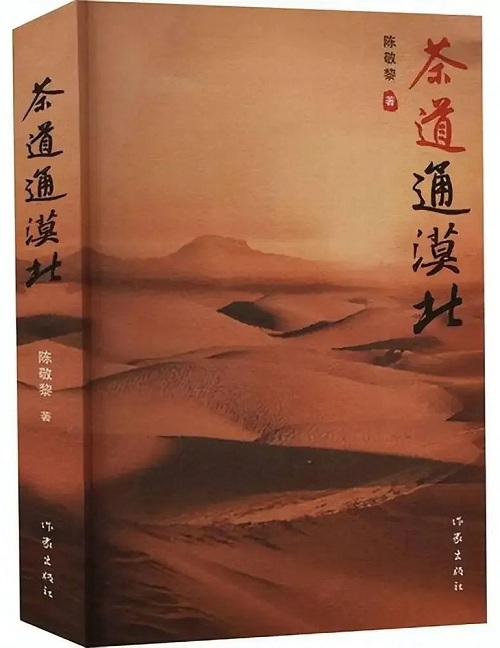
陈敬黎长篇小说《茶道通漠北》
一、青砖茶与其生存的时代
一般认为晋商于明初兴起。其大致的发展可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起于盐,兴于茶,辉煌于票号。从最初为明军输送军需由江南向西北乃至于欧洲转运茶叶,直至由钱庄而票号,汇通天下。五百年间晋商一直对中国经济贸易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们先于福建武夷山一带,后在湖北蒲圻、咸宁一带建茶叶基地,向西北、俄蒙转运。武汉,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商埠重镇、交通枢纽,是“东方茶港”。小说告诉我们,“从汉江边到丹水池形成长达三十华里的汉口码头”,有十万之众的码头工人与运输茶叶的船工队伍,可谓壮观。
《茶道通漠北》反复提到了晋商。其中如大盛魁,有“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之言。而渠家商帮,与小说中的何氏关系密切,是多少代的合作伙伴、商业“相与”。何氏在山西的产业就建在渠家之邻。小说有一条伏线,就是寻找何家次子何建刚。而何建刚正是被何氏之长何安鹤暗中收养的晋商裴家之遗孳裴载言。因而,应该说是寻找“裴载言”。尽管是他人之后,何安鹤却待他亲如己出。裴载言成为情节推进的一个“暗眼”。而在明面上则是拓展以“生甡川”为代表的青砖茶市场为故事的核心。“生甡川”青砖茶,史有其名。湖北咸宁之柏墩,确是盛产茶叶之地。按照陈敬黎的描述,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柏墩本地的茶庄陆续倒闭,或合并至规模较大的长盛川、长裕川。后来他们又合并为“宏源川”。不久更名为“生甡川”,就是小说中何氏家族经营的茶庄。有研究者如武汉大学教授刘再起指出,生产这种黑茶所需之水取自咸宁柏墩境内的“生甡川”。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时候,长裕川正式更名为“生甡川”。
陈敬黎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大致描绘出了生甡川青砖茶的情形。不过其中也存有一点疑义。据刘再起《晋商与万里茶道》研究认为,长裕川、长盛川等均为山西祁县渠家之茶庄。也就是说,“生甡川”应该是渠家之产业。不过,这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小说是不是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是另一回事。在小说中也出现了渠家后人渠庆吉至咸宁柏墩收茶的情节。但这里的渠家,似乎只是一个与何家合作的客商,与生甡川商号没有关系。按照陈敬黎的描述,何氏一家是从事茶叶生产的世家。其先祖何盛川,明末时在山西为官,于祁县渠家相邻之地置产建屋。后发现茶叶能赚钱,写信给其弟何裕川,让宗亲广开茶园,获利颇巨,并在山西推广何氏砖茶。其在祁县经营的茶庄叫“长盛川”,其弟在武汉开设的茶庄叫“长裕川”。按照这种描述,长盛川、长裕川均为何氏产业。在何氏一门中还出现了曾任鄂南特委书记、南方局宣传部长等职的何功伟烈士。这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川”字牌砖茶在蒙古草原地区与俄罗斯等地有巨大的影响。但也不能简单说源于生甡川砖茶。不论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小说设定的时间,生甡川的出现均较晚,只有大约二十来年。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在蒙古草原产生深远的影响似需推敲。而实际上由晋商创立的“川”字牌茶砖,在湖北羊楼洞一带至少已经生产了一百五六十年以上。它是众多晋商在这一带收购制作砖茶的“集体”品牌。如最早进入湖北羊楼洞一带的大盛魁之大玉川、巨盛川、三玉川商号,郝家之天顺川商号,渠家之长裕川、晋裕川、长源川、长盛川等商号。(刘再起著,《晋商与万里茶道》,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12月第1版,第75页、第81页)“川”字牌砖茶不仅深受草原民众、欧俄饮者之喜爱,亦成为草原地带的一般等价物。其信誉非比寻常。
《茶道通漠北》表现的时代,陈敬黎没有直接说明。但在叙述中有对相关背景的介绍。间或也提到了一些与时间有关的表述。小说设定的时间大约有十多年左右。这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北洋政府已经建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复辟帝制业已失败。皖系、直系、奉系军阀混战,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反对孙中山国民政府的蒙古王公们仰仗俄国人宣布了独立。内蒙古中的权贵则与日本人勾结,组建“蒙古义勇军”,密谋进京推翻共和政府。而俄国与日本加紧对内外蒙古的渗透,民族矛盾日渐复杂。孙中山在南方组织力量,发起“护法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这也是小说结束的时间节点。在这一时期内,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主要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小说也涉及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重要历史事件,描写了何建朴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董必武、陈秋潭,以及林育南等人的交往。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革旧图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资本、民营资本均得到了发展,近代化迈开了新步伐。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日渐被外国列强渗透,对民族资本的挤压日深。以茶叶这一产业言,在现代工业、现代交通日渐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的生产方式、运输方式已不适应。而列强盗取茶叶种植生产技术,在印度、日本等地开辟新的生产基地,对传统茶叶市场进一步形成了挤压。以陆路为主的贸易模式逐渐被水路、海路替代。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机器取代。以晋商为主的西北市场、欧蒙市场不断丢失,份额日渐减少。其传统优势被不断地削减。在《茶道通漠北》的时代,辉煌一时的大盛魁商号已不复昔日荣耀。渠家等晋商翘楚也面临严峻挑战。小说的主人公湖北咸宁柏墩之何氏茶叶也遭遇着生存还是毁灭的考验。早在1850年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到,“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第1版,第133页)大约70多年后,马克思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这正是陈敬黎为我们描绘的中国的现实。
但是中国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从社会形态言,新的力量——工人及其阶层正在形成,走上的历史的舞台。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场景。尽管是一次失败的罢工,但仍然显现出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生产方式也在发生着变革。以机器为主的新的生产方式,以铁路为代表的新的运输方式等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反映了中国日见显现出来的与现代化接轨的历史趋势。在这个正发生着深刻变革的时代,对每一个人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即使是茶叶,也存在着命运抉择的问题。而诸如何建朴这样的曾经留学海外,具有浓烈家国情怀的人士,当然不会置身其外。他像每一个人一样,不自觉地裹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二、救自家与救国家
《茶道通漠北》的主人公何建朴出生于茶业世家。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何安鹤遭同道暗算,郁郁而亡。何氏茶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甡川茶庄面临倒闭。于是,他从日本回国,主持家业。小说一开始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大劫案。在何建朴带商队往内蒙归化,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的商道上,遇到了卢金斗手下卢奇义部的抢劫。小说以卢奇义劫走何家次子何建刚,胁迫何家交出名贵的祖制青砖贡茶而放行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更复杂的茶道之争正在展开。从小说的情节发展言,是以何建朴救自己、救何家开始的。正因为社会动乱,才导致商道不宁,商事危亡。就何氏家族而言,屡遭土匪抢劫,又遇家父病亡,可谓雪上加霜。尽管何建朴有能力有才学,却无法逃避匪盗横行的现实。何建朴需要做的是如何改变商道的现状。
何建朴一行在危急时刻搭救了布日固德,并结为生死兄弟。布日固德是蒙族人,任绥远都统暑参谋长。他热爱国家,为人诚朴,带兵严整,治军有方,在剿匪中屡立战功,深受绥远人民称赞。何建朴与布日固德一起,对卢金斗一伙开展了剿灭,迫使卢金斗败退川陕。之后,又与大盛魁掌柜段履庄等设计除掉日本黑龙会特务,不仅稳定了漠北茶叶市场,亦破坏了日本企图分化中国,鼓动内蒙独立,占领分裂东北的图谋。在这一过程中,何建朴从救自家的努力中拯救了西北地区的茶叶市场,也为日后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投奔北伐军埋下了思想、行动与人脉的伏笔。
小说为我们勾勒出何建朴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他对种茶、制茶,乃至于茶叶贸易有天然的喜好、敬意。留学日本的经历又使他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接触了许多新的人物。他的眼界、观念等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日期间,何建朴就参加过李大钊领导的反对“二十一条”的活动。回国后,发现自己竟难以做一个单纯的商人。虽然认真做事,诚实经商,却不断地受到同行的打压。他们甚至勾结匪盗,暗通日寇;劫持商队,杀人越货,茶叶市场日见萧条。国家不兴,商事难兴。何建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有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当年,他曾亲眼看到辛亥革命起义的志士们为国浴血奋战。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又经历了共产党人、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的牺牲。偶然的机会,何建朴结识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要求加入董必武等在武昌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希望能够为革命出力。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何建朴参加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以及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甚至阅读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感到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也许是中国的一条好路子”。他认为,“这些军阀没有人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的鼻子都被外国人牵着,外国人叫他往东,他便往东,叫他往西,他便往西,没有真正赶走外国列强的雄才大略”。他坚信中国独立自主的希望在共产党和革命军。小说甚至虚构了何建朴从武汉至上海,再到广州,想参加黄埔军校投入革命的情节。在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他看到了负责在上海招生送行的青年毛泽东与恽代英。虽然没有说话,也没有交往,但这一经历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他知道,“只要有李大钊、董必武和他只见过一面的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在,中国不愁独立富强不了。” 他的这种转变,既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当代表着希望的北伐战争爆发,革命军一路高歌开向武汉,欲消灭北洋军阀的时候,何家在武昌的总部被军阀征用为抵抗北伐军的守城指挥部。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亲手点燃了标志何氏家族数百年心血的总部,奔向即将到来的革命军。这一幕颇具象征意义,喻示着一个从拯救自家向拯救国家升华的新的何建朴之诞生。
三、叙述策略与传奇模式
《茶道通漠北》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小说,基本上拿起来就不愿放下。这种好看,依我之见主要是得益于作者的叙述。
首先是小说的叙述节奏。陈敬黎总是设计接连不断的“事件”来演绎情节。这些事件的出现并不是读者可以预见的,而是突然发生的。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它与前面的事件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但往往会节外生枝,出人意料地发生。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何氏商队从山西右玉出发,前往绥远。这段商路近年来劫匪猖獗。特别是卢金斗一伙,杀人越货,戗害商帮,无恶不作。前不久何家刚有一批货物被卢金斗的手下卢奇义劫走。这一切似乎在暗示何建朴一行将要与劫匪遭遇。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却是何建朴被一个身负重伤的军官的手枪顶在了脑门上。他们搭救了一个来路不明、奄奄一息的军官布日固德。这一设计使叙述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这时,人们更想知道的是这个人是谁。但陈敬黎就是不告诉读者,反而再一次节外生枝,让劫匪卢奇义一伙出现。但卢奇义的出现也并不简单,有很多铺垫,非常像传统戏曲中主要角色的出场,要一式一式地出,不能一下就出来。开始与何建朴一行叫阵的是一个叫呼斯楞的军官。在呼斯楞叫阵告一段落后,这帮劫匪中又出来一个黑衣人,名字叫昂赫巴雅尔。这个人气势不凡,言语斯文,行事讲究,颇有心计,与一般的劫匪很不一样。至此,人们仍然没有把他们与卢奇义联系起来。但昂赫巴雅尔却自报家门姓卢,他的义兄就是卢金斗,昂赫巴雅尔是他的蒙古名。这时,传说中的劫匪卢奇义才真真实实地来到读者的面前。他与何建朴的一番心理较量显然占了上风。但就在这时,陈敬黎再一次节外生枝,让一声枪响打伤了呼斯楞的手腕。情节又一次在突然之间发生了逆转。如此种种,小说吸引人的力量首先就体现在这些不断发生的“事件”中,引发读者不停地追问:又怎么了?为什么?
不过,在这种不断的节外生枝中,作者的叙述并没有游离主体情节。他只是在主体情节中不断地设计好像要游离而去,实际上却使其情节更加丰满起来的“圈套”。但陈敬黎并不仅仅如此,他总是要不断地调动强化读者的心理期待,在情节发展的某种节点“逆转”情节,形成叙述的悬念。在卢奇义与何建朴一行的纠葛中,被救的布日固德昏死过去,藏在了树洞中。他会不会被发现就成为新的悬念。随之,何建刚开枪之后怎么办就成为悬念上叠加的悬念。当卢奇义终于押着何建刚离开后,人们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当何建朴一行到达归化城时,却被连人带物全部扣押。情节又发生了逆转,新的悬念出现了。小说告诉读者,作为卢金斗左膀右臂的卢奇义是一名杀人不见血的劫匪。但是,随着叙述的推进,他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陈敬黎告诉我们,卢奇义本来是晋商乔家的学徒,爱上了晋商裴家的二小姐裴润碧,两人私定终身。但裴家被卢金斗灭门,裴润碧亦死于非命。只有其子裴载言侥幸逃脱。深爱裴小姐的卢奇义决心要保护裴载言,为裴家报仇——亲手杀了卢金斗。他的办法是投靠卢金斗,在取得信任后借机下手。而裴家少爷裴载言正是被何安鹤秘密收养的何建刚。这时,一个巨大的逆转出现了。卢奇义不再是仇人,而是同道。
《茶道通漠北》在情节设计上有一条明线,就是生甡川茶庄的发展。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寻找保护何建刚——裴氏之后人。前者正是小说集中精力叙述的故事。而后者则断断续续、云里雾里地影响着情节的走向。两者的统一使小说有了丰富的内涵,显现出更具吸引力的品格。但是,在这样的叙述线之上,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精神线,就是诸如何建朴这样的商人,包括他身边的亲友、伙计、相与等是如何觉醒,最终走上救国之道的。陈敬黎并没有直接去写他们如何参加革命,而是不断地描写他们如何去拓展茶叶市场。这应该是作者精明的地方。有资料介绍说,陈敬黎在采风中得知何氏家族有诸如何功伟这样的烈士,滋生了创作一部具有红色因子小说的愿望。但以我之见,他如果直接去写何建朴等人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话,就会失去这一题材的独特性。所幸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何建朴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战士,而是努力表现他精神世界的转变,描写他处于“游离”状态的境遇、行为。在小说中,何建朴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然他加入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却从未参加过这个组织的活动。即使在林祥谦、施洋牺牲的现场,他也并不是有组织地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何建朴只是出于关心,想知道罢工的情况而遭遇了这一悲壮时刻。他也参加了抢运施洋遗体的行动,但并不知道组织这一行动的人是谁,是如何策划的这些核心事宜。他只是被要求送一些吃的东西。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何建朴只是一个“在场”的局外人。他最重要的身份仍然是商人,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进步商人。这种人物设计表面上弱化了何建朴在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实际上更符合他这种“转变中人”的实际,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由此亦折射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陈敬黎的叙述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理想情调。除了小说中的人物怀有救国救民的理想外,更主要的是其叙事方式。其情节设计非常的理想化。事件的发生发展均是作者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小说人物性格、事件演变的必然。从绥远到呼伦贝尔,尽管远隔千里,但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在奉天开设何家的商行,好像也很简单。卢奇义为裴家报仇,混入匪帮,杀人越货,但一句报仇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似乎从前的诸多恶行都可以忽略不计,终成为何氏一家的好友,视如兄弟。何建朴对这样的人物也没有在内心深处表现出任何复杂的心态。卢奇义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的反思。但这一人物的行为毕竟涉及到许多价值观的问题,亦非儿戏。至少作者的处理过于简单。小说塑造了两位令人喜爱的女性。一个是钱氏之女,钱珍珠;一个是闻家千金,闻兰馨。或为巨商之女,或为权贵之后。她们的家世虽然不同,但均高贵美丽,品格非凡,胆识过人,分别爱上了何家大小少爷。钱家本来与何家有市场争夺之隙,又被日本黑龙会胁迫,成为分裂国家、扰乱市场的黑手。但钱珍珠与其父截然不同。不仅给何家通风报信,施以援手,且疯狂地爱上了何建朴,未婚先孕,终于出家,隐入佛门。但在小说的最后又突然来找何建朴,与他一起逃离武汉,投奔革命。这期间钱珍珠的遭遇作者并不交代,而是语焉不详地让她消失,在需要的时候又让她出现。消失与出现完全视作者的意图,而不是情节的发展。闻家千金闻兰馨,出生名门,轻车宝马,执着地爱上了身世复杂的何建刚,也就是几乎被灭门的裴氏之子裴载言。她不论门第,善解人意,可灯下读书,能厨中治家,既玲珑剔透,又诚挚宽厚,实在是人中龙凤,女中璧玉,无论哪一方面都无可挑剔。
小说的这种叙事策略,我们可视之为浪漫主义手法。但也应该是接续了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手笔,并注入了“现代”元素。所谓传奇,就是把人世间的情事集中化、夸张化、理想化,使其显现出与一般人事不同的特异超常之处。这似乎也很适合茶道崎岖这类的故事。从湖北咸宁,至武汉,经长江水运,到河南之赊旗店,再渡过涛涛黄河,翻越巍巍太行,一路往北,出杀虎口,进入茫茫草原。举目四望,不见人烟。回顾来路,竟比去路还要苍茫。更何况一路上还有风雨云雪,虎豹豺狼。杀人越货,视为常见。要在这样的路途中行走,没有非凡的毅力与胆识是不可能的。其间的故事当然极富传奇色彩。我们前人所行之路,所做之事,所遇之累,今天的人们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更不可能亲身体验。这当然应该有非凡的激情,超常的智慧与卓拔的能力。如果不是传奇,还能是什么?
四、地域、民族与人格
《茶道通漠北》描写了几乎是东南西北各地不同的生活。其东,至奉天即今之沈阳与哈尔滨;其南,主要是武汉,以及咸宁之柏墩;西过山西,北至绥远,即今之呼和浩特。此外还涉及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以及吉林、呼伦贝尔等地。把这些地方联系起来的是茶,主要是生甡川青砖茶,以及其主人何建朴。
山西之晋商,是万里茶路的开拓者。这条茶道,最初是从福建武夷山一带定制采购茶叶,然后由晋商转运至中俄边界的恰克图。每年年终,由六位中国商人,主要是晋商,与六位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商定下一年度茶叶的需求量、价格,由晋商采运至恰克图,然后转运至莫斯科,以及欧洲各地。晋商亦在莫斯科等欧洲城市开设商号,成为实实在在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商帮。太平天国时战事纷乱,交通受阻,武夷山之商路中断。晋商又在湖北蒲圻羊楼洞一带,也包括咸宁之柏墩,以及湖南临湘之羊楼司、聂家市等地建立茶叶基地,再经武汉北上,转运至恰克图。马克思在其《俄国的对华贸易》中就注意到,来自中国大陆腹地汉口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使得中俄边境小镇恰克图变成了“沙漠上的威尼斯”。“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恰克图和距它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第1版,第49页)当恰克图成为亚洲大陆地理与贸易的中心后,正是中欧以茶叶为主的国际贸易兴盛的时代。
在这条商路上,归化即今呼和浩特是非常重要的中转地。各地商家,包括晋商,当然也有鄂商等在这里开设了各类商号。晋人创建的大盛魁,其最后的总部就设在归化。不过,在陈敬黎的描写中,山西只是小说的“文化背景”。主要是为何氏茶叶之生产销售提供一种不得不说的存在。至少何家与晋商之乔家、渠家、裴家,以及大盛魁等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显现出晋鄂两地商人之间超越了合作、生意的友情。他们都是商界之正气、道义所在。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晋人形象。如裴载言,也就是何建刚。他勇敢、忠义、感恩,明辨是非,在何建朴的影响下,完成了从报私仇向报国仇的转变。而卢奇义,为报裴氏血仇,采取极端手段,混入卢金斗匪帮,欲寻机手刃仇人。这似乎也可视为一种“义”的表达。最具时代意义的是段履庄,大盛魁商号之经理、末世柱梁。他生不逢时,在内忧外患中走上历史的舞台。段履庄不仅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也是一位有现代意识的变革者、雄才大略的爱国志士。他紧随时代之潮流,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在商界、政界均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山西也是湖北等地商人进入漠北,通达归化的必经之地。在很长的时期内,需从武汉经河南渡黄河越太行,再过晋中,一直往北至大同、右玉,穿杀虎口进入草原,才能到达归化。小说为我们描绘了这段商路的景色、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情状。茫茫草原,荒无人烟。时或飞沙走石,时或暴雨如注。常有土匪袭扰,命悬一线,苍凉孤寂。尽管这是塞外商路的一般情状,但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漫长的商路需要商人们一步一步地行走。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开通了从汉口至大同的铁路。人们不再需要乘船骑驼转运货物,而是从汉口由火车直接开往大同,再将货物转送各地。
在小说中,何建朴从归化到了哈尔滨、吉林,后来又在奉天开设了商号。东北地区亦是其十分重要的活动地。在奉天,何建朴拓展了何氏家族的市场,设立了“寿鹤恒商行”;找到了自己的弟弟何建刚,完成了父亲何安鹤归还裴氏家产的遗愿;为裴家报了血仇,剿灭了土匪卢金斗,保住了裴家的血脉。更重要的是,东北之行使何建朴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更为深刻,对中国未来的认识更具本质。在这一带,他看到了奉天城遍地是外国人的商厦、店铺。列强们正向中国张开血盆的大口,企图吞并中国。而军阀们却在为各自的利益争夺。天下不宁,国将不国。他们仰仗国外势力,听命于外国人,成为其争夺中国的代理人。这些军阀难以改变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未来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为何建朴与董必武等人的接触提供了参照。他告诉何建刚,为张作霖这样的人卖命是愚忠,南方的革命党与革命军才是为国家独立而战的军队,才是中国的希望,与他们在一起才是正道。小说也对奉天等东北一带的地域风情、社会形态、历史沿革进行了描写。如奉天的马拉火车,遍地开设的外国商号,军阀大员们的奢侈生活等等。不过就叙述而言,其笔墨主要集中在情节的推进上。陈敬黎最生动鲜活的描写还是他的家乡湖北武汉与咸宁柏墩。
小说告诉我们,何氏在武汉设有生甡川总部、汉口茶庄、货运仓库、钱利通钱庄等,与当时曹祥泰杂货店、刘有余中药店、维新百货店等成为武昌最具财力的四大名庄。小说介绍了武汉的商业形态、政治形势,以及官商关系。特别是何家与钱家、刘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何家在武昌司门口开设有钱利通钱庄,在保安街毗邻督署衙门开有生甡川总部;董必武在抚院街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蟠龙山上有汉口一带唯一的一座尼姑庵等等。对上世纪初期的武汉,作者非常熟悉,娓娓道来,不经意间就勾勒出一幅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都市风情画。小说特别描写了柏墩茶叶“开庄”的繁盛之景。在茶叶收获的季节,柏墩及其附近的茶农们把茶叶运往何氏之“梅阁”——一个集收购、烘制、销售,以及接待来客的处所。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近百的茶工在不同的岗位劳作,以至于何家的佣工都忙不过来。何家多少年的相与——合作伙伴山西祁县的渠家掌柜渠庆吉也从汉口乘船赶来,亲见开庄之茶叶盛事。小说描写了柏墩的历史,特别是茶叶的历史;描绘了柏墩街市的繁华,介绍了茶叶的兴衰与茶道的变化,以及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列强对中国茶叶市场的挤压,回顾了何家与渠家数代人之间的合作,以及由此结成的生死情谊,甚至介绍了柏墩的美食。这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生气的所在,是一个汇集着希望与未来的时刻,但也是一个隐藏着危机与困惑的季节。茶与人、与国,正结成难以分割的共同体,使人们既充满了信心,又隐藏着担忧。柏墩的现实,正是当时中国的现实。
何氏茶叶在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号。草原大漠中的归化城是小说设定的目的地。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归化、绥远二城的历史、现状,介绍了城市的商业、政治、社会形态。这里是小说情节最重要的发生地。何氏茶叶被竞争对手买通土匪与当地官员联手扣押。本来繁华的茶业市场显现出更深刻的危机。出于自救,何建朴联合布日固德剿灭土匪,漠北市场显现出往日的繁荣。同时,又与段履庄等发现了日本人利用黑龙会成员勾结土匪,暗杀要员,抢劫商队,图谋分裂的种种恶行。他们与布日古德等策划剿灭日本特务,分裂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不论是归化,还是奉天,地处边陲,人口复杂。小说充分地描写了汉、蒙等多民族人民之间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愿望与共同的命运。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本是汉族的人却喜欢取一个蒙族名字。如卢奇义,本是乔家学徒。但他有一个昂赫巴雅尔的蒙族名字。何建朴则以蒙古名字阿木尔在奉天租房子做商铺。这个商铺就叫“那达慕商行”。其中也有蒙族人使用汉名的。何家在归化的仓房里有两个蒙古族伙计,一个叫额日敦巴日,是神虎的意思。另一个叫博日格德,是猎隼的意思。他们都是何安鹤在草原收养的孤儿。为了方便,就叫他们为虎与鹰。这当然是按字义转译的汉名。但他们也坦然接受。
《茶道通漠北》似乎要突出蒙汉两族之间源远流长的深厚情谊。小说为我们介绍了归化城的来历。这座城的建造者是著名的三娘子,名为种金哈屯。她嫁给了蒙古顺义王阿勒坦汗,主张与明王朝通好,和平相处,被明册封为忠顺夫人。人们也称归化城为三娘子城。这座耸立在草原上的城市,在出现之初就是蒙汉人民友好共生的象征。而内地商人的茶叶生意,亦是这种情谊的体现。诸如何氏这样的商家,在草原地带的经营当然受到了许多蒙古朋友如布日古德,以及虎、鹰等的支持关照。小说还设计了一个在归化城生甡川茶庄当伙计的蒙族青年,叫巴图巴雅尔。他忠诚、机智,干练,在何建朴遭遇伏击时驾车脱离险境,护送至城里的医院治疗。何建朴在武汉时曾遇到名为巴特尔的蒙族青年。他武功高强,有正义感,对社会的认知十分深刻,受到何建朴的信任。而何氏一家亦视他们为兄弟。正是汉蒙人民的辛勤劳作才换来草原的兴旺安宁。多少年来,他们相扶相持,农牧相融,才有了自己的国家、土地、牛羊。辽阔的草原、奔涌的长江,都是他们生存的依托。
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融为一体,共同生活,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亦是人们相互帮扶的现实。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浓郁情意。何氏虽为湖北之巨商,但其茶叶市场的开拓与在漠北的晋地商人息息相关。他们与大盛魁商号世代交好,视渠家为体己。何安鹤在临终前特别嘱咐何建朴,不要断了与渠家的联系。何氏对裴家更是义重如天。小说有很多的细节表现何建朴的个人品格。虽然家财万贯,但其生活极为简朴。出行从来是自己一人,行李都是随身携带。他陪母亲从武汉往奉天。给母亲买的是包厢卧铺,自己却是普通的硬座。他不仅经营何家的产业,还常下厨做饭,回家洗衣,丝毫没有巨商大贾的浮华奢靡之气,也没有颐指气使的乖戾之风。他不仅对高官富商礼仪周全,对普通百姓、佣工伙计亦十分真诚。经商以取义为先,获利以共赢为上,做人以情义为重,行事以家国为大。小说着力描写的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意义的价值体现。这不仅是何建朴个人的品格修为,亦是商道、人道的典型缩影。
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何建朴们四处奔波追求的东西多已成为现实。武汉,再次展现出英雄的品格,成为中华腹地连通八方的中心城市。她不仅是一处商贸重镇,亦是现代工业、交通、金融与文化的重镇。地处塞外的归化城,也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呼和浩特。这座青色之城,郁郁苍苍,充满生机。苍茫商路不再荒无人烟,而是一派欣欣向荣。广袤的中华沃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劳作生活,养儿育女,生生不息,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并维护着更大的家。浓郁的家国情怀在血液中流淌,每一个人都汇入了这一滚滚不息的洪流之中。尽管可能只是一滴水,但千万滴水终将汇成不可阻挡的巨浪,将开创更为迷人的崭新时代。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创作,已发表研究成果300多万字。出版有文艺评论集《寂寞的爱心》《人民作家西戎》《生命因你而美丽》《艺术的精神》《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历史文化著作《追思文化大师》《我们的文明》《被遮蔽的文明》等。主编的作品有《聚焦山西电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 学》《刘慈欣现象观察》《“晋军崛起”论》《山西历史文化读本》《三晋史话·综合卷》 《山西历史举要》《开放与融合》《与大学生谈心》等。曾先后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艺术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西省出版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