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诗人耿相新与《复眼的世界》
我和耿相新先生同处一城,在文学会场偶或见到,在我的印象里,耿相新总是照亮灰蒙蒙氛围的那位,红上衣配他的思想者神情,沉默或者发言,都有种既沉思又脱逸的气质。他是给文学会场带来特色和记忆的人物。世事匆忙,岁月恍惚,我这个散淡的人,对这印象并无深究。
直到几年前,我因写一篇评论查阅史学资料时,偶然发现耿相新的历史小说《忽必烈汗》(外文出版社,2013),有着“见人所不见处”的史识,方知他是历史系出身,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中文系出身的同行中,大家的阅读与写作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界外的高人,却带给你惊讶和不可企及。譬如,耿相新的另一本书——《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2011),出版同仁李世琦在书评《一位出版家修撰的书籍通史》中写道:“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他曾师从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刘乃和教授,潜心学习历史文献学两年,在历史文献的考证、辨析等方面得其真传。而刘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入室弟子。这样说起来,耿相新算是陈垣的再传弟子。虽然他本人毫无托附骥尾之意,但我们从《中国简帛书籍史》书后附录的多达26页的参考文献中,看到了他的真功夫。”在这本书中,史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激情熔于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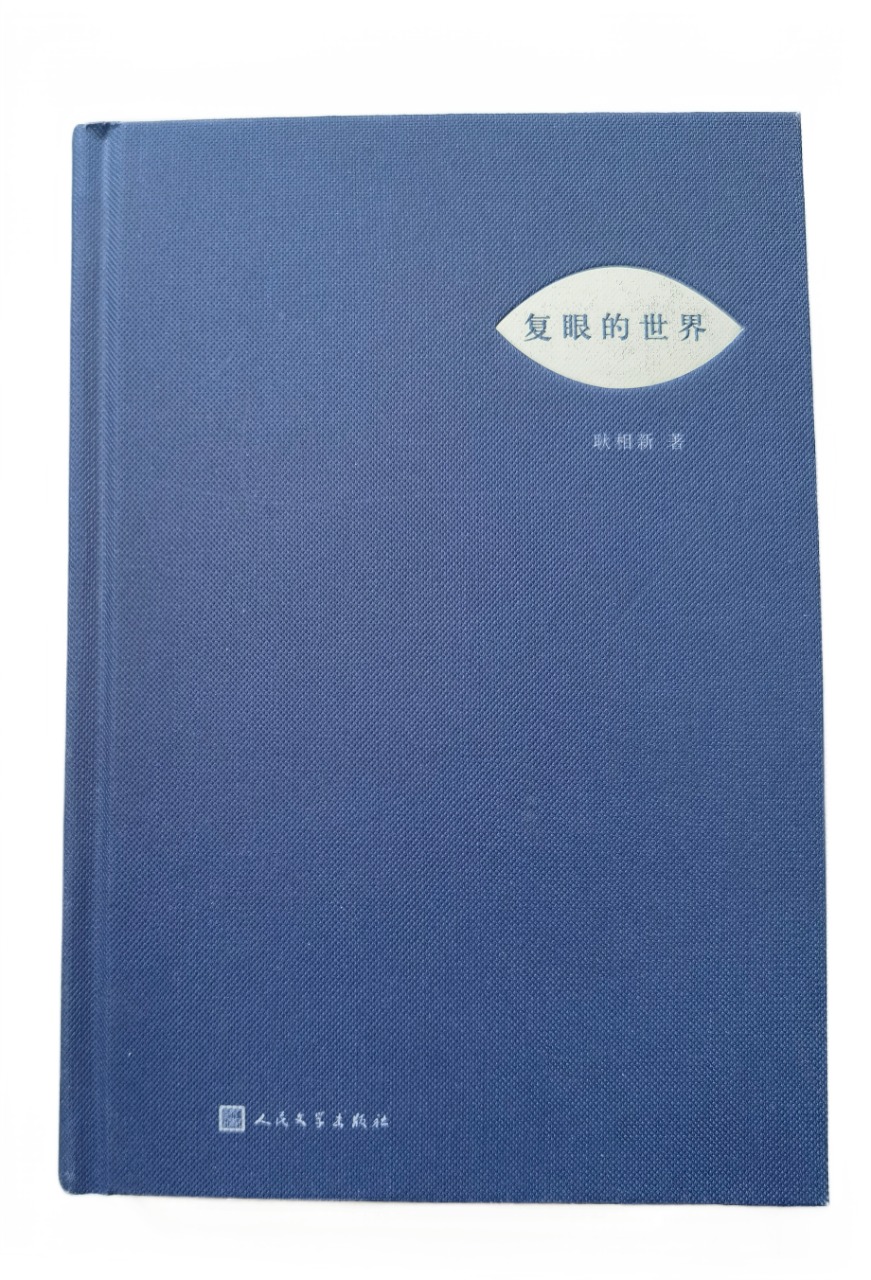
耿相新诗集《复眼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耿相新曾是大象出版社的总编辑,如今是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首先是一个极其专业、现代的资深出版人,他主编的“解读华夏几千年文化之根、血缘之根”的《寻根》杂志,主持的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大象学术译丛”等,都曾是一代人的精神记忆。
这个有深厚史学功底的思想者,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带出与众生喧哗的时代不一样的气息。2022年春天,在为郑州第19届“绿城读书节”代言时,别人自我介绍多用大词、亮词,惟有耿相新的几句话让我感慨并记住,他说:“我是耿相新,我的职业是出版人,我从事出版工作已经37年,我一辈子是为书而生,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作为对时代文化生活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必需自我介绍时,他选择平素的词汇。
作为诗人、学者的耿相新,潜入到创造性生活中的耿相新,在他的新诗集《复眼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里,作者简介都没有。也许是版式设计使然,也许是他有意把自己的诸多社会身份及成就屏蔽在诗之外,我更相信是后者——选择性的沉默,因为这符合耿相新的精神真实。这诗集封面,没有这个时代流行的推荐语;浅蓝色布纹,经典简洁,呈现着诗人内在的风格。
在所有的文体中,诗应是最不宜于谈论的,《复眼的世界》更是难以描述。可以说,《复眼的世界》属于诗中的奥义诗,诗评家耿占春为诗集写了长篇导读,吴思敬在序里写:“这是一部文人之诗,一部哲人的思想录,一位精神飘泊者的歌吟。”当一部诗集这样被描述时,意味着它像经验之海中萃取的盐,类似小说家中的卡夫卡,诗歌中的艾略特,涉世不深的读者会觉它的奥不可及与不易阅读,但历经世事的读者会唏嘘它穿越时空的真实。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耿相新表现出对这个快速变动、复杂而庞大的世界努力认清的野心。一个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学参照系里的作家、诗人,应有这样的野心。曾经,诗人耿相新对“复眼”充满憧憬和好奇,如蜜蜂、蝴蝶、蜻蜓们的复眼,擅长捕捉任何移动的东西,但后来他发现,复眼的成像不甚清晰,认清这个复杂的世界并不能以眼睛的数量取胜,也不能完全依赖快速的反应,正如他在《代序》里讲:“我曾经相信眼睛,但此时,我更依赖思索。复眼,已经过时。”
“复眼”是看世界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隐喻,意味着认识这个世界的N种方式。诗人以这种观看方式,来描述变化中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多种影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固化”的语言和观念的消解,是对经验和文化的重新考量,并且诗人自己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超越。
诗人耿相新以思想者的深度,以不仅是复眼的方式,表达我们最熟悉的经验时,瞬间惊醒起我们的眼与心,让我们面对一种内心隐痛的陌生感——经验的分裂、不可把握。“镜中的脸,还是不是自己的脸/犹如,你眼中的他,还是不是他……”(《镜中的脸》)“古道上的人,一如既往,回归到了地下/古道上的云,一如既往,回归到了天上”(《崤崡古道》)他在写现象,分明又是在写大时空里万物的秩序与命运。
“当我的声音,被周围听懂时/我却,无限地热爱上了,闭嘴……”(《一束光》)“一个人,携带着沉重的思考/那些疑问,在长发上,随风而动/他行走在知识的十字路口,孤苦/他是在荒凉中离家的行者……”(《道》)这些诗句,像是耿相新的精神自画像。一个有思想力和人类情怀的诗人,他深深懂得语言的限度——懂得节制与沉默,懂得写作的要义是对于真相的不断寻找和发现。
他这样写人在宇宙间的孤独感,寻找或自由与被规定之间的悖论:“所有的人都是孤儿/太阳系里飘浮着一个星球/栖息在上的人类,无法摆脱/被遗弃的心态,徒劳而不懈/寻找邻居,企图群居于天河的岸……”“一个人就是一个星球,自传//然后公转,在不被抛弃的轨道上你不能离开。你必须牢记,你的位置”(《孤儿》)
这是史学家、诗人耿相新和一般作家、诗人的不同之处,他不止于经验的表达,他似乎想通过诗学表达,来完成对个体和人类世界认清的野心。
这个有历史感和世界感的诗人,首先或同时,是一个有大视野的诗读者、研究者。一天,我在“小红书”上意外发现他收集了新时期以来所有的汉译诗歌经典,并分类评介研究。他以史的方式、以“竭泽而渔法”,梳理世界经典诗歌和诗人。当史学家耿相新以“考古”的方式来面对诗歌时,诗界人谁能比得过这份较真溯源和发现呢?这让我想起大作家纳博科夫和伍尔夫曾强调过的,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是一个优秀的读者。面对耿相新的世界诗歌史研读,我于内心惊叹:学术、写作和人生本该如此深度、深情。
2022年初夏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