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游戏”:你只是得到,你并未选择

作家的油画像 Astrid Kjellberg-Juel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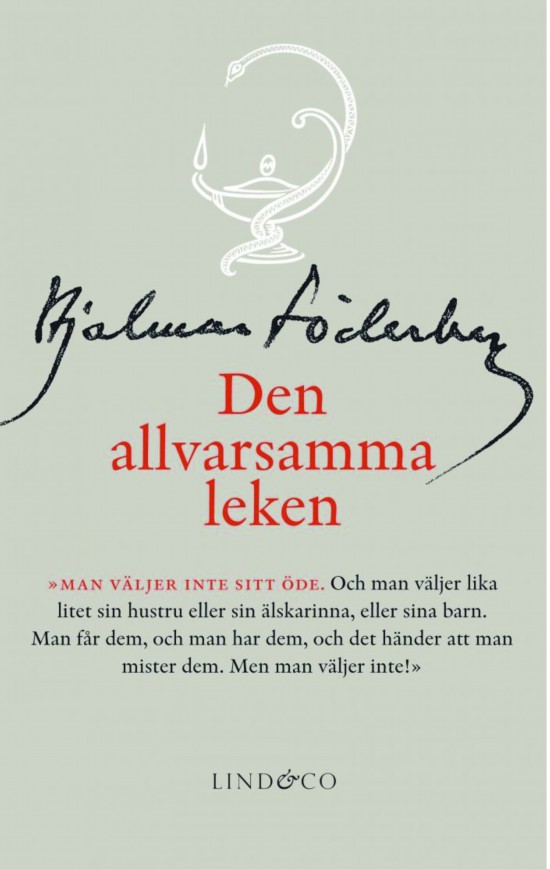
《严肃的游戏》瑞典语版
在他生命后来的阶段里,瑟德尔贝里会想起1906年的那个秋天,他称之为炼狱。他觉得自己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弯曲的地下通道,越来越窄,后来他必须爬着,他找不到出口,也看不到一丁点光亮。有一天他照着镜子,他才30多岁,可他觉得自己老了,每一天都老一岁。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Hjalmar Söderberg 1869-1941)是瑞典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他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公务员家庭,是小说家、剧作家,也曾在斯德哥尔摩当记者。
虽然母亲曾为他的文学志趣忧心,他的从文之路颇为顺畅,20岁前后便开始在《每日新闻》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他一生著有《错觉》(1895)、《马汀·别克的青春》(1901)、《格拉斯医生》(1905)和《严肃的游戏》(1912)这4部中长篇小说,约90篇短篇小说,《雅特露德》(1906)等3部戏剧。在一场严肃的婚外情游戏后,他抛开对诗歌、文学和情色的幻觉,南下哥本哈根,在那里写时事评论并研究基督教史。
写了又写的情与爱
无法找到第二个瑞典作家像瑟德尔贝里这样不厌其烦地在文本中启用情爱素材。他有一则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亲吻》,写女孩和男孩初吻前微妙的心理活动,他写得更多的是幻灭的情与爱。
瑟德尔贝里笔下的情爱,炙热而执著时仿佛宗教体验,比如格拉斯医生的单相思,雅特露德对爱的执念,前者是地下的潜流,后者是地表的激流。“爱,它到底是什么?”雅特露德也说不清,相反,她觉得爱是个奇怪的字眼儿,听来古怪,不像真正的瑞典语。爱,它到底是什么,若拿它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怜惜,意思不含糊。若将其聚焦于情侣,则无论用什么语言来解释,都会让人迷失在语词里吧。
雅特露德需要完满的爱,三个男人都没法让她满意,她似乎注定要处于孤独之中。《错觉》的男主人公、一名医学院学生游走于女人之间,抛弃一个,让另一个怀了孕。《马汀·别克的青春》的内容部分基于童年记忆,是瑟德尔贝里在文学上的一次突破,包含对两性关系和生命意义的探讨。《格拉斯医生》以世纪之交的日记铺展出一起谋杀案,牧师的婚内强奸、海尔嘉的婚外通奸、格拉斯的单相思都让瑟德尔贝里看来越发像书写情爱的专业户。1940年代,有评论家将瑟德尔贝里的最后一部小说《严肃的游戏》称为“我们的文学中最好的爱情小说”,这一说法近百年来被看作赞誉,可它也一定会误导出对《严肃的游戏》的表面化阅读。
瑟德尔贝里的情色故事并非纯白色。即便《亲吻》那样的纯爱素描,也没用单线条,而是加入了时而敌对的心理活动。而《严肃的游戏》里作为背景的夏日恋曲中有海水的波光和星星的闪亮,是全书最纯粹而浪漫的篇章,可还有些别的。有嫖妓经历的阿维德在亲吻莉迪亚的瞬间,怀疑莉迪亚已非处女之身。莉迪亚与阿维德10年后的旧情复燃里没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纯粹,一次次交欢,阿维德期待身体外更深的连接而求之不得。像是画一个不曾画完的圈,像证明对当下存在状态的不满,唯独不像纯爱。
瑟德尔贝里本人的婚外情既为他提供了海尔嘉、雅特露德及《严肃的游戏》的女主人公莉迪亚的原型,也提供了故事。就像瑟德尔贝里过早抛开文学一样,他一面将情色作为观察和描摹的对象,一面层层剥开情色的外皮。那些摊开的外皮无言地暗示,情色是人活着会经过的试炼之一,它在一些瞬间帮人超越日常的绝望,它给人不同时期的状态着色,而最根本的,它只是让人理解存在的滋味。瑟德尔贝里一再书写情色,终究是写它如何现出原形、灰飞烟灭。
严肃的游戏
单从情节看,《严肃的游戏》说了一段陈腐的婚外情事。年龄相仿的莉迪亚和阿维德在夏日海岛相爱。阿维德不愿过早受拘束,不确定这段情和以往的有何区别,不能在经济上支撑婚姻。秋天到了,虽说对莉迪亚日思夜想,他却没去找她,而让命运决定一切。可当他听说19岁的莉迪亚嫁给51岁的名学者时,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日子是往前走的,命运将阿维德放进一桩不错的婚姻,并且他过得很幸福。
夏日恋情只是一道背景,真正的故事10年后才开始。那时秋已走远,在寒冷的冬夜,阿维德和莉迪亚偶然重逢、旧情复燃。不久,莉迪亚离了婚,到斯德哥尔摩独居,她完全无意和阿维德做夫妻,而是周旋于几个情人之间。阿维德不堪面对真相,踏上南下的列车、远离伤心之地。
小说人物几乎都有原型。莉迪亚的原型叫玛瑞尔·冯·普拉腾,19岁时结婚,30岁时离开55岁的贵族丈夫和11岁的儿子,在20世纪初从南方北上斯德哥尔摩追求文学梦。她以一封女粉丝的信搭建起与风头正健的“马汀·别克”的联系。两人的婚外情从1902年持续到1906年。玛瑞尔同时与另几位作家有或长或短的桃色关系。这个摩登女性对瑟德尔贝里构成毁灭性打击。得知情敌之后,他不得不立刻逃离丑闻,逃离故乡。《严肃的游戏》因此常被读作一个男人因为对一个尤物的激情而自我破碎的故事。可或许这只是误读。
叫“莉迪亚”的森林宁芙
1922年夏,在《严肃的游戏》出版10年后,瑟德尔贝里收到一封来自莉迪亚· 斯蒂勒女士的信,她发表过一两首诗歌,问大作家是否因此才对这个姓名有印象,借用到自己的小说里。大作家对这奇怪的巧合吃惊不已,他回复说,莉迪亚来自贺拉斯的文字。
贺拉斯诗集里有不少情诗,莉迪亚出现在四首诗里。诗里的“我”以局外人姿态描述莉迪亚的情感故事,又时时藏不住情绪化表达。诗歌讲述一名男子迷恋莉迪亚,以至忘记了职责,爱使他嫉妒,流出最苦的胆汁。到第三首,嫉妒发展为复仇的欲望,莉迪亚老了,不像从前那般令人垂涎。最后一首诗里的对话透露,“我”和莉迪亚也有过一段情。“我”想知道,爱情的钟声若有机会再次为往昔的情侣敲响,会怎么样。可如今,莉迪亚身边有另一男子,诗人正与金发的克洛伊在一起。贺拉斯问,若古老的维纳斯回来了,金发的克洛伊给扔了出去,一扇门为莉迪亚重新敞开,会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严肃的游戏》演绎了为莉迪亚重开一扇门的故事,阿维德金发的妻子达格玛成了现代小说版的克洛伊。
贺拉斯的莉迪亚是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诗歌里常见的喜怒无常而妩媚诱人的女人,总周旋在暴风雨般的情人关系里。古罗马的莉迪亚来到北欧的自然和文学环境下是个什么样呢。和莉迪亚偷情日久的阿维德有一天给自己斟上一杯酒,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妻子就在门外,而他想起几行诗来:“可这颗心,叫森林宁芙偷走了的,/他再也拿不回来。/他的灵魂在月光下逐梦,/他没法再爱一个配偶。”男人非要投入宁芙那巨大的诱惑不可,尽管将无法再爱一个人类的妻子。
重归斯德哥尔摩的莉迪亚不再是夏夜的天真少女,她不在父亲膝下,也不在丈夫跟前,她的第一个婚外情人不是阿维德。成了阿维德的情妇后,她和其他男子发生了关系,其中一个在圣诞节早晨自杀,因为不久前,当阿维德在莉迪亚那里过夜时,这人按了门铃,吃了闭门羹。相比于有一个私生子,对妻子不忠的阿维德,按当时社会的逻辑,阿维德只是陷入了中产阶级男子的生活常规,莉迪亚则被看作对男性有杀伤力的蛇蝎美人。这一看法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1973年,有女作家出版小说,采用了莉迪亚的视角,并将故事挪到20世纪中期。
无论如何,阿维德也在莉迪亚那儿吃闭门羹后,一天,他看着自己的幼女,竟冒出这样的疑问:“我的孩子,你长大后,会是个达格玛,诱惑一个男人同她结婚……还是说变成个莉迪亚,诱惑一个又一个男人,从不安顿下来,直到年老和死亡带来结束……”
你只是得到,你并未选择
创作之初,瑟德尔贝里将《严肃的游戏》定名《莉迪亚的错》。若将小说情节狭义地误解为婚恋纠葛,卷入纠葛的所有人都犯过错。这游戏里有一条以情爱之名包裹着的欺骗链条。莉迪亚的丈夫不该用富贵“买下我作为合法的情人。怀孕和孩子则不在他的规划之内”;达格玛不该用谎言让阿维德就范; 阿维德和莉迪亚不曾忠实于夏日恋情,各自成婚后不曾忠实于婚姻。当然莉迪亚对道德观做出的挑战最大,在阿维德看来,是莉迪亚“勾引”了男人,还让其中一个送了命。
感情纠葛里的错只在表面,深处是命运里无法避免的错。许多要素出现在生命路的两边,像树上的果子,人以为可以自主地摘取它们,却往往是不得不如此,一定会如此。
有人曾询问瑟德尔贝里,书名到底是偏于“严肃”,还是“游戏”,得到的回答是两者一样重要。
地产大亨的女儿达格玛对阿维德有兴趣,报社同事麦克尔说:“小心!从前是男人找女人,那是旧风俗。如今女人来找男人,而且不择手段!”阿维德很快就对诱惑投降,她给他提供年轻和美丽,不接受便是傻瓜。与阿维德上床之前,达格玛问:“你爱我吗?”“当然,”他回答:“我爱你。”阿维德觉得,不这么说无法开始床笫之欢。“爱呀爱的……他已失去自己的第一颗心。他认为要7年才能长出一颗新的来。可一个人自然的冲动没有休眠,远远没有。”几乎每一晚,她都潜入他的公寓。即便如此,阿维德一再表示不会结婚。最后,达格玛跟他哭诉,父母得知了两人的关系而震怒,她只好说他俩已秘密订婚。阿维德上门赔罪,做了这一家的女婿。多年后,他才明白,父母震怒和秘密订婚的戏码是达格玛自编自导的。
麦克尔提醒过阿维德:你利用她以及她对你的爱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是人之常情,可这样做也很卑鄙……你不想结婚,你没错,你结不起。可问题不是你想怎么样,而是会发生些什么!你不选择,你并不选择你的命运,正如你并不选择父母和自己……正如你并不选择妻子、情妇或子女。你得到、拥有,也可能失去他们,可你并不选择他们!”
那不存在的湖泊
莉迪亚问阿维德:“你能告诉我吗,陶拟泽湖在哪儿?”阿维德觉得耳熟,却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过或读过:“我怕是不知道,我猜它在德国或瑞士的某个地方。怎么,你打算去那儿?”莉迪亚说:“想去,非常想,要是我能找到它在哪儿。”他俩接着有如下的对话:
“那应该不会太难。”
“恐怕很难,”她说,“昨晚我失眠了,想着《当咱们死人醒来时》里的一段。始终听见脑子里有句话:可爱的,可爱的是陶拟泽湖的生活!而后我想,我猜,并没有那样的湖,可也许那正是它如此可爱的原因。”
“哦,这样啊,我想你说得对,那样的湖一定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
事实上,在嫁给名学者之前,莉迪亚给阿维德寄去一张小卡片,上边画着秋色中的水面,又说她真想到远方去。那远方的湖一定不会出现在人所生活的环境里。可爱的湖,它在易卜生的那出戏里和美好往昔一同出现,是存在着幸福的地方。莉迪亚想到那里去,不像要返回过去,更像要获得眼下和未来的幸福。
幸福在哪里呢,在哪里?它就在阿维德和达格玛的婚姻里。
阿维德和达格玛从命运中得到的婚礼于1904年2月10日举行。那一天报童奔走在街头,于暴风雪里高喊:号外号外,俄罗斯、日本交战!显然这不是瑞典常见的有六月新娘的明媚婚礼,这场婚礼安排在暴风雪之日,婚礼的主角未必不是疯着,天疯着,世界疯着,像一场大闹剧里套着小闹剧。
然而,在关于阿维德和达格玛婚姻的段落里,集中出现了三次和幸福相关的表述:“阿维德和达格玛在一起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阿维德和妻子过着开心的日子”,“除此之外,他们非常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岁月流逝。”这恐怕就是命运中的许多婚姻的状况,没多少人会自寻烦恼,把脑袋伸进“除此之外”的袋子里,看里头有些什么。
十年后,阿维德和莉迪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偶然相遇,中场休息时,他俩的手伸出来,找到彼此。沉默。而后,她低声说:“你幸福吗?”他沉默了片刻回答:“我想没有人真正幸福,可不管怎么说你得继续活着,尽己所能。”“没错,”她说,“我猜你做得到。”他们没再说什么。阿维德以自己的语言诠释了瑟德尔贝里以世俗标准颁给他的幸福奖状。
炼狱和地下通道
十年后,他俩共度一夏,像是对海岛夏日做遥远的呼应。在同床共枕前,莉迪亚说:“这一个夏天里我俩的日子再不会有了,永远也不会了……”阿维德觉得他们能永远相爱,莉迪亚拿眼睛笑了笑:“能,当然能,永远并且始终,至少直到明天早晨!”如此,她率先点穿了情爱的虚幻,而她也早已用追逐其他情人的行动来粉碎爱的幻觉。
情爱闪耀着绚丽光芒时或能让人战胜自身的残忍、狡猾和欺骗,然而这不意味着情爱中不含残忍、狡猾和欺骗。情爱的魔力消散时,那些大大小小、有意无意的残忍、狡猾和欺骗显现出来,像融雪下的一切。情爱会变,灵魂是,人也是,在变幻着的时间和环境中变化。人在生长,灵魂在生长,从软到硬,从单纯到浑浊。仲夏夜,少年格拉斯亲吻了初恋,而在医生的回忆里,那个时空是失落的天堂。也是夏夜,10年前阿维德和莉迪亚在星星闪亮时亲吻,10年后,他俩从偷情的狂喜跌入冷漠的背叛,这一前一后恍若隔世。
瑟德尔贝里并未局限于所处时代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他无法改变社会的倾向性,但他最大限度地赞美了女性,无论雅特露德、海尔嘉或莉迪亚,都是男士仰慕的对象。海尔嘉无辜而美好,雅特露德执著而热烈。瑟德尔贝里不太理解的是莉迪亚,从阿维德的视线看去,10年后的莉迪亚矛盾而冷漠。而她们都是玛瑞尔的化身。
因为妻子的疾病和经济压力,瑟德尔贝里婚姻的院落里火星四溅,和玛瑞尔的情事如火上浇油。瑟德尔贝里自述这段情是自己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而玛瑞尔在信中跟人表示,她从未爱过作家本人,只爱上了马汀·别克。
《严肃的游戏》对死亡的激情做了防腐处理。如果说斯特林堡和他笔下的男人多以仇恨结束和女人的关系,瑟德尔贝里和他的男主人公们多以分手和伤痛来了断。《严肃的游戏》将自己扮成情色悲剧,可它不过是诉说生而为人的悲哀。婚外情本身并未对婚姻产生致命的作用,出了大问题的是阿维德和莉迪亚的情爱本身,它从夹杂谎言的真情演绎到满是谎言的假意。这是世上不少人与事的状态。这不意味着人得否定一切,只意味着并非一切都是人以为的模样。摘树上的果同时是自愿的和被迫的。人生中的不少抉择和行动与此相似。
“在他生命的后来的阶段里,阿维德会想起1908年这个秋天,他称之为炼狱。他觉得自己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弯曲的地下通道,越来越窄,后来他必须爬着……他找不到出口,也看不到一丁点光亮……突然,他觉得自己老了。似乎每一天都老一岁。”情色所铺的常常是这样的炼狱和地下通道。
苦涩而彷徨的男子们
瑟德尔贝里时常聚焦世纪之交和现代化大潮中缺乏行动力的男子,来自韦姆兰乡间的阿维德是其中的代表。阿维德对都市现代性时有困惑,身处保守的中产阶级传统和新时代女性的夹击之间。他在经济上不够独立,不能随心地娶他所爱的女人,又无力抵御富家千金的诱惑。记者身份增加了他的自信,却无法消除他的困顿,他效力的报社本身因经济原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又竭力报道着世界的风风雨雨。阿维德顺水推舟地完成了对婚姻及婚外情的选择,像无以果腹的人摘下长在必经之路边上的果子,他选又没得选,却早晚得选。这人看上去苦涩而彷徨,自作自受、自相矛盾,也正因为如此,才契合了人的普遍弱点,促生了作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小猫雅各布和美德
瑟德尔贝里的文字率真而优美,没有同时代作品难以摆脱的道德宣讲。也给读者充分留白,开放的文本和他对事物难免怀疑的态度相当吻合。关于道德,瑟德尔贝里写过这样的插曲:
“儿时的我对善恶还挺了解,后来忘了。儿时我确信小猫抓老鼠很乖,嘴里叼着小鸟走来就太淘气,我对这些就跟知道二二得四一样确信……记得某年夏天我们住在乡下,那是个星期日,我们受邀去教区长家就餐。餐桌摆在花园里。突然……黑白斑点的小猫雅各布气定神闲地走来,嘴里叼着只小燕雀。教区长震怒,起身在整个花园里追逐小猫,好将美德鞭打到它罪恶的皮毛里。与此同时,烤鸭凉了。猫爬到了一棵树上,牧师带着悬而未决的案子走回来:实在抱歉,朋友们,我急躁;看到猫将它那食肉动物的牙齿咬在无辜的小鸟身上,我内心十分不安。给我夹块鸭肉,亲爱的妈妈!”
带着对道德的模糊性的洞察力,瑟德尔贝里从不对道德问题做简单的回答。当他不得不直面这些难题时,往往用诙谐和讽刺来应对。那并不意味着圆滑和失真,有时反因为逼真而显得尖锐,就比如阿维德在海岛夏夜亲吻莉迪亚时的那段关于处女贞操的联想。
被严肃对待的虚无
在留下的照片或图画上,瑟德尔贝里总一脸严肃,像一个命中注定的苦恼人,偏这苦恼人严肃地跌入了一场玩不起的游戏。
瑟德尔贝里很欣赏中国诗歌,有人因此觉得他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从中国文化中感染的些许特色,比如说带着忧郁的宿命论。
处女作小说《错觉》的黑白线描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不乏幽默,基调冷而悲,其后的作品里的诸多元素、主题,对人生怀疑的态度都已深埋下去。像土里的水仙花球,一旦三月春暖便冒出绿叶、开出相同又不同的花。男主角难定生活方向,站在深渊边。他也想走向大众认可的幸福和成功,可这条路上荆棘丛生。
接着的几部小说都涉及男主人公不被祝福的爱情,不愿适应主流模式、又不得不随波逐流的无奈,都书写了人与存在的搏斗。
《马丁·伯克的青春》的忧郁里时而闪过清冽的思想光亮。马丁本想成为诗人和自由思想者,而冬夜冻结了诗歌、幻想和青春。瑟德尔贝里以食物置于冰上给粘住作比,又写到,“我曾渴望在巨大的激情之火中燃烧。它从没来过,要么是因为我不配获得这么大的荣誉。”后来马丁怀疑这样的火更像快乐之火,火却不是他的元素。他只和冰雪相关,“一旦真正的春天的太阳进入我的生活,我很快会腐烂”。最终,马丁走入永不消散的冬雾。小说带着瑟德尔贝里内心的悸动呈现了幻灭。
《格拉斯医生》让一名医生坦露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和情感。年已30岁,渴望崇高的爱情又一日日被空虚吞噬。年轻而美丽的牧师太太海尔嘉向医生坦白婚内强奸、无法离婚的隐情,希望医生帮她找个借口,好拥有身体的独立。格拉斯医生很快明白海尔嘉的情人是谁, 却没停止对海尔嘉的单恋。牧师让医生给弄死了。牧师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活着的人的难题消失,海尔嘉遭到情人背叛,对格拉斯医生内心的挣扎一无所知。一切结束时,除了寒冬和空虚,再没有别的。
青春片段还未从记忆里消失,现实婚姻无法消除灵魂的困顿。阿维德几乎是个不错的男人,工作勤恳、对他人友善,按生活惯性对待妻子,但他找不到更大的生活意义,和莉迪亚的偷情成了一管麻醉剂。他背叛妻子又被情人背叛。从一场游戏中醒来,他发现周围是可怕的虚空。
《格拉斯医生》里运作的是离奇的谋杀情节,在《严肃的游戏》里,情色以软刀子杀人,但整个故事距日常世界很近而更具普遍意义。它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对梦想和现实的双重远离,对是与非的不置可否。
瑟德尔贝里曾企图寻找两个灵魂和两个身体完全融合的情爱。斯特林堡让爱情变成一场权力争斗,瑟德尔贝里则让男女在生命的舞蹈中相吸相斥,曲终人散而见生之虚空。
如幻如梦、无法驾驭,情色如此,人生和世界亦如是。《严肃的游戏》里个人情感的虚无只是大世界虚无的一个缩影。在更大的世界里,报社随时有倒闭的危险,挪威闹着和瑞典脱钩,欧洲弥漫着战争风云。世界是一个更大的虚空,这是瑟德尔贝里传达的叹息,他的思想和感知并不积极,却是真实的、现代的、因而能传至久远的。他和他的男主人公一样与世界有天生的游离,而这样的他也是同时代人忠诚的记录者和敏锐的心灵观察者。带着压抑的悲哀和不情愿的宿命感,看穿了谎言和幻觉的他,曾于斯德哥尔摩的石子路上,在克拉拉教堂的钟声里踽踽独行。
想做社会的灵魂
情色和人生问题上的幻灭感没让瑟德尔贝里彻底遁入书斋,比怀疑和幻灭更强大的是他的真诚和勇气。1922年问世的第三部戏剧《命运之时》以一次大战为背景,包含对战争爆发机制的分析,描绘了人文主义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代,瑟德尔贝里呼吁世界沉睡的良心,反对狂热主义和好战思想,强调纳粹主义意味着文明的最终衰落。瑟德尔贝里对1930年代德国事态的洞察引人瞩目,如阿维德年轻时梦想成为的那样,他被誉为社会的灵魂。他对纳粹主义和好战思想的警惕,在今日仍有现实意义。
瑟德尔贝里过早抛弃文学创作对世界文学来说是一大损失。从翻译语种的数量、图书借阅量、再版数、影视和舞台上的亮相频率看,瑟德尔贝里的小说是瑞典乃止北欧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他写出了瑞典文学中最完美、最温婉,深刻而敏锐的书页。文本折射着时代,不机械、不被动,以文学虚构调动了自身的观察和体验。他的记录自然流畅又暗藏精巧构思,让夏和冬都传达出象征的意义。在他年仅30岁前后留下的文字里有许多难以复制的成分:明澈如赤子,诗意和激情如青年,洞察人的虚伪和生的虚幻如垂暮老人。他描摹时代画卷,人的行动和情感和国内外时事、和斯德哥尔摩的建筑和四季互为生命的证人。克拉拉教堂的钟声今犹在,阿维德和达格玛走过的桥也在,莉迪亚挽着未婚夫走过的动物园岛上的小径仍是个最美丽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从1890年代初开始,瑟德尔贝里出色地翻译了不少诗歌和小说。这些诗人和作家包括敏感的J.P. 雅各布森、颓废而审美的波德莱尔、怀疑论者海涅、古典自然主义者莫泊桑。瑟德尔贝里仿佛按自身的色调挑选了他们。我总觉得那个尖刻而锐利的麦克尔和看似懦弱的阿维德是瑟德尔贝里的两面,麦克尔谈起混乱的意大利局势时说:“我们活在一个好战的时代,兄弟。奸淫,奸淫,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莎士比亚这么说。今日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