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性智慧感应生存哲学 ——读刘亮程长篇新作《本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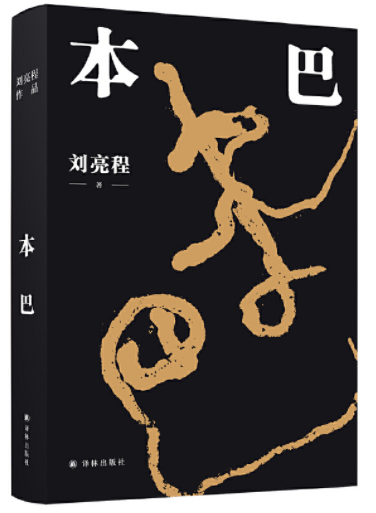
刘亮程的《本巴》承续了不断式微的浪漫主义传统,它同时用诗去思,以小说追问形而上的本有,是当代文坛里稀缺的气质。
刘亮程的长篇新作《本巴》如同诗篇,故事就像哲学。小说不写切近的历史疼痛,而直写蛮荒传说;表面写民族记忆,其实追索人类久远幼年。整部小说的核心,即回返原初,叩问存在,记住本真——赋予个体历史意识,于时间中把握此在。而这本书的探索,也抵达很多作家未曾触及的领域——历史与自然如何同构。
1
小说里英雄史诗《江格尔》的说唱者,也表述了作家的史诗观:“我们祖先曾做过多少堪称伟大的事,都没有进入史诗。东归也一样,那场让十几万人和数百万牲畜死亡的漫长迁徙,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们说起它时还会伤心,会恐惧,会因为那些亲人的流血牺牲感到疼痛。史诗是没有疼痛的。”这是浪漫主义抒情,它以痛苦为代价,赎回了动人心魄的历史诗性。部族丢掉了生命和家当,能留下的只剩史诗。
刘亮程将史诗艺术化入小说故事,实现了叙事的繁复升级。这表现在利用叙事时间的不对等落差,不同标准的时间兑换,造成了文本内的时间集成,与杂糅装置。正如相对论的一种理论感受,时间变形是故事魔力的前提。我们发现类似海德格尔式的“四域”感受,天地人神的共在与持存。这是故事最具冲击的艺术效果,民族史诗天然带有沟通历史、此在的功能气质。汇通人神,将未来变为一种历史,是时空往复的内在性归化。作家把握的是史诗的感官气魄,原始型的浪漫思维,转化为现代性叙事艺术。
混沌不清的意象世界,传说的飘忽,时间的开放,口头流传的随意,反而成就艺术极端自由。那就是无限、未知与混沌。换言之,叙事时间完全靠意象、类比和标记描述。刘亮程发挥口头文学对书面文学的宰治,依旧用模糊性、类比性思维写小说,放弃确定性。同时,小说的往来阔大,更源于作家构建出恢宏的“比例尺”,搭建出符号的帝国:全是一眼万年,一念生死,一瞬枯荣的超量感官,这就是大象无形。历史中的万物刍狗,全成为被摆弄的玩具。小说人物则依赖游戏,符号化生存,他们全成为历史生活的表象与缩拟。
小说的想象力如此蛮荒,具有不可理喻的创造力。可能是少数民族奔放宏大,亲近自然的诗性积淀,给了作家诸多启发。刘亮程完美保有这种原始生态,而故事类型又突破民族的界限。江格尔梦里征战莽古斯(如魏征梦斩),蒙根汗为救江格尔,让儿子洪古尔顶替(如赵氏孤儿)。不愿出生的哈日王,以母亲肚脐为眼为口(如刑天之力)。从原型分析角度看,这些暗合也揭示人类的命运,有跨民族的共通感与化约性。
2
作家强化了两种世界的划分:童年的与成年的,未生的与已生的,清醒的与沉睡的。本质上,这是对存在本身的抗拒怀疑。不生不死,永恒轮回,是故事追求的境地。所以,才有极类似与相对位的人物序列:本巴国有不愿长大的吃奶英雄洪古尔,不愿出生的弟弟赫兰,拉玛汗国就有不愿出生的哈日王。“但是洪古尔知道,只有那个在母亲怀抱的哈日王,清楚洪古尔和赫兰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的目光比谋士策吉看得更远。他不一样的两只眼睛,一只看见清醒,一只看见睡梦。”
可见,只有哈日王用综合、复视与交互的方法,感应世界。这是历史理性的目光。本巴国的最大危机是只愿长醉不复醒,班布来宫的酒宴没完没了,没有能打仗的人。这种关系意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统一,前者是理性照见,后者是梦与醉的迷狂。我们发现,哈日王的太阳属性,本巴国靠做梦杀敌的本事,皆是暗合。换言之,世界的二元划分,无论是童年成年,清醒沉睡,游戏现实,都有待于转接汇通。
它如何实现?只有依赖想象式感应,以诗性构建生存哲学。所以,小说里生命体验,灵肉感知,都用近乎诗句的语言吟唱出来,刘亮程更像游吟诗人。“人无路可走时,影子也是路。”影子是通往梦的道路,做梦是穿梭时空的法宝。小说文本就是做梦者和说梦者的无休止游戏,“这仅仅是一个游戏,我们把《江格尔》史诗中好玩的游戏都搬出来,让游客参与其中,一起玩。”
你会发现类于叙事圈套的重现,那就是从史诗逃逸,冲入现实的冲动。人物如何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对认识论模式造成冲击:“赫兰隐隐听出是在讲他的事。他在哈日王的梦中看见自己转世在东归部族中,做了小江格尔齐。以后的事他便不知道了。他一直担心在那个雪夜说唱史诗的自己,是否走出寒冬活了下来。那位小江格尔齐叫赫兰吧。赫兰说。”赫兰转世为齐,指认自己的故事,大有柏拉图“回想说”意味。
这里的许多人,都起了《江格尔》史诗中的英雄名字。就像理念世界和它照见的影子世界,现实人物成为史诗人物的投影。但小说的设计却凸显出对话精神——一边来自祖先的遥远目光,亘古照拂,一边是子孙的荣耀承续,追慕英雄。“影子会把我们和史诗世界连接在一起。我们相信在影子和黑夜伸去的远方,史诗里的人都真实存在着。”艺术信仰,有时比神学管用。
3
顾颉刚等疑古学派历史学家,向来专注神话传说与信史关系的考辨问题。作为小说家,恰好可以利用这种暧昧,写出具有历史美学的文学作品。《本巴》实现了历史的寓言化,刘亮程超越了重述神话,故事新编的框架意图。正如知名历史作家房龙的《宽容》,用象征的世界重溯人类历史长河。刘亮程意欲表述史诗所包孕的人类困惑——痛苦,残忍与诱惑。这些都指向生存寓言,是关于历史命运的诗性反思。
更重要的是,他用一种游戏精神阐释这种历史生成。游戏可以是命运的终结,也可以是另一历史的开端。生死幻灭此消彼长,全是游戏之轮推动。这在小说层面,也是叙事的板块轮动。我们发现,作家用一种离散、绵延、断裂的空间性,取代了同一的,具有确定起源的线性历史。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永恒的不断生成。我更愿用尼采的精神之轮,看待小说的游戏之轮。从骆驼到狮子最终变婴儿,说明从精神之负重,到精神之“我要”,最后抵达了“我是”。小说用三种游戏,说明历史的逻辑,是具象对抽象的概括。
从搬家家到捉迷藏,再到做梦梦,其实就是回归孩童,复归本源,寻找存在者之存在的尝试。刘亮程深沉“表象了历史”,又使人物去追寻潜藏的历史意志。搬家家就是历史循环论,揭示出治理系统内部不断的内耗,只有闭环的位移,却毫无上升与演进。捉迷藏,则是历史的遮蔽。你找的是哪种历史,是浮出地表的,还是有意深埋的?透明与匿名,是历史的另一属性。
游戏与劳动实践,曾是解释人类创造活动的两大观点。《本巴》暗示游戏有回归童心,遗忘芜杂,欢愉狂欢的一面,更警觉到它的危险,诱惑与麻痹。游戏本就是戏仿,是生活之图示,象征的仪式。人的本质力量需要这种耗费。生活在别处,是人类最大的幻觉。刘亮程不乏对现代性的嘲讽与反思。与祖先相比,我们可怜,玩了他们剩下的,而且还是拙劣模仿。游牧生活变异成如今的旅游生活。“我们刚刚定居下来,过上不再四处游牧的安定日子,别处的人却一群一群地旅游到这里,来寻找我们不久前放弃的游牧生活。”
刘亮程将叙事意图变得非常繁复,在这种宏大史诗气质下,是神话思维,是口头传说的肆无忌惮,是寓言的劝谕与生存哲学。《本巴》的深度建立在玄虚至极的时空体验里,故事中一切空间都是时间化的,以年数来表述距离,位置和空间。小说的时空体艺术,被发挥到极致。然而,作家的终极追求,却是活在时间之外。超出三界,不在五行,大约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极限,艺术为一个可能的世界立法,而这种可能性建立于读者的信仰之上。
在当下文坛,不少作家在写“疑似现实主义”,陷入自我悖谬的境地——看似现实,反而失实,因为既虚了美,又隐了恶,那是“戴上头套的现实主义”。《本巴》承续了不断式微的浪漫主义传统,它同时用诗去思,以小说追问形而上的本有,是当代文坛里稀缺的气质。刘亮程像一位“大地作家”,能把故事放在大地上,成为自然物。换言之,他于自然的视角,去求历史意志、求人类生存的真经,乃是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