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笔下女性的家庭角色断裂与情感置换:风暴眼的沉默
近几年,女性的生存地位不断地被进行讨论和书写,在职场上,大部分女性受到性别歧视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也有诸多职业女性为此发声,强调在事业上的男女平等。但很显然,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地位仍然被剥削和捆缚,而可怕的是,在这一点上,女性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甚至就连女性本身都很难意识到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也正是因此,女性在无意识中被灌输的男权社会理念才更加尖锐和苛刻。
与今天职场中强调的男女平等不同,在家庭角色定位中,女性天然地被赋予了所谓“避风港”的角色,事实上,这种看似温和的比喻却是对女性独立想象的摧残。在这些传统的角色赋予乃至家庭定位上,女性的形象实际上是被扭曲了,这些情感的捆缚也充当了男权社会下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延续了男权支配欲望的观念。

电影《82年的金智英》海报
2019年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实际上就对于这种女性长期被忽略和驯化的家庭地位提出了尖锐的探讨。家庭生活的牢笼特性被从未有过的显现,而电影中女性对于女性被无意识的压榨和剥削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事实上,同样的关怀在张惠雯的小说中也早有显现。
在家庭生活的书写中,她展示了一种隔绝的荒芜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缓慢而遮蔽,往往将自我构筑成了扭曲空间下的诡秘泡影,在个体的场域中自我奔逃,但在自我空间之外,却少有人能够注意到她们的情感焦虑,这也就提出了对于今天家庭生活中女性的身份地位思考。
一、家庭生活中所覆盖的牢笼属性
在家庭的内部空间中,女性往往被迫分置于封闭的狭小角落内,例如厨房、卧室等需要她们劳作的地方,在大部分时候,女性在家庭中承载着屈从地位,也就是不得不投身于烦琐的布局工作之中,同时,这些单调的劳作使得女性与外界隔绝,也就导致了她们不得不顺从于琐碎无序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自我压抑。
事实上,在家庭空间的角度上来说,女性在这一封闭空间内所奔波逃避的是男权社会的打击和压制,女性不得不从属于这种压制,并且成为男性财产的一部分,与世隔绝地归属于她们的配偶。关于父权和夫权的状态其实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有展示和书写,因此,张惠雯也提出了一重全新的思考,那就是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所面对的自我妥协。
在父权制社会秩序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是被不断内置和同化的,这也是张惠雯小说中所希望谈论的问题,很显然,在今天,我们很难再直观地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状况,但实际上,性别歧视无所不在,性别的固化观念也存在于家庭和职场生活中。
以小说《沉默的母亲》[1] 来谈,实际上,这是一部带有强烈的东、西方糅合文化的作品,一个嫁到美国的中国女性,带有亚洲文化中一切所谓的女性“优良品质”,她贤惠、顾家,同时不爱慕虚荣,这在任何一个男权社会下都被认为是妻子的最佳人选,也正是因此,沃克先生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娶了这个女人。
作为旁观者来审视这段婚姻不难看出其畸形与可笑,沃克先生作为丈夫和父亲,也就是这个家庭中的绝对掌权者,他身上带有强烈的自私自利色彩,他一面拿对中国妻子的要求——贤惠、保守、顾家、生养孩子等,来要求自己的妻子,一面又不肯付出中国家庭中常见的丈夫所需要负担的,他计较每一份支出,同时不肯支付婚宴的钱,也不肯让父母住入家中。
很显然,这些捆缚和压制在生活中都慢慢积聚成为了沃克太太的生活日常,然而,当父亲生病,她希望从丈夫手中拿到一些钱时,她却面临从未有过的苛刻,丈夫举出了一个又一个例子来拒绝拿出这笔钱,而长期在牢笼中生活而不自知的沃克太太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生活的真相。
生活的真相仿佛一瞬间在她面前揭开了,那就是,她没有自己的一分钱!而在这背后的更深层的真相是:在这个家里,她没有任何决定权,这里的什么都不属于她,她在这里的意义就是生养一个又一个孩子!她一夜之间变得心如死灰。
同样被生活的牢笼所扣住的女性还有《二人世界》[2] 中的“她”,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给这些角色以命名,似乎也在暗示着,这种生活是同样地铺排在大部分女性的日常之中。事实上,小说中的“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并不算是一个传统的母亲或是妻子形象,“她”不确定对孩子的爱,“她”无法做到对孩子全然付出,但又对丈夫的“不成熟”而感到愠怒,更与普通的父权文化不相符的是,“她”有一个情人。但小说也正是通过这个情人来展现出“她”在婚姻生活中的困顿和闭塞。
小说多次地提到了女性和男性面对新生生命的不同,对于“她”来说,她必须经历生活被男孩和家务填满,必须经历时时刻刻的苦恼和琐事,孩子挤占了她所有的空间,无论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在这些麻木而琐碎的事件里,她不再具有整块的时间,必须习惯妥协于乏味的生活状况。
但对于丈夫来说,他“始终如一。他是始终欢迎孩子到来的那个人”。他既意识不到妻子的改变,也不能够做出有效的疏导。
女性在退居家庭生活之后,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状况的流失,更是与外界的完全脱节,同时也是自己人生的琐碎与游离,因此,当小说中的“她”开始拒绝情人的看望,以及“不再从他的电话里得到快乐和甜蜜”时,她所面对的就是被改变的断裂。
在小说的最后,她不再能够从肉体的快乐中得到快乐,即便是在床上,也一次又一次想起儿子,同时,她也赌气似的向情人展示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凌乱、邋遢、“怀着一种自毁的、夹杂着报复的快意想象他看见自己这副模样的反应”。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她”已然进入了家庭的囚笼之中。

在生命个体的幽闭空间之下,生活是缓慢的、空间是逼仄的,与世隔绝的痛感不仅令女性和社会生活脱节,就连和枕边人乃至家庭生活中的其他人也产生了割裂,深刻象征着被遮蔽的捆缚与囚笼。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家庭生活的牢笼属性也就是在此,从东方的儒家思想来说,“女主内”的思想深远地影响着家庭关系,在父权制的社会原则下,女性必须站在伦理角度中,以照顾家庭、服从人伦感情等来退居到生活的后方。
二、女性向内坍塌与向外断裂
沉默的囚笼过后,我们所需要探讨的就是女性与外界隔离过后的缠绕与奔逃。当女性在社会秩序与日常的生活秩序中产生龃龉之时,即便是沉默,也会有爆发和崩塌的可能。事实上,张惠雯在她的女性题材小说中往往会谈到女性在婚姻中的逃离。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很难从家庭生活中得到关心或者是尊重,只有男性无休止的冷漠和压迫,因此,面对这种日复一日的痛苦,女性只能选择逃离和反叛。
很显然,尤其以东方社会秩序来看,男权社会驯化女性的一个核心就是婚姻家庭中的训诫,而在女性被迫退让到家庭中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社会角色被绑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假设为隐蔽的奴性身份。一方面,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不需要对女性的付出表达感谢,所有在家庭中的付出都显得理所应当;而另一方面,女性却需要对男性带回来的钱财表示感谢,作为谋生者所存在的男性看起来具备了比女性更高的社会价值,女性的价值自然被忽略了。
当两性关系被放置到家庭生活中时,还往往会出现一个婆婆的角色,事实上,这一角色代表着女性在父权制统治秩序中的纵向核心,在传统观念下,“多年媳妇熬成婆”,这一句就可以看出女性在传统思想下的绝对附庸。即便“婆婆”的身份使得女性在老年时期具有了崇高的权力,但这一权力仍然是附庸于男性,同时也是指向了“儿子”,来作为“帮凶”压榨儿媳。
在中国传统婚姻的缔结中,亲子关系里的人们重视人伦,因此,女性对儿子的情感投射也就伴随了对于儿媳的打压和排挤,她们要求儿媳的绝对服从,同时也作为性别统治者的“帮凶”,强行把女性拉扯回到家庭生活之中,通过这种单向度的性别统治和年龄优势,来试图满足自己的情感以及权力需要。
因此,被压榨的悲剧女性为了逃离这种囚笼的境况,一部分选择了自我向内的坍塌,一部分则选择了向外的断裂。从小说《沉默的母亲》来看,小说中的沃克太太就是典型的自我坍塌者,当她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真相”之后,在表面上,她仍然维持着得体和贤惠,照常做家务,但同时,当着丈夫的面她食不下咽。但当丈夫走后,“她像只老鼠一样把去超市采购时顺便买来的各种廉价零食藏在车库里的那些空箱子里,然后在孩子们睡着,或是看电视,或是在楼上玩儿的任何时机里拿出来,像个得了吞咽强迫症的人一样贪婪地往嘴里塞着薯片、士力架、彩色软糖、奶油曲奇饼……”
而在之后女儿的叙述中,母亲在躁郁症的心理疾病中走向了自我毁灭。她是一个沉默的少言寡语的顺从者,她的可怜之处不仅在于她受到了所谓“贤良淑德”思想的荼毒,更在于她的无力抗争。事实上,她的抗争都只能从自我的毁灭中展示悲剧。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场梦没有醒,沃克太太将永远是沃克先生沉默的、顺从的妻子,但不幸的是,父亲的生病以及沃克先生的冷漠将她飞快地从梦中醒了过来,她的不幸之处也在于此,她被操控了一生,但残酷逼仄的社会现实也令她无法真正选择觉醒,她能够用以反抗的也只有生命,这正是她对于男权社会最为激烈却也最为惨淡的反抗。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生病的这一情节构建大约也是经过了作者的思考,女性从父权文化中逃离,则被迫卷入夫权之中,而她的觉醒,也实际上是父权与夫权倾轧下的自我折磨。
而在小说《玫瑰玫瑰》[3] 中,作者则书写了另一种向外的找寻与断裂。岛屿上的女主人盛情邀请“我”去她家中做客,但当“我”抵达这座岛屿,又接触了她的生活之后,“我”才了解到看似广袤空间下的逼仄与痛苦。
无性婚姻所造成的是一个女人在压抑欲望之下的崩塌与恐惧,如果说《二人世界》《沉默的母亲》等所讲述的都是女性在亲子关系中所遭遇的情感勒索,那么,《玫瑰玫瑰》[3] 则展示了配偶关系中的情绪匮乏。小说所借用的是无性婚姻中的复杂况味,有效书写了女性在这种压抑与自闭下的自我否认。
在“我”的眼光中来看,这对夫妻是天生一对、是互相支持且相爱的,但婚姻之下,各自的痛苦就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了解,一方面,性爱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即代表着情感的缺失和孤立,女性无法从亲密关系中获得真实的温暖;另一方面,在东亚文化的影响中,女性也必须压抑自己的性欲望,因此,女主人只能选择向“我”说出一切,即便是在自我处境全面坍塌的时刻,她也只能进行断裂的输出,而非全然自我的找寻。全然锋利的向外断裂之下,小说呈现出了女性在孤独时刻的静默与错位,无法在家庭亲密关系中获得温情的当下,小说缔结出了更为丰满的情绪张力。
同样的情感勒索还出现在了小说《雪从南方来》[4] 中,在此,家庭仍然作为了风暴的中心,而有所不同的是,小说选取了男性作为风暴眼,来回望两个女性的挣扎和失落。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离异的带着小女儿的单身男人,在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之后试图让爱人和女儿和平共处,但却在年幼女儿的无知之恶下,失去了重新开始的可能。

事实上,这类故事的核心并不鲜见,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矛盾向来是东方家庭中经久不衰的书写主题,然而,小说却以一封邮件起始,试图展示这对父女在长久的平静生活下的暗流涌动与风暴迭起,柔弱的女儿是曾经亲手毁掉他爱情的刽子手,而被他误解的徐宁也永远没有了回来的可能。
另一面,徐宁的角色也值得被关注,在小说中,她实际上是一个温厚的继母形象,即便是面对他没来由的指责和失控,以及小敏混沌的欺骗假装之下,她所选择的也是断然离开:
“不用回答,什么都不用说!”她站起来说,拿一张纸巾擦掉脸上的泪,样子像是如释重负,“我应该早就明白的。我应该早就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在徐宁的世界中,她的如释重负何尝不是一种向外的断裂,被主观投射的继母形象固然带有陌生环境下先入为主的标签,同时,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及时奔逃也引出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逃离是绝对支配过后的具象挣扎,也避免了她们成为家庭生活中的献祭物品。
三、“心血来潮”下的女性自我博弈
作为移民作家,我们常常会谈论到张惠雯在其小说中所显现的关于差异文化的认同感与身份意识,实际上,在其现实性的小说中,人物大多弥漫着一种困顿的身份焦虑。这也是小说叙述的核心之所在,而这种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是对于生存困境的讨论和情感的捕捉,尤其以女性身份来谈,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身份焦虑,她们有着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同时,却也具备对于未知远方的向往。
在这种欲望的割裂之下,小说呈现出对于移民生活的隐喻性写照,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时常是双重的困境。从家庭生活上来看,在张惠雯的小说中,大部分女性的移民大多与配偶有关,因此,她们的奔赴实际上是从原生家庭中离开,去往另一个地方重建家园,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生命际遇的漂泊和游荡。同时,她们也需要面对常规的灵魂的漂泊和探索,在生活之中,她们的生命历程是真实而又隐蔽的,小说关注了女性的内心情感,将她们无根的茫然加以深刻的书写和展示。
在前文中我们讲述了关于女性意识在家庭生活中的被囚禁状况,实际上,家庭的囚笼化深层次的是对于夫权乃至男权思想的反抗,而在张惠雯另外几部小说中,她则剔除了这种对于抵抗或者是直观的交锋,而是在凝视的角度下,体现女性主义的博弈与追求。这种凝视往往来自女性在亲密关系之外所开拓的另一重情感,作为情人或者“红颜知己”的她们,在这种关系中开辟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另一面,也正是从这种看似错误的遗憾感情中,小说将女性的觉醒意识推到了高潮。
从小说《关于南京的记忆》[5] 来谈,第一人称“我”的情感是复杂而动荡的。张惠雯巧妙地借用了移民的身份,来展示女性的双重情感困境。一方面,“我”习惯了和男友的生活,也不准备对这种生活加以改变,但“他”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局面,同时,“我”的这种小小的精神出轨,也使得“我”对自我情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这可以看作是女性在长久恒定亲密关系中的一段小小的“心血来潮”。而事实上,这种“心血来潮”并非情感的流失,而可以看作是女性对于婚姻乃至爱情的旁观和浮靡,对于“我”来说,这种“不同寻常的友情”是女性决绝后的身份找寻,被纠正的错误在多年之后令人神伤,也正是出于某种不可追的怀恋。
早在柯莱特的小说《面具后的女人》[6] 中,就有对这种“心血来潮”的描绘:“她会像丢弃葡萄皮儿一样松开那年轻人的嘴唇,然后离开,到处晃悠,和遇到的其他人亲昵,再忘掉他们,直到疲惫后回到家,品味她源自决绝个性里的独立、自由和率真,品味作为陌生人的那种寂寥空虚而又毫无羞愧的、怪异的愉悦——就像这次百无聊赖之下单纯的外遇里,一个小小的面具和奇怪的装扮让她品味到的那样。”
这种感慨的情绪积聚而成的是对于男性力量的解构,这种解构无关所谓的叛逆或是觉醒,更多的是对于自我成长的救赎,是一个不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自我成长。在《关于南京的记忆》中,“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成熟回望的视角,小说不再具备感情上的取舍,同时也没有任何不合乎伦理道德的因素,正相反,小说全篇都在对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进行深刻的书写,这一角色具备女性的隐忍,同时也有着对于自身欲望的关注。
而很显然,从小说的题目就可以看得出,以人到中年的回望来看,“我”的怅然若失实际上也是对“我”情感关系的怀恋和追溯,在移民过后,“我”的身份认同是缺失的,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在海外的生活经历,都使得“我”失去了生命力的涌动,也正是因此,“我”对于男人的怀念,也可以看作是对“南京”,也就是对那一段生活的怀念。小说利用了这种情绪上的复杂情感,来表现一个女性无声的悲痛和挣扎。
在社会语境下,女性的欲望时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因此,女性在回望时刻的撕扯实际上也是对于“本我”的否定,对“超我”的追寻,小说中的“我”,无论自我生活如何平淡,始终都怀有对理想他者的渴望和筹谋,对于那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心血来潮”,多年的生活已然将这一小小的精神出轨加以篡改,也就构成了对于超我理想的追寻。
很显然,在社会处境下,女性的形象往往逃不脱妻子或是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或者说情感关系下,女性的独立意识是被隐匿的,也正是因此,张惠雯提出了她全新的思考。在她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女性在自我情感关系上的找寻,看似背德的情感书写所烘托的是鲜明而确切的女性力量,事实上,她们也通过情感关系的觉醒来塑造自我的独立意识和身份认同。
四、情欲符号中的具象隐喻
无论女性主义文学如何阐释和变更,无论女性的社会身份认同如何找寻,实际上,对于女性主义的话题书写永远逃不开对于身体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由于天然的生理因素,女性在性生活中常常被强行冠以被支配的地位,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也就来源于此,再加上金钱与性关系的交换,更使得女性成为了从属地位,不具备被平等对待的价值。
但今天的女性主义文学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对于女性特权的强调,同时,女性对自我的身体控制权也有了全新的认知和理解,女性不再从属于男性获得性快感和性价值,正相反,女性成了主导地位,在反抗的随意掌控中消解了情欲附属,完成了对自我性别的认同和书写。
从小说《双份儿》[7] 来谈,和《关于南京的记忆》相似,小说同样都是以中年人的视角回望年轻时所经历的一段情感,也同样都对这一未发生的情愫抱有怅然若失。但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不同也就从此显现。
在小说《关于南京的记忆》中,“我”是平等地与“他”交流,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友情”,但也到此为止了,而也是因为这个人,“我”时至今日仍然对南京有着好感。但在小说《双份儿》中,“我”作为男性的回忆却是灰暗的、沉重的。对于“我”来说,那个女人的形象带有更为复杂的情绪。
小说将这个女性设置成了一个“高级妓女”的形象,对于初入生意场上的“我”来说,能够保持在淤泥之中不沾染泥土已然是需要很大力量,因此,对于妓女的解救所构建的也是一个具象的身份象征。女人的身体所构筑的是一个圣洁的、代表了强烈的权力空间。一方面,身体是这个女人所存在的本钱,也是她能够获得利益交换的来由;但另一方面,她也会利用自己的智慧,来赚取“双份儿”钱。在“我”劝告她从良,希望她能够拥有正常生活时,她转头就向更高级告密。这种对于妓女的身体失控的隐喻,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在情欲和利益之下的全面溃败。
事实上,在小说的最后,“我”已然发现,“我”早已成为了那个“我”曾经所看不起或者说看不懂的女人:
“他有时会突然陷入那种阴沉的情绪之中,仿佛被浓雾笼罩……而他仍然得在那些日复一日的琐碎、没有意义的事务里消磨着余留的暗淡的有生之年……在他这个年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激动地、匆忙地赶路,除了去捕捉、占有、体会那一点点快乐,但这快乐又转瞬消散,之后就把他抛掷在漫长的荫翳之中。他想,他也有他的“双份儿”,他明知卑劣、罪孽却始终舍弃不了的东西。”
正是由此,一个拯救者转换为了捕捉者,小说不仅将女性身体卷入到政治中,更是借助了巨大的颠覆性力量,来对权力的结构进行反转和讽喻。拿了“双份儿”的女性看似是从属地位,但却具备了对于那时的“我”的支配权,而后来在漫长的荫翳中自我消解的“我”,也无法回归到天真的状态,只能塑造一个虚幻的欲望形态,自我沉沦到权力关系之中,来书写永恒的话语霸权,以及叙述者对于风暴眼中心的某种批判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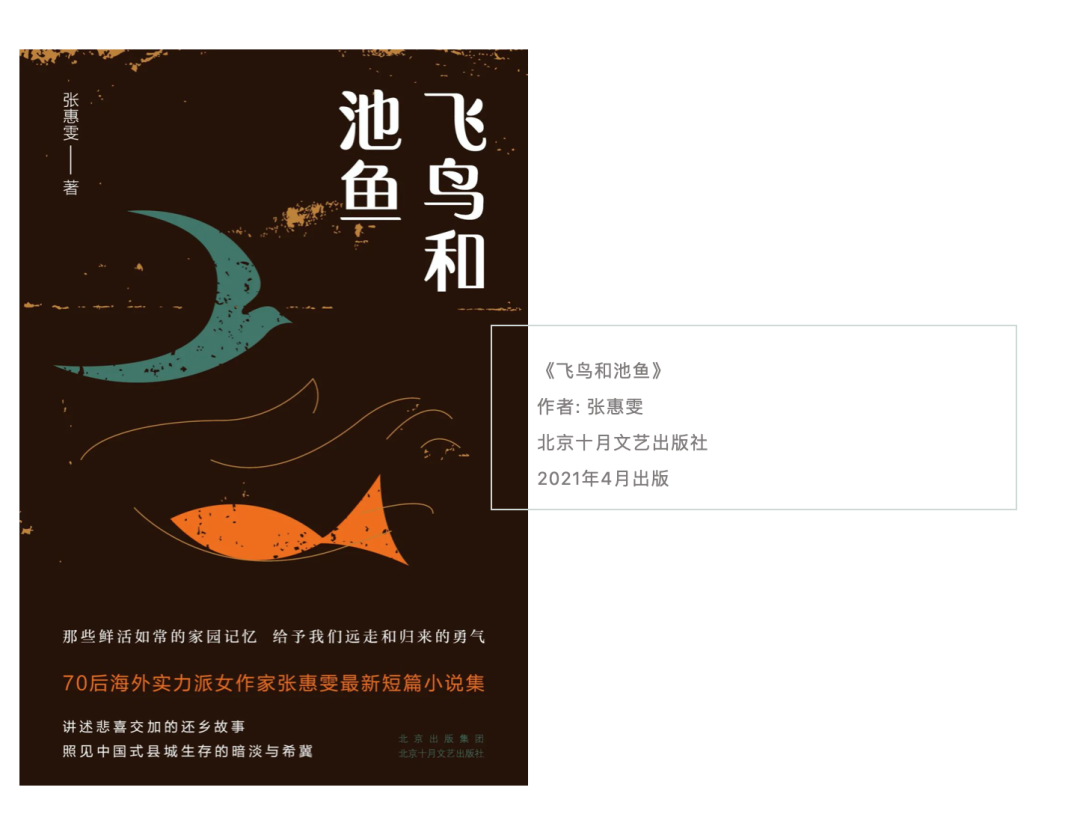
作为移民作家,张惠雯的作品往往能够超越单一的国度,对东方视角下的西方场域进行更加强烈的显现,而在小说所重置的情感困境之下,作家通过女性的自我价值找寻与家庭身份的割裂来完成对于精神捆缚困境的书写,这种情感张力之下,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同时,也能够穿透到现实世界之中,勾连出非常态空间之下的崩裂与坍塌。
[1] 张惠雯:《沉默的母亲》,《江南》,2018年,第5期。
[2] 张惠雯:《二人世界》,《收获》,2019年,第2期。
[3] 张惠雯:《玫瑰玫瑰》,《收获》,2020年,第3期。
[4] 张惠雯:《雪从南方来》,《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
[5] 张惠雯:《关于南京的记忆》,《花城》,2020年,第6期。
[6] [法]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面具后的女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7] 张惠雯:《双份儿》,《上海文学》,2019年,第5期。
原文刊发于《粤海风》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