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弗兰纳根:他以一己之力为塔斯马尼亚提供了声音
澳大利亚的南端有一座叫做塔斯马尼亚的岛屿,距澳大利亚最近的陆地还有一百公里,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出生于这里。在塔斯曼尼亚土地上居住生活的,要么是流放犯的后代,要么是原住民的后代,弗兰纳根的家乡在一个采矿小镇上,镇子在一大片古老的热带雨林中间,镇上大概有八百人。

如此强调弗兰纳根的出生地,因为这是一个远离世人之地,讲述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一个旅行者到流放地参观行刑表演,这里有一台杀人机器,执行刑罚的军官带领旅行者参观对一个士兵的行刑表演时,这个本来的执法者却用杀人机器亲手杀死了自己。当看到这本书时,弗兰纳根不禁想起了从小到大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这里同样是流放之地,流放犯和原住民的后代经历了种种苦难而深受影响,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会描写塔斯马尼亚的生活,没有人去描写他们生活中的悲与喜,起与伏。于是,弗兰纳根决定为塔斯马尼亚提供一种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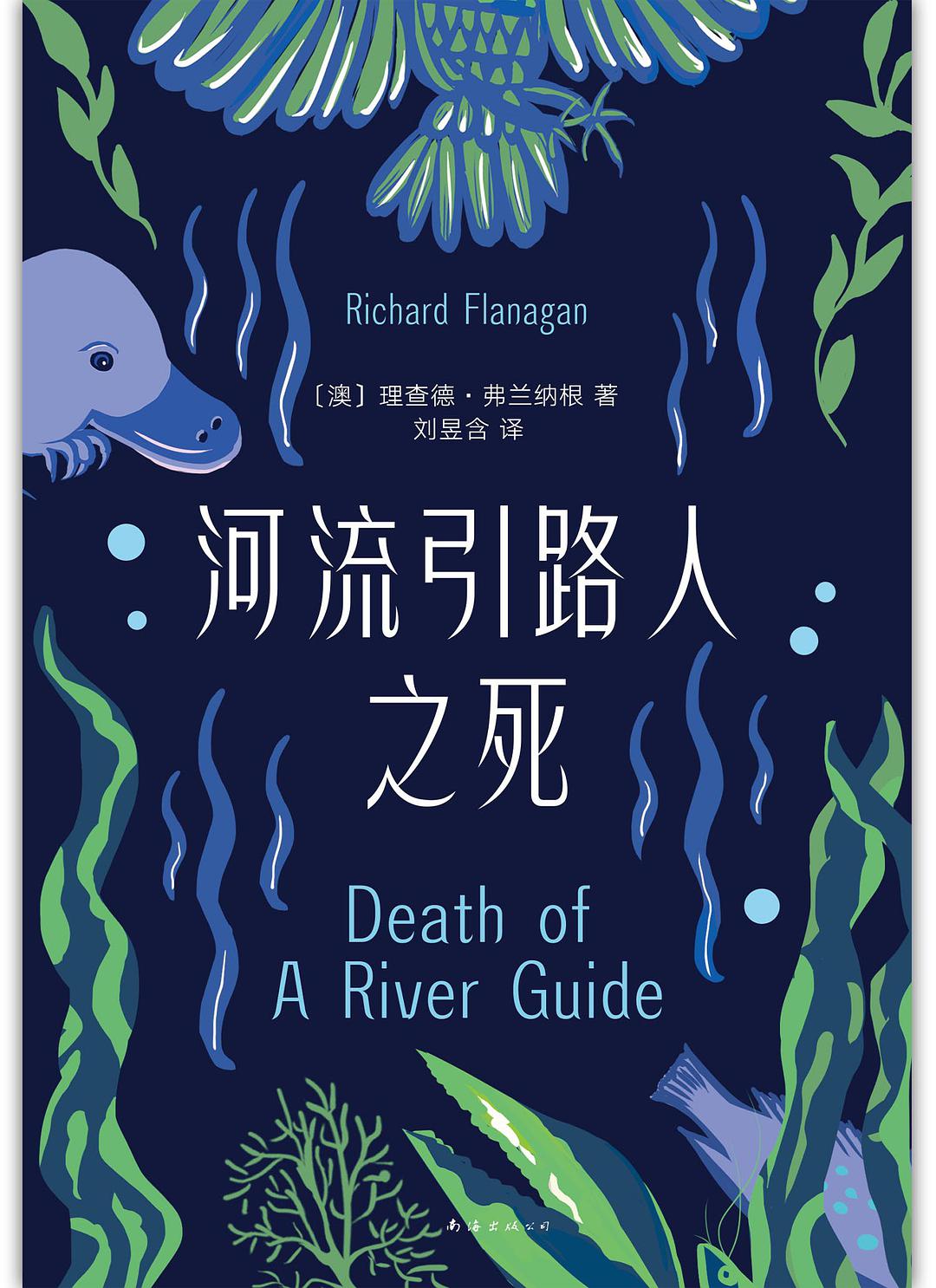
1994年,弗兰纳根写下了处女作、长篇小说《河流引路人之死》,16岁时他辍学回家当了一名河道导航员,小说正是以这段经历为背景,描绘一位河流引路人在塔斯马尼亚富兰克林河里的激流中船只倾覆、溺水而亡的故事。溺水的弥留之际,记忆随着湍急的水流旋转,生出层叠幻象,在河流引路人眼前汇成无数斑斓的漩涡,视线沿一圈圈扩散的水波望去,他看到了他、他的父母、这片土地上他所有的族人活过的生命。透过河流引路人的眼睛,讲述了塔斯马尼亚作为流放之地的悲惨历史,殖民主义者对大自然和塔斯马尼亚岛原住民残酷的践踏蹂躏。如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所言,“透过主人公意识扩张与收缩的棱镜,弗兰纳根把个体的私人故事与其祖辈传承、与塔斯马尼亚的神话历史紧密绑缚。”近日,弗兰纳根的这部处女作由新经典引进出版,这也成为《深入北方的小路》后他被引进国内的第二部小说。
事实上,弗兰纳根的祖父母并不识字,只有父亲是家里唯一接受过非常基础的学校教育的人。父亲对文字的美感和魔力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在他看来,人如果有机会接触到文字,会是多么自由和超然,人可以用它来窥测宇宙。这让弗兰纳根幼年时就有了“当作家”的想法,“那些世代识文断字的人可能已经失去对这种自由、超然之力的感触,但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它。文字对我来说就像一张魔毯,把我从这座小岛上带到了远方。”
弗兰纳根欣赏威廉·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在于这些作家给予了他写作上很深的影响。在谈及卡夫卡时,他说卡夫卡给了他一种写作的启示,“有时候你要揭露现实的时候,未必需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有时候用非现实的角度来写,其实能更深刻地揭露现实。”由此不难理解,在《河流引路人之死》中,弗兰纳根为何将故事以一个溺亡者的视角展开,整部小说也像是一个语言万花筒,梦幻、故事、传统、历史在这里逐次呈现,魔幻而又现实。
而对于福克纳,弗兰纳根认为,他给自己最大的震动是他对于那些小人物的描写,“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些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都展示了非常丰富的内心以及复杂的情绪,都保留了尊严。”同时,福克纳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南方人,福克纳来自密西西比,当时在美国也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地区。所以当我读到和我有类似背景的福克纳的作品的时,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像他一样描述我的生活。”而福克纳描写人物内心活动、人物语言对白时呈现出的一种诗歌的韵律感,这种韵律感又写得不那么刻意,和我们生活中的语言也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也让弗兰纳根对于自己小说的语言更为斟酌,他善于深思、审慎、精确的风格在他的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叙述的分寸和节奏的把握上尤为显著。
2018年,弗兰纳根来中国参加第十一届澳大利亚文学周,曾与作家余华展开一次对谈,围绕的是他获得布克奖的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说以泰、缅交界处的死亡铁路为背景,以弗兰纳根父亲的经历为原型,双线讲述身为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白天竭力营救手下的士兵,晚上独自一人时追忆生命中唯一一次爱情。战争过去,他却再也不会与人分享,也不懂如何去爱。布克奖颁奖词说,“文学的两大主题是爱与战争,《深入北方的小路》正是这样一部关于爱与战争的巨著。弗兰纳根用其优雅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充斥着罪恶和英雄主义的故事,将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相连。”
余华则细述了这部小说的好处,“主要人物都在第一章的回想或者是那种恍恍惚惚的回忆里出现,读第二章以后,这个故事一下子打开了……读完以后,又重新回来读第一章,我觉得第一章就是他一直想打开的这个小说的门,作为一个作者,他要打开一个长幅,看看他的路通往什么地方。”而在第三章中,弗兰纳根写澳大利亚的故事,描述修死亡铁路中饥饿、疾病、瘟疫流传等各种各样生活,“从弗兰纳根选择写什么,他怎么又把那些东西表现出来,你就知道那个家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这与弗兰纳根的自述可以做一番对照,“在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以为写东西必须要有很好的写作技巧,要有非常高深的写作功力。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在写作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任何成功的作家,他们是通过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作品传达出了他们的内心。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很多作家并不能真正地以他们的手写他们的心。每一个作家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试图探索怎样真正呈现他们的心声。”
英国文化协会曾如此形容弗兰纳根:“弗兰纳根的作品是对塔斯马尼亚、对口述传统故事的赞歌;是对常常被故意忽视的、失落过去的爱意再现;是庆祝,是安魂曲,是对诸多沉默的愤怒;它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就对澳大利亚知之甚少的人来说,是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自《河流引路人之死》起,他就书写出塔斯马尼亚的泥土、气味、炎热和血液,书写那些被席卷而去的无名者、那些看似要被压垮的、默然不语的人,书写他们的尊严和意义。如余华所言,“弗兰纳根已经是当今在世作家中杰出的一位,他写下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故事,他家乡的故事,已经在当代世界文学里占有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