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平原烈火》:一部不可复制的抗战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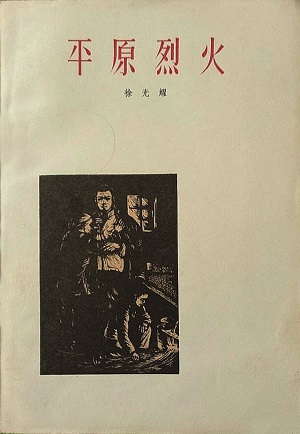
1949年11月27日,24岁的徐光耀在天津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抗战小说《平原烈火》。《人民文学》当时节选发表时,编辑们将其称为工农兵创作的第一座“纪念碑”。到了1951年3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文学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便是这《平原烈火》。四个“第一”,标示出《平原烈火》在1949年这个“红色经典出版元年”的特殊意义。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史在对“红色经典”的描述中,《平原烈火》很少被提及。甚至1959年10月推出的一套“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丛书中,《铜墙铁壁》《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1954年左右出版的著作都位列其中,还是不见《平原烈火》的踪影。文学史对《平原烈火》的这一“遗漏”,近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引起对新中国文学价值建构的反思。
探究1949年的文学史现场,《平原烈火》的“被遗漏”似乎有三个缘由更为突出。一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战争文学,主要以硝烟未尽的解放战争为主,抗日小说的数量不多。这与创作者对解放战争的充盈记忆和澎湃激情有关,更与新中国文学此时正在着力塑造的目标有关。毕竟,无论是涉及战争全局的《保卫延安》,还是局部战场上的《红日》,都更容易将党的领导力、军民生死与共的战斗精神进行极致性的书写,其主旋律更突出鲜明,也更能突出“为工农兵”的文学方向。《平原枪声》《荷花淀》以及《敌后武工队》等抗日作品则集中于敌后的游击战争,党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类抗战小说显然还不够支撑。第二,“改编”是文学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无论是《新儿女英雄传》还是《吕梁英雄传》等均采取了章回体的叙述形式,这一文学形式最能为大众广泛接受,是表现英雄传奇、戏剧性冲突的恰当载体,也最容易快速塑造新中国的文学范式。年轻的徐光耀没有选择章回体的形式,而以现代叙述将生死体验倾泻出来,尤其是将八路军一支小部队从低谷到奋起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对象,其戏剧性、传奇性难比两部“英雄传”。第三,恐怕与文学评价的时代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太需要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理念也被奉为圭臬,《平原烈火》也有金刚似的英雄周铁汉,但战火中走出来的徐光耀为我们敞开的文本内容,实际上并不以人物为重。
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十七年乃至后来一段时间,抗战小说都比较少见。但必须承认,作品的背后其实是宽容、解放的观念。一旦抗战历史观放置到全民族的视野下被成功塑型,《历史的天空》《亮剑》《百团大战》《长沙保卫战》《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开始取得突破。即便如此,相对《大决战》《开国大典》等表现解放战争的剧目,反映中华民族浴血14年抗战的全景式扛鼎之作至今仍是缺憾,反倒是被缺乏基本史实的“抗日神剧”搅乱。在这“大制作缺乏”和“神剧丛生”的尴尬之中,70年前处于“红色经典元年”的《平原烈火》反倒显示出填补性的价值。简单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复制的抗战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样貌反映了八路军抗战的历史真实,其真实性非亲历者难以虚构,而对于基层民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胜恐惧中成就英雄的描绘,既朴素天然又引起后人真正的尊重。
《平原烈火》开篇以白描方式展示了一幅日军扫荡下冀中抗日平原“地狱”般的全景。“一九四二年五月……冈村宁次坐上飞机,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扫荡’,残酷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红火。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金黄的麦子轧烂在地上,骑兵包围了村庄,村庄烧起来,熊熊的火苗把黑烟卷上天去。步兵们端着刺刀,到处追着、赶着,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又从西村追到东村。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枪响,遍地女人哭孩子叫……”这幅极具画面感的描写,岂是“神剧”编造者所能想象。对于徐光耀这个刚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作家来说,创作是将真实的体验转化成“文字上的战争”。书写之时,他将“先烈王先臣司令员的遗像挂在墙上,使之正对书桌,一抬头,便见他的微笑”;“一大堆烈士尸体的形象”自动在记忆中“涌过来、荡过去”;“书不是我写的,而是烈士用自己的血肉写成的”。亲身参加的100多场战斗是他创作的现实主义基础,文字上的一切成了战斗的“原景重现”。仅此一点,《平原烈火》便可成为今日抗战作品“取景”“临摹”的珍稀资源。
在习惯塑造传奇英雄形象的新中国战争小说群体面前,《平原烈火》又显另类。小说中的主角周铁汉有作者在那一时代塑造革命英雄的努力,意志坚定、英勇献身,但丁玲直接指出“有点概念化”;反倒是作为配角的大队长钱万里有更深的内涵,即便危急时刻依然沉稳,破解困局时的现场查勘、反复推演,对决策失败时的沉痛自责以及危急时刻的睿智果敢,寥寥数笔,即让这一基层指战员的形象神韵毕现。
其实,相对章回体对传奇英雄形象的着力塑造,《平原烈火》的笔触主要在一支小部队生死起伏的成长过程。这是冀中抗日分区下辖规模不能再小的一个大队,突破日军封锁线后由100多人剩下仅仅37人。他们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日军又以碉堡、公路、机动巡逻和遍地的“皇协军”、汉奸便衣、反水的地主控制了乡村;死亡的危机在百姓中弥漫,群众与之隔绝,这群农民战士几乎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沮丧、恐惧等低落的士气在全书开篇扑面而来……小部队将求生存放在第一位,先是化整为零、化到三四人最小的单元,岂料竟被敌人零碎歼灭。低谷之际,他们主动求变,侦察敌情,集中出击,敲掉首恶,以小小的胜利一点点重振士气。在此过程,你发现民间的智慧在战斗中一点点激发出来,他们无师自通,除便衣、巧袭击,发动攻心战,分化伪军、孤立碉堡……战斗的烈火再次燃烧,冀中大地重新成为他们来去自由的海洋,最终配合八路军发起了反攻。
《平原烈火》紧紧围绕“战斗”而写,成了冀中平原党领导下一群农民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智慧自发生长、各式战斗方式如古老的器具一样琳琅满目的集合体,更是这群农民军在突围、失败、低谷、爬升、再挫折、再爬升、终于汇合为军民战斗洪流的成长史。如果把战争本身视为一个生命体,《平原枪声》则是对这个生命体银钩铁画、具体而微的书写。
1950年代的评论者希望徐光耀将《平原烈火》写成三部曲,塑造出周铁汉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农业化的代表性形象。徐光耀终未成笔。也许反倒是幸运。确实,文学既需要史诗般的英雄形象,也需要为后人将战争中积聚的情感、潜藏的技巧智慧以及战场的“原生态”一一敞开。《平原烈火》之所以不可复制,恰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