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衎:一个青年作家的“超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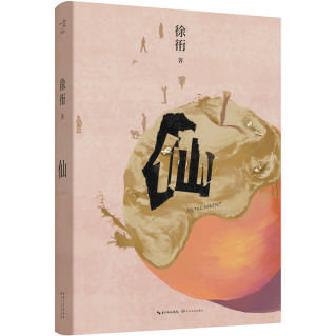
《仙》徐衎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徐衎
尽管以前有过长篇作品的正式出版,但对青年作家徐衎来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仙》的出版,才更像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他生于1989年,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获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但一直到2015年的中篇小说《肉林执》,他才觉得,仿佛成熟了。《肉林执》发表在《收获》杂志60年纪念专刊上,和莫言、冯骥才、黄永玉等人的作品同时刊出,一鸣惊人。《仙》中收录的,正是包括《肉林执》在内的这时期前后的七篇中短篇作品。
不合一般中短篇集的命名规则,《仙》中并没有一篇叫做“仙”的同名作品。其实原本是有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收入,更名已来不及,于是阴差阳错成了徐衎所说的“一张没有同名主打歌的专辑”。但他细细一想,“仙”作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隐喻,倒也恰当:书中的人都是生活在小城里的小人物,领受着自己的一份微细的命运,却“不妨碍他们在某个层面上有飞升超脱的愿望”。因此书的英文名干脆叫detachment,超脱。正如内封上所绘的源自书中的一个场景,一辆行驶在混乱街道上的三轮车,负重载着一幅巨大的海报牌,上面画着一个金黄的月亮。
徐衎笔下的故事常常发生在“婺城”。婺是浙江金华的古称,而浙江金华是徐衎的故乡,他用这个半虚半实的地名指代他所成长其中的广大江南城镇。那里兼有富庶和惘然,生长着徐衎所熟悉的南方百态人生,但他的小说又并非对那些人生的复刻,而是有更精彩的“超脱”,即如作家艾伟所言,他能“在庸常的底层生活中挖掘出诗性,在不可能的地方开出花朵”。《仙》,是在人心深处震颤的花瓣。近日,书乡对徐衎进行了专访。
■想吃禁果而不得的小人物们
对于《仙》的主题,徐衎自己有两句总结:“小的城里的小的民和小的命”,以及,“日常、家常以及日常底下稍稍不日常的一丝危机”。除了《俄狄浦斯2184》是一篇科幻作品外,其他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乃至边缘人,阿婆、保姆、下岗工人、残疾人、智力障碍人士、移民,等。日常的丝丝波澜未必掀起真实生活的飓风大浪,却足以搅动一场场内心的风暴。
《肉林执》一篇中,有个在义肢工厂上班的作家鲁贝贝,爱好文学的邮递员曾对她说,“鲁老师写的大部分人物都有一股没法伸张的冲动和欲望,蠢蠢欲动,只到蠢蠢欲动为止”。这评价似乎也正可以用来形容徐衎自己的小说和人物。在正常两性世界中压抑真实面向的艺术家鲁贝贝,还有《苹果刑》中向两个收养的孤残儿童讲授秘事的黄阿姨、《心经》中被寂寞所啮的老妇萃梅、《乌鸦工厂》中无声诉爱的哑巴工人、《红墙绿水黄琉璃》中随陌生人远走异乡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武昌,他们是现实生活中一道道不被人注意的沉默灰影,但徐衎的视角向平、向深处伸展,挖掘他们隐秘的内心,让我们听到轰然鼓噪其中的欲望潮音:渴求性与爱、渴求接纳与认同、渴求出走与回归……然而,这些欲望常是无声的呐喊,很难有彻底释放的出口,只默然归作未充分燃烧的灰烬。
前段时间,徐衎和浙江作协主席艾伟有一次笔谈,艾伟有个观点很有趣:“所有故事,其实都是偷吃禁果的故事……作家需要让人物偷吃禁果,让人物比作家走得更远。”徐衎由此悟到,作为文字世界的创始者,他正是在让人物“想够禁果而不得”,于是,“压抑、不满足或延迟满足,让人物总处于一种煎熬、干渴的状态”。欲望被压抑从而变形之后的姿态,成为他小说中独特的景观。
读这些小说让人时而想起张爱玲和施蛰存,评论家李璐在一篇文章中甚至将其与施蛰存《春阳》里的那位婵阿姨做了跨越时代的对照。纷杂的人事,潜隐的情欲,对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心理细致入微的描摹——很难想象出自一个约近90后的青年男作家笔下。徐衎说,张爱玲和施蛰存确是他上学时爱读的作家,着眼于“小”而不是宏大,亦是个人文学趣味使然的因素,但他坦白说,这种“着眼于人”的写法并没有什么值得自矜的,“在你不懂得太多社会规则或者历史积累的时候,单单去深挖、深描一个人物,从技术层面是比较好操作的,所以小说真的也是藏拙的艺术”。如今回望,这些作品集中写于2014至2017年,是写作途上一个阶段的产物,这几年他正在突破自身和“一个人”的局限,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许多年轻作家的写作题材绕不开自我的代际经验,缺乏历史与社会纵深感,因而在徐衎这里读到这些相对聚焦“他者”的书写,多少有惊喜之感。徐衎这些年的确因此收获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赞誉,自陈“吃了一些红利”,但他自己倒是冷静下来了,且反倒有个反向的观点,认为年轻作者写父辈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恰恰相反,“因为有太多的模板和现成的经典可以因循,这样的写作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且,“成功、经典的中年妇女形象多么多”。于他而言,这大概并非侈谈——缘于他所生活的江南市镇环境,对外人来说陌生的经验,对他自己来说却并不遥远,甚至小说里那些边缘人物,很多也都有原型。或可以说,这批笼统归为前期的作品,在许多维度上正映射、调用着徐衎自身沉淀的经验,它们建筑、重构成了一个婺城世界。
■工业质感的江南
《仙》中作为底色的“婺城”,与嘈嘈切切的人的故事相比略微有些灰蒙,但依然以各种草灰蛇线的形态游曳在其中,不仅是舞台,也推动故事。我们在碎片中拼凑着这座纸上小城的面目:
工厂是这里基本的城市空间和话语场所——《苹果刑》中的奶厂和纺织厂,“包装车间散落着一沓沓塑料标签纸,一瓶浑浊的成品奶端端正正摆在窗台上”;《肉林执》中的地毯厂和义肢厂,“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双手机械地拼装出许许多多的手和腿,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橡胶的甜腥气”;《乌鸦工厂》里的鞋厂,“右手垫进鞋肚,右手掌代替右脚掌从操作台这头走到头,换手,换鞋,走回来,一双牛皮鞋就抽检合格了”……工厂养活着作为工人的主人公们,而工厂的没落倒闭让他们跌进不确定的命运,随之而来的荒诞感像炮弹一样炸开。产业的起起落落,城市的拆迁改造,人员的流进流出,这里时刻发生着变化,上演着阶层、性别、地域、代际的冲突,构成故事生产的土壤,也呈现一个典型江南工商业城镇的图景。
徐衎的故乡浙江金华古称婺州,而小说中的“婺城”,事实上一并纳入了徐衎自己在武义县(隶属金华)、金华市、义乌市等地的成长和工作经验——“义乌,大家都很熟悉了,世界小商品之都嘛。”而于他更深刻的,还是在武义县城长大的经历。在徐衎记忆中,那里有一大片工业园区,诸如门厂、保温杯厂之类形形色色的厂子特别多。因此工人是徐衎并不陌生的群体,买断工龄的工厂职工,福利厂的残疾人,“因缘际会都有所接触,都有所感触,就写了”。当地还有很多来自湖南、贵州等地的务工者,《心经》里以当地阿婆萃梅之眼看去的那家来自贵州的租房客就撬开了这一层。
婺城有种工业质感,但这种源自东南沿海改革潮头地区的工业感又不同于双雪涛、班宇等当代东北作家们笔下东北老工业区的冰冷、沉重、朋克乃至魔幻(如今我们从文学中对当代工厂获得的印象常常来自于此),而是笼罩着一种细碎的商品经济气息:人们迷恋挣钱,头脑活络地寻找出路,同时还有充分的余裕关注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内心欲望和别人的流言蜚语、绯闻八卦。徐衎说,这种差别里面首先有历史的因素,东北和江南两个地域的工业发展历程和体系有很大不同,在文学中呈现出的气象自然也不同。而且,它们被书写的时代也不同——他喜欢双雪涛,不过,“双雪涛写的多是过去时的工厂,我写的是当下的工厂”。在徐衎印象中,工厂不只是旧时光的惨淡布景,而的确也有欣欣向荣的一面。他记得,去年疫情期间,外贸订单不仅没减,反而激增,工人比往年还忙。这些不同的生态,丰富了当代工厂书写或者说城镇、县城书写的多义性。
■社会打开的广阔维度
南方人徐衎在北方度过了七年求学岁月,再回到南方,是2014年研究生毕业之时。七年里,他接受的是专业的文学学术训练,尽管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祖训”,但创作并未因此停滞。他回想起来,研究生期间一度是有些苦闷,因为研究思潮与革命远多于具体作家作品,但现在却依然会感到从那段学术训练中受惠,譬如,学会对落入窠臼的警惕,由此获得一种内在的自反性,这“像一盏探照灯全程照着我”。比如《肉林执》中,那种对南方县城氛围与细节的铺叙并不罕有,但徐衎实际试图越过它们探讨的主题是,“异类”的特权和隐私,及他们如何在人群中获得呼吸空间。
《肉林执》无疑对徐衎很重要,他自我梳理时,会将其视作“自觉写作的一个成熟的标志”,至今会怀念写作它的2015年,也会诚恳地感谢人们对这一篇的肯定。当时他并未设想能写出一个中篇来,第一稿如他以前的篇幅习惯,写了一万五千字,编辑说,何必这么赶呢,可以从容地展开来。于是推翻重写,写了三万字。“这个是没想到的,里面人物其实挺多的,但把这么多人物用一个中篇结构完成了,完成度还不错,是一个小突破。”《肉林执》后来不仅成功发表在首屈一指的文学刊物《收获》上,而且还是发表在《收获》60周年纪念专刊上,分量自不待言,这对徐衎是个非常大的鼓舞,觉得在文学道路上更有了一点底气。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把那本杂志放在床头,“每天觉得和做梦一样”,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歌手拿到了金曲奖”。
那正是徐衎刚刚从学校毕业之初的几年。徐衎不是全职写作,他有一份看似和写作并无什么关联的本职——电网公司员工。但他觉得这也没什么违和的,一方面,“毕竟写的不是大IP、容易影视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生计问题,要不啃老地养活自己”,另一方面,他身边很多写作的朋友也都有着各种写作之外的工作。事实上,这份工作对他也是有益的,和校园不一样的工作、社会环境给他很多新的感触,同事们爱聊天,传递来的种种新信息为他的小说打开了新的维度。徐衎从内心觉得,从2014年开始,和以前闭塞、狭隘、常常只停留在素材层面上的写作状态不一样了,变得更开阔,可以进入写作的东西更多。譬如《苹果刑》中对身心智力不健全的孤残儿童的书写,灵感和素材就来自单位组织的一次慰问活动。它和《仙》中的其他作品,就是处于这两三年“社会人”转换期的产物。大门逐渐敞开,接下来的几年,徐衎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研班,获得了“人民文学·紫金之星”奖,步调渐稳。
现在,徐衎正在将兴趣和热情转向其他领域,转向自己的同辈人,关注职场、年轻夫妻甚至疫情等更为当下的议题,眼下正在写一个长篇的东西。写作十多年,终于出版了第一部比较满意的小说集,在今天更新迭代的世界里仿佛显得不太快,但对好好写作这件事来说,并不慢。徐衎希望的是,若干年后,看到从前的作品,能“不悔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