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诞生地,以写作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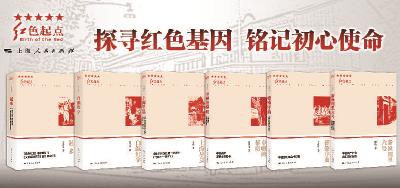
从党的诞生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以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这座城市,也是一座革命历史资源的富矿,如何以文学的形式予以深度挖掘和立体呈现,是摆在上海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以整体性、系统性的创作策划,2016年起,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市作协启动了“红色起点”主题创作项目,第一季推出的六部纪实文学作品引起热烈反响,第二季的多部作品目下也已进入编辑出版阶段;同期,主题创作项目的“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将推出第三辑,共呈现200多个精悍有力的革命遗迹故事。以两个主题创作项目的成果,上海作家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有力的答卷。
对于参与其中的多位作家而言,主题创作不同于个人书写,更是从体例、题材到写作方式的一次自我挑战和自我更新。
为了写《白纸红字》,作家程小莹进行了多次踏访和资料搜集。左联的事迹在史学上拥有丰富资料,回忆录、纪念文章、专家文献等资料堆叠如山。他苦寻的,是一个文学的角度。“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纷繁复杂的衍变和发展,给我们用文学叙事来书写城市红色历史题材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和方法。”从关注工人生活到向城市书写,近年则从虚构转向非虚构,投入现实主义题材和红色革命题材的创作,程小莹在写作上的跨越,内含着一种作家的自觉——他一直在写城市,如今则是由表及里,在对于城市文化肌理的深层剖析中寻找上海何以成为上海。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六十多年的程小莹,人生履迹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他非常清楚这里有一种上海人称之为“压箱底”的东西,而非虚构的形式,能够将其更为清晰地呈现:“这座城市的底蕴和历史的传承,在百年以来以一颗红色种子的形式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里面有无数可敬可爱又充满个性的人物,也有对于城市的认同感。”
程小莹说,每个人都会与自己的城市建立一种精神联系,有外观、生态上的认知,更多的是精神、灵魂上的体验和感知。关于左联的写作,是他的一次铭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所有一切都是城市的记忆,在其中你能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基本元素,和那些城市叙事里的浓重色彩,它们都拥有一种生长、发展的力量。”经由这番写作经历所打开的,则是一种新的历史思考,和城市文学的叙事空间,“更多人的故事不断地告诉我们,发生在上海的革命故事与上海如今的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城市文化的历史底蕴日积月累,足以让我们用文学叙事把这座城市珍贵的、有时代感的东西用文字保存下来。”
参与了两季“红色起点”创作的作家杨绣丽曾以诗歌创作为主,她说,自己在本质上依旧是个诗人。许多人觉得,诗人的洒脱随性和主题创作的严谨严肃很难调和,所以当数年前开始纪实文学的筹备和书写时,有不少朋友询问她能否胜任。《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末》问世后,这些疑问渐渐烟消云散。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在历史上存续的时间很短,这所学校里却曾走出过丁玲、王剑虹、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伟大的女性。以她们在这一阶段的故事为引,杨绣丽用散文的笔法重塑了一个时代的革命女性精神。她不断地被她们的事迹所震撼、打动,在写作时融入了大量个人情感。“写作这本书的许多个瞬间,我会想,换作我在那个年代,会怎么做?按我的性格,大概也走上革命道路了。”诗人是感性的,纪实文学的写作则要求理性为先,杨绣丽发现,这两者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却出乎意料地被“红色”这样一种色彩所调和。“那个年代敢于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奋斗和牺牲的人,心里都有一种激情。写诗的人,一样要有一种激情。如今在和平环境下,很少有情况能激发人们心中的这种情感,回望和深入红色历史的过程,唤醒了我心里的这部分感受。”
即将推出的“红色起点”第二季新作中,早期红色期刊、书籍等出版物成为了她追寻的对象。有时,为了一两张佐证当时出版物参与人员的材料,她需要辗转再三才能看到原件。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完成作品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总体性的资料收集和酝酿基础上创作的,最考验人的地方都在于‘如何写’。写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不‘怵’了。”最大的改变,也许来自一种对于题材把握能力的提升——如今她更直接地感受到,有底气的写作,会让作者进入更为流畅的创作状态。更有收获的一点,则在于纪实文学的写作对于诗歌的反哺。在整体性思考和书写的磨砺下,她清楚地意识到,抒情的同时,诗歌,特别是长诗在结构和叙事性上都有能从纪实写作中参鉴的地方。从而,那些在纪实文学中容纳不了的情感,纷纷以诗歌的方式在杨绣丽心中渐渐成型——以长诗《晨曦的路线》,她把在书写平民女校时候未能尽的感受倾情抒发;在献礼建党百年华诞的长诗《大地飞涌时光的朝霞》中,她以赤诚和激情写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赞歌:“……汲取时日的信仰/汲取薪火的力量/大地飞涌时光的朝霞/一条细小的溪流 筚路蓝缕/慢慢扩展成百年的河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光辉土地上/依然闪烁着朝气蓬勃的青春之光……”
接下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的主题创作任务初期,身为“80后”的作家王瑢内心颇感“纠结”。这种“纠结”,与她及不少同龄人对于历史的隔膜感不无相干:“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对红色历史的了解停留在孩童时代的课本和老电影上。对我来说,到底怎么写的确是个挑战。”
此后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王瑢不断往返于红色革命遗址、图书馆、档案馆等地收集资料,买了所有她认为与主题相关的书籍、碟片,看了网上所有关于同期资料的纪录片。尽管这些资料后来90%没有用上,却为王瑢补上了一堂历史课。原本以为看资料会是一段枯燥的经历,她却一下就“陷”了进去,“当你以往印象里仅有的一个历史知识点,还原成具体的人、地、事时,就好像从一滴水里突然发现一片海洋,你能不为这海洋的澎湃和浩瀚而动容吗?”这段过程也让她发现,红色历史从不是她所以为的单一色调,而是拥有丰厚层次、褶皱与纹理,由血与火交融而成的复调。“读完浩若烟海的史料,进入到那个历史场域中,我才真正意识到以往自己对于红色革命的认识那么偏颇片面,也真正领悟到如今我们珍贵和来之不易的幸福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王瑢完成了书稿,也交付了她自认为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写作:“作品中每个历史伟人,都成为了我脑海中熟识的、栩栩如生的友人。我终于领悟了他们所经历的、所奉献的一切,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写作,让更多年轻人真正理解他们、走近他们。”
对网络作家君天来说,“红色起点”的写作,更像是一次自然而然的选择。自小,君天就喜爱历史,许多历史英雄人物都是他如数家珍的偶像。在能够自由发挥的网络文学写作中,他就曾选择岳飞、于谦等民族英雄作为书写对象,展开浩荡的历史长卷。
在选择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书写对象后,君天曾走访原址,发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起点”——位于溧阳路的麦加里弄堂旧址早已拆迁,只有网上的一些历史图片可供参考。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随即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参与起义的革命志士英勇就义,如今已很难找到经历过起义的当事人。而当时一批党员同志撤离上海时,把资料销毁或带走,致使如今相关的资料并不多。着手收集时,相关题材的资料书,包括起义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成为君天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许多会议记录并不完整,也没有前因后果,为了交叉查证,君天不断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虽然所写的是1926年至1927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但做功课的过程中,他想要了解的是工人武装起义与北伐战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起义会在上海发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生;参与的人之前做过什么、结局又是什么等等。“资料收集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由点及面、由一个具体点位向一整条历史脉络靠拢的过程。”
对君天而言,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当所有事实如同证据链一样摆在眼前时,所形成的是一条清晰无比的历史脉络。“当我们通过真真切切的事件作为证据,推导出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纯粹依靠一个激情的念头和头脑发热的热度来写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正确的东西’。”这次写作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他厘清了这一阶段的脉络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也帮助他从更高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了解其重要作用和意义。“为什么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当梳理完这段过往时,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在作家们的感怀中,有一点无比清晰:红色主题书写,从不是概念和理念先行,而是写作面向的全新拓展,是小我向大我、内在世界向广阔天地的巨大跨越。正像程小莹的感悟,当我们所熟知的生活在历史的视角下被深刻理解和文学抒写时,所唤起的是关于共同政治理想的初始记忆。“体悟这样的初心与使命,会得到许多启迪,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程小莹说,“那个初心从历史的舞台回到了今朝,是一个人正在眺望着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