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的文学名人——阿兰·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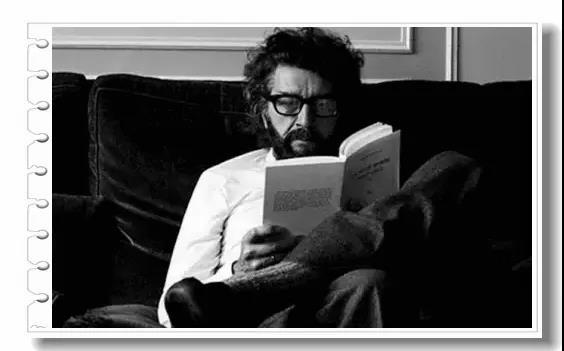
法国《读书》杂志2000年夏季号(总第287号)上发表了记者伊莱娜·弗兰对阿兰·罗伯-格里耶进行的采访,现根据网上的译稿摘编如下。
记者:在法国或者国外,只要说出您的名字,人们都会点头,表示非常尊敬,即使您很久没有发表作品也是如此。您怎样解释这种奇特的影响?
罗伯-格里耶:我要用安迪.沃霍尔的话来回答您:“我主要是由于我的名声才出名。”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了。所以往往有人走近我,吃惊地小声问道:“您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我说:“是的。”接着我问道:“您读过我的书?”他们都用一种害怕的声调说“没有”,然后又低声说:“不过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人们都是这个样子。
记者:您是怎样出名的?
罗伯-格里耶:我的《橡皮块》发表以后,批评家们惊讶地保持沉默。接着发表的《窥视者》却引起了轰动,几乎立刻就取得了成功。因为在发表《窥视者》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谈够了萨特和加缪,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就转向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说明我的作品是如何不堪卒读。当时在评论界称霸的那几个人,认为文学到巴尔扎克就为止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尤其是对于外国文学,无论是卡夫卡还是福克纳的作品都没有读过。
记者:您提到他们时似乎觉得很好笑……
罗伯-格里耶:太可笑了!他们往往走得很远:例如埃米尔.昂里奥,他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断定我是一个疯子,很可能是个杀人犯。
记者:在赢得读者之前,您靠什么谋生?
罗伯-格里耶:我有一张国立农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只要拿出来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在50年代,文学还没有被当成一种职业,更不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受穷也能被人理解。我有时候住在朋友们借给我的一间仆人住的房间里,穿他们不愿意再穿的衣服。我认为只要不去饭店,活下去就很容易……今天一个青年作家就要有一套房子,一条狗,一辆轿车。他要马上卖掉他的书,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最好是成为畅销书的作者。
记者:这是一种指责?
罗伯-格里耶:不,我不作评价。文学是由各种文学组成的。有带来麻烦的文学,也有不妨碍任何人的文学。
记者:您的作品被大量译成外文,因此您的名声在国外比在法国还大?
罗伯-格里耶:外国对我的书感兴趣,就像对波尔多葡萄酒、干酪和香水等其他特别尖端的法国产品一样。比如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很善于把它们做成畅销书,而且比法国人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在健在的法国作家当中,被译成中文的作品最多的原因。
记者:您的影片对于扩大您的作品的影响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罗伯-格里耶:电影面对的是另一批观众。它使您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吸引闲人的地方。普通的观众常常觉得我的影片不可理解,但是还要来看,因为性挑逗虽然在我的全部小说里都有,但是在影片里要明显得多了,这就提高了上座率。不过这些影片也使我付出了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代价。1985年,我获奖的形势很有利,当时瑞典的影片资料馆安排了一场我的影片回顾展,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愤怒,他们起来反对法国的色情影片。于是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我对此感到高兴。
记者: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正在做什么……
罗伯-格里耶:我正在写一部作品和拍摄一部影片,但是我不想多谈,因为我还不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什么结果。
记者:您对法国文学的现状有何看法?
罗伯-格里耶:时代更加平静了。没有杜拉斯,没有克洛德.西蒙。让.艾什诺兹、让-菲力普.图森是优秀的作家,但他们是想要把书卖出去,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即使是杜拉斯,在生命的暮年,也多么想成为一个富婆。
记者:您是否逃避大众传播媒介?
罗伯-格里耶:不,我不时在电视上露面。我不是一个野人。我对画家、电影工作者和作家们的阶层很有好感。我非常主张“全世界作家们,联合起来”。我要再次表明,我认为存在着多种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唯一优秀的文学。
记者:您曾经宣称不再写小说了。
罗伯-格里耶:是的,这会方便我的生活:再没有人会不断地问我正在写什么。而且,我还对生活中别的东西感兴趣,我不感到自己要拴在办公桌前不得不生产什么。要让我动笔写作,我必须真正有一本书在脑子里。这当然并不意味书已经完全想好了,规划好了,不,我只是头脑中有一部要求诞生的书。这一段构思过程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叙事形式在酝酿,背景或事件因素渐渐地组织起来。最后,我开始写,而在这时候,一切都具体化了,包括文学的形式,发生的事情,人物的样子。比如说,正是在写作《反复》的时候,两个对立的叙述者变成了双胞胎:就是当其中的一个在摆着两张很小的儿童床的房间里醒来的时候,两张床一模一样,房间中的一切也都成双成对,一切都是双重的。这一切,我事先并没有想好。但是,双重化的想法毕竟是有计划的,因为《反复》本身就在重写克尔凯郭尔的一本书,一本同样叫做《反复》的书。
克尔凯郭尔跟蕾吉娜·奥尔森分了手,自愿毁灭了他的爱情,在书中,他想象他将重构这段爱情:他重返柏林,重做同样的行为,去同一个剧院,重看同一出戏剧,同一个演员……并发现这行不通。两张一样的床的场景也许来自克尔凯郭尔对猎手街57号的公寓——我的叙述者也住在那里——所做的描写,他这样说过,“两个房间是如此相像,以至于看起来,一个就像是另一个在镜子中的反映。”他久久地展开着这种双重化的印象,他的文字在我自己的书中被完全重复了。
记者:您同样还反复了您以前小说中的因素,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您的全部作品都浓缩在了这一本书中。
罗伯-格里耶:一开始,是在复写《橡皮》中的事情,而《橡皮》本身就已经是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复写了。就是说,不是重复,而是“反复”,按克尔凯郭尔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上,就仿佛《橡皮》是一本成了废墟的书,我采用其中的片段,为的是把它们放在另一个范围内。此外,在《橡皮》中,就已经有对许多别的作品的影射了。从我最初的那些书开始,我就用过去的废墟残块来构建另外的东西。而此后的所有作品,都包括对我以前作品或者对别的作家作品的引用和回顾。例如,我突然插入一句马拉美的诗歌,在上下文中并不显眼。我对文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当然,不是整个的文学,但是我的文选还是相当广泛的。我喜欢的作家,法国的或外国的,我随他们长大、随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些作家,都是“我”,都构成了我,我是由残块片断构成的,我只能这样地恢复自己。
记者:您还曾宣称过,您所写的只是关于您自己的东西。
罗伯-格里耶:从我的第一本书起,情况就是如此,我的第一本书《弑君者》,一开始被伽利马出版社拒绝,只是在1978年才出版。一切都是自传性的,但一切又都是混杂的:种种事件被移了位。再说一遍,这都是些我的片断,就仿佛我自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废墟:旧约、日耳曼神话、凯尔特文明和希腊神话,在我的教育中是那么的重要。我是由所有这些文化的片段造成的,是这些碎片的一个保管者。我反复使用这些文化废墟或被我的记忆抛弃的碎屑,那是为了使它们移位,使它们显示在另一道光线下,是为了让博物馆中的物件变成活生生的石头。
记者:这些废墟或者这些碎片,您是怎样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呢?
罗伯-格里耶:我不说是粘贴,而更愿意说是剪辑或者重构。从我的童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一种忧虑之中,担心世界会坍塌成废墟。开始,在3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解体了。今天的人们也许会很惊奇,贝当元帅当年竟如此轻而易举地操纵了这个民族,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共和国陷于一种信誉扫地、一种土崩瓦解中,不仅在属于法兰西行动[当时的一个右翼政治组织]派的我们家,而且在全体法兰西人民中,全都如此。政府成立三天就倒台,这是左派和右派多多少少暧昧可疑的共治的结果,这绝对是令人忧伤的。战争来临了,而世界上最漂亮的、最强大的、最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三天中就垮了。当1945年和平重现时,从布雷斯特到华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正是在这一片废墟之上,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不断地建立起来。在1945年,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欲望变得从未有过地强烈:不仅在创作者中,而且在读者中,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要求,要求改变。两年前,在1999年12月的飓风袭击中,我的林地中有85%的树木被毁。这个林园,我已经彻底地跟它合成一体了:四十年来,我照应老树,我栽种新树,而它们,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中就全毁了。今天,我还在补种。我已经80岁了,但是,我也许还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始终在重构。
记者:战争期间,您在做什么呢?
罗伯-格里耶:1940年,我才18岁,这样,我就没有入伍。我是在两年之后20岁的时候,被维希政府招去入伍的,那机构叫做STO,是专门接替战俘的:我这一类的人必须到德国的工厂去干活,而战俘们则被替换回他们的家。我很情愿地去了,但战俘们却没能回来。那是一些劳动营,很苦,但跟灭绝营完全是两回事。一年之后,我病倒了,被遣返回国。
记者:在《无限》的最后一册中,马尔塞兰·普雷奈指责您是贝当分子。您怎么回答呢?
罗伯-格里耶:我跟95%的法国人一样,曾是贝当分子。否认这一点,在今天声称什么当时(那些人也不了解当时)不会当贝当分子,那是一种虚伪,是纯粹的犯混。如此说来,马尔塞兰·普雷奈从来就算不上是世纪的精英。此外,说我是贝当分子,实在算不上是什么独家新闻,因为我自己已经在我的一些书中讲过那些事了,例如在《重现的镜子》中。我们这位亲爱的普雷奈突然的愤慨来自我的证实,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我说过,菲利普·索莱尔斯已经把《原样》的出租椅子女人般的虔诚扔到了阴影中。
记者:再回到双重化和两重性上来。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您写道,小说中好的人物应该是双重的。为什么?
罗伯-格里耶:人们总是跟我争论,因为我把巴尔扎克当作陪衬物。我说到巴尔扎克的伟大作品,它们建设起了一个特别一致的、具有意义的、令人放心的世界——1830年胜利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而那时候,整个社会和小说叙事被凝固在混凝土中。世界骨化了,封闭在自身中。必须等到福楼拜出现,使得文本中的空白和缺口、意义的丢失、无用的和无度的物件能重新产生。那是一些超越了其意义的物件,而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超越意义。意义与世界在他的作品中是彼此彻底一致的。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是一个现代的作家,在他身上没有矛盾,而在世界中,到处充满着矛盾。我在这里说的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在现代世界中,事物发展的动力恰恰是缺乏和矛盾。而现代人物则双重化,以便跟自己作斗争。福楼拜,随后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再随后是卡夫卡,都描绘一个丢失了意义的、变得陌生的、令人不安的、荒诞的世界,一个不断寻找着一种可能的新意义的世界。
记者:通过使用色情、幽默、一种不断变化的叙述法,您是不是在寻求着歪曲现实?
罗伯-格里耶:我倒更愿意说是颠覆现实。说到色情,那是一些歪曲。我继续坚持认为,我的文学与现代精神相吻合。确实,在今天,人们回归到更为理性化的叙述。比如米歇尔·乌艾勒贝克……
记者: ……他跟您一样,曾经学过农艺。
罗伯-格里耶:是的,但不是同一个文学派别。人们说他是一个现代作家,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社会。除去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区别在巴尔扎克作品中也有同样的东西:卢卡契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革命作家是巴尔扎克,因为他说到了社会问题。然而,这只是从主题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伯克莱大学教授雷奥·贝尔撒尼回答得很恰当,他说,巴尔扎克加强了资产阶级,因为他使用它的话语,对它的叙述并不提出疑问。在乌艾勒贝克的作品中,情况也一样:他并没有动摇什么东西。这么说,我丝毫没有反对他的意思。不妨说,那根本不是我的世界。
记者: 在《反复》中,有一个少女,她混入到邪恶的剧情中。在我们穿越的道德化阶段,您难道不怕遇到审查的麻烦吗?
罗伯-格里耶:我的电影已经遭到过审查的麻烦了,尤其是在意大利。在法国只有过一次,我差点儿因《火的游戏》遭罪。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刚获得了荣誉团勋章——那时候,文化部寻求一些左翼人士做装饰——,我便反复掂量,权衡利弊。突然,人们放过了我。再说,那毕竟是一些幻觉场景……于是,我想那书不会有问题了。一个女权主义组织把我从一个美国大学中赶走,因为在我的书中,女人的形象是不正确的。这很荒诞。在《反复》中,这个少女比她周围那些想制服她的男人要更有智慧,更有活力,更机灵。在《欲念浮动》中,阿尼塞·阿尔维娜的情况也是如此:三个被她嘲弄了的男人,警察、法官和神甫,在她身边都显得那么的不可靠。而这,就是女人的一种反面形象?
记者:人们可以对《反复》作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阅读:女性阉割,物恋对象,俄狄浦斯情结。
罗伯-格里耶:心理分析学是那些试图使人类规范化的所谓科学之一,我特别喜欢拿它的象征体系来游戏,搬用它,把它带到危险中。那些象征属于现代性的老一套。一个科学家不会相信一种理论的真理。它只是一种工具,尽此而已。
记者:新小说在人们心中始终像是一种十分理论化、十分客观的方法。
罗伯-格里耶:对新小说,人们写了实在太多的蠢话。比如说,在我的书中,人、人类是不在场的。人们很平静地就把它们简化为客观性……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转向了客体的主观性,它属于目光,属于意向性。话虽如此,我并不抱怨人们散布的关于新小说的蠢话,那可是一种极好的广告:当人们让你说极其荒唐的话——诸如“书不是由一个作者写的,而是由一个书写者写的”——时,它会使众人担心,它会使你明白。相反,真的,它不会使读者跑上去的。
记者:而在美国,人们伸开双臂欢迎您。
罗伯-格里耶:画家们,是的,但不是作家们。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那一代人不知道我,另一些甚至咒骂我。倒是那些最年轻的对我感兴趣,比如杰罗姆·查林,他十六岁时就读了《窥视者》。画家们,显然包括劳申伯格、利希腾斯坦、韦塞尔曼、罗森奎斯特和沃霍尔。由于沃霍尔说话有些困难,他满足于为他的朋友们拍照。他不断地拍我,但我猜,他的照相机里恐怕没有胶卷。那只是一个纯粹的交流感情的动作,一个维持联系的动作。
记者:新小说问世五十年之后,您是不是对今天年轻的法国文学的状况有些失望?
罗伯-格里耶:不太失望,因为毕竟还有些很好的作者。比如说,玛丽·恩迪耶,她有一种非凡的写作能力。她的世界不是现实主义的,但却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只想说,最强有力的并不在市场上。或者说,当他们开始进入市场后,他们通常就不那么好了。我们是处在一个深刻厌倦的时代。首先,年轻的作家们更喜欢把书卖出去,而这根本就不是过去作家们的计划。那时候,没有人特别关心这些,纪德也好,新小说也好,萨特也好,都不是为了把书卖出去才写作的。假如能卖出去,他们当然很高兴,但是,刺激他们写作的兴奋点在另一边,亨利·米肖曾说过:“任何能卖出二百册以上的书,都是一部坏书。”他把杠杠划得很高。今天,年轻作家们要结婚,要维持家庭,要有一辆汽车,一套房子,但不从事一个另外的职业。这可决不是我生存的目的。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已经是一个农艺师,有一份丰厚的薪水,我生活在法兰西堡的一座大房子里,有两辆汽车,有一些雇工,而我离开了这一切,来写没有人想要的书,来尝试发明新的形式,而毫不考虑从中获得回报。
记者:人们还能发明新的形式吗?
罗伯-格里耶:想是的,但是时代的条件却少多了。说起来令人忧伤,但我们或许缺少某些废墟。对我来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一个冰冻的阶段,从社会、从文学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冰冻阶段,世界固定在它自身的稳定中。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人们只有置身在文学之外,就是说,通过搞社会学,才能够创造出文学奇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