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在墨西哥,寻找鲁尔福

即将过去的这个冬天,据说是近二十年来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我记忆里另一个寒冷的冬天是2009年,翻译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的那段时光。当时我租住在成贤街上一间原属东南大学教工宿舍的单室套老房子里。一天当中,房间受阳光眷顾的时间是短暂的,冷风倒是很殷勤地不断从窗缝中摸爬进来,空调的制热效果也不尽人意。我还记得那年冬天老是下雨,寒气与潮气混在一起,阴惨惨的,倒是比较适合想象书中的悲剧场景。
事实上,在翻译这部墨西哥写实作品之前,我从没去过墨西哥。我唯有在想象中还原那些故事发生的场景。然而所谓真实的叙事场景是不存在的,作家描述的那些时空都只在虚构之中,逼肖现实而非原原本本的现实。正因为此,想在山东高密寻找莫言作品故事人物的访客多是失望的。
当我坐进飞往墨西哥的班机、开始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涯时,《燃烧的原野》(译林第一版)的译稿刚刚下厂印刷。我已明白,此行是找不到那些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的,也见不着作家本人——他早在1986年就与世长辞了。我只是想验证一下,今天的现实中的墨西哥,在多大程度上还是鲁尔福笔下的那个墨西哥。

鲁尔福与马尔克斯
1917年,胡安·鲁尔福出生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农村。他七岁丧父,十一岁丧母,成为孤儿。他不得不由祖母抚养,后又被送入瓜达拉哈拉的孤儿院。
我是在2011年的春天抵达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的。乘坐长途客车从高原上的墨西哥城出来,一路海拔渐低,气温也越来越高。4月里的瓜达拉哈拉已是30多摄氏度的高温,哈利斯科其他各地想必也同此酷热。行进在瓜达拉哈拉上空的烈日下,我不由想起鲁尔福笔下的那块给晒得冒烟的荒野。在《我们分到了地》的故事中,一群期待分享革命胜利果实的农民行进在干燥、炙热的白土平原上,忍着饥渴,寻找着政府承诺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也没有找到那爿憧憬中的沃土,因为他们被分到的就是这块“硬牛皮”、这块“烫得像饼铛似的”荒原。
我在瓜达拉哈拉的一家风味餐厅里见到了这所谓“饼铛”(comal),一种源自印第安人文化传统、至今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广泛使用的炊具:一个架在火上烤的陶土圆盘,用来把玉米面团摊成薄饼皮。鲁尔福的名篇《佩德罗·巴拉莫》中的魔幻村庄科马拉(Comala)之名就来自这种炊具,可见那是一块热得多么吓人的土地。
这样的酷热,与热带的激情、革命的热烈毫无关系。在鲁尔福笔下,这样的酷热反倒与荒凉靠得更近。在从首都通往哈利斯科的公路上,我见到的这热带的原野就是一派荒凉的景象。那些在平原上孤独耸立的火山,仿佛刚刚经历过,或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爆发,在此期间,天和地都静寂不动,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出奇的明净。
我曾以翻译的身份陪同一个中方代表团考察墨西哥医疗卫生基础建设。我们去的是伊达尔戈,墨国最穷的州之一。我们与墨国卫生部官员一起在高雅精致的酒店里品尝当地美食,随后去参观条件简陋得与中国的乡下卫生所相差无几的州立妇产医院,以及荒野中被牛羊粪便气味包围的妇幼保健所。当地官员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这些年来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战战兢兢地想给上级官员留下好印象。在这个国家,这样的场景,仿佛一百年来都在重复发生。
在瓜达拉哈拉这座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我并没有见到与鲁尔福有关的纪念雕塑或是遗迹。周末的夜晚,市中心街道上三五成群喝着啤酒的年轻人,多是瓜达拉哈拉大学的学生。1933年,鲁尔福曾尝试进入这所大学深造,却正逢罢课闹事,只得另做他图,远赴首都,在高等学府中插班旁听。
1930年代的墨西哥城是一如今天这般庞杂喧嚣、充满活力的。迭戈·里维拉用他的画笔装点着公共建筑物的外墙,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宣布将石油收归国有,阿方索·雷耶斯接来一批批流亡无所的西班牙文人朋友以丰富墨西哥的思想界……1934年,胡安·鲁尔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我在墨西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城度过的。在这里,世界一流的豪宅名车与第三世界的贫穷并存。在地铁里,在拥挤的小巴士上,在街边小摊之间,我看到了那些皮肤黝黑的面孔。他们成批成批地从鲁尔福笔下的破败乡村中出逃,希冀着能在大城市中找到幸福生活,却绝少被城市所接纳。他们以各种方式营生,带着自己为数众多的子孙顽强地生活下去,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去除的“碍眼景象”。
与高档社区圣塔菲的摩天大楼相伴的满山红屋顶,不是别墅区,而是贫民窟。这些居民都是从“卢维纳”逃出来的吗?
根据鲁尔福在《卢维纳》中的叙述,这是大山深处一座被遗忘了的破落小镇。青壮人口都弃它而去,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在孤独中等待老去和死亡。“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连狗都死光了,这寂静都没有狗叫声相伴了。人去了那里,待到习惯了那里的大风,就只能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了。”将近百年过去,“卢维纳”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消失,而是越来越多了。
我曾在墨西哥外交部大楼的门口看到过一次震撼人心的艺展。一位来自南方穷山沟的艺术家,在多年后返回故乡时,看到的是与“卢维纳”一般凄凉孤寂的农村。没有经济发展的惠顾,没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人们背起行囊,去城市、去首都、去北邻的美国谋求生路了。他在查阅了人口档案后,捏了一千个形态各异的泥人,代表这出走的两千五百多个老乡。这支泥人大军组成的方阵无声地站立在官府门口,仿佛蕴藏着某种巨大的力量。事实上,肉体的他们散落在各大城市的角落,成了没有故乡的游魂。
鲁尔福也曾云游四方。在1946年至1952年为固特异公司工作期间,他借着推销产品的机会走访墨西哥各地,在乡村中听老人们讲述最土最纯朴的故事。这些不受任何文艺法则束缚、充满奇幻的故事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少灵感。1953年和1955年,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声名鹊起。然而,此后他便绝少从事小说创作了,仿佛先前发表的重磅作品已经耗尽了他的叙事才能,或者仿佛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说:在完成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激情之后,鲁尔福便沉沉睡去。虽然这两部作品让他成为拉丁美洲最出色的作家之一,他却很少在公共媒体中抛头露面,直至离世。
从固特异公司离职后,鲁尔福进入墨西哥国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墨西哥原住民文化传统的维护工作。尽管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写作关怀穷苦人、印第安人,也许他是在停止创作小说之后,把这份情怀默默地灌注在平庸的、日常的公务工作中了。而他也是被翻译成最多种美洲土著语言的拉美作家之一。印第安人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自己的生活。那些在贫苦乡村里日日重演,为鲁尔福冷静地叙述出来的仇杀、通奸、垂死挣扎,破除了田园牧歌的优美神话,生存的现实被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墨西哥,族群众多的印第安人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有一些甚至在五百年前的西班牙殖民征服时代就躲进深山,从此与世隔绝,将古老的生活方式延续下去。“现代化”进程还是无情地开进了他们维系传统的社区,抢走他们的土地,逼迫他们接受“文明”、融入资本市场弱肉强食的秩序中。在墨西哥的媒体中,印第安人权利被侵犯、奋起反击的事件时有报道。
2010年秋,我在墨西哥城街头目睹了一次印第安原住民的大游行。他们身穿民族传统服饰,打着最平白的标语,呼吁人们关注他们正在遭受的野蛮掠夺。队伍中,一位头戴绿军帽的女青年向沿路所见的路人分发传单。我接过传单,问她在抗议什么,她急急地告诉我,她的村庄岌岌可危,背后有人指使的准军事组织向村民开枪,企图让所有反对土地买卖的村民噤声。我还想问更多,她抱歉地朝我笑笑,追赶着前行的游行队伍远去了。
我曾在书店里找到一本胡安·鲁尔福的摄影作品集。摄影是他的一大业余爱好。除了文字,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像作品。在其中的一幅照片上,我看到两个戴着草帽的印第安人远去的背影。女的提着篮子走着路,男的骑在瘦马上,向着辽阔的天空进发。他们究竟是往哪里去呢?鲁尔福没有留下答案。
2020年4月于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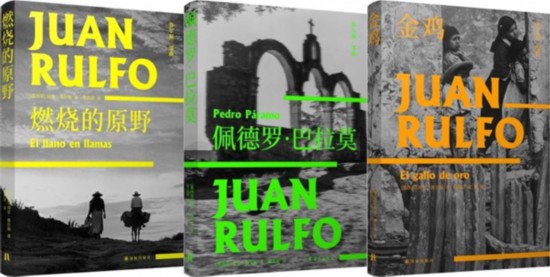
“鲁尔福三部曲”,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