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泽平诗歌的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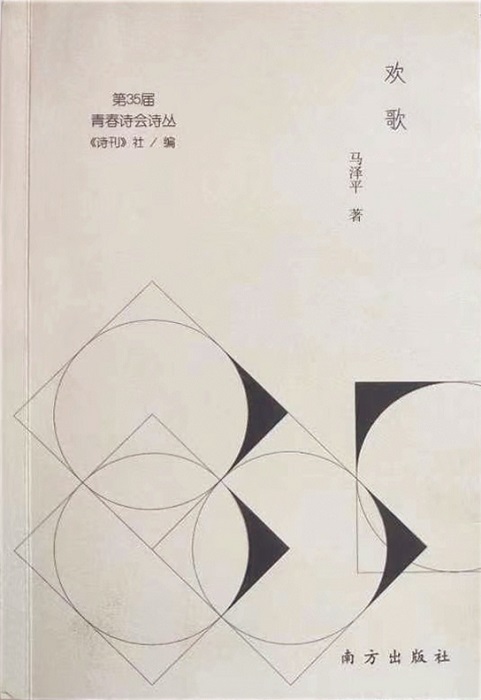
也许是出版商们脸上流露出的不安神情神迹般改写了《抒情时代》的命运,使之以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为名,被阅读、被解读,也达成了米兰∙昆德拉在20世纪50代中期就产生的那个欲念:“解决一个美学问题:怎样写一部属于‘诗歌批评’的小说,同时它自身又是诗歌(传达诗歌的激情和想象)。” 对于一开始立志要写小说的马泽平而言,《生活在别处》是他众多小说读物中的一款,虽不能肯定这部小说在文体意识上带给马泽平多大的影响,但就马泽平此后诗歌中所面对和解决的“美学问题”而言,与昆德拉有着类似的思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用诗歌完成小说的抱负又使诗歌葆有诗性,或者说,是以何种方式在诗歌中暗藏那个小说的梦想,且能够最大化地成就诗歌。追溯马泽平诗歌的艺术源头就会发现,构造马泽平诗歌的建筑艺术已不仅是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的相互扶持,而且借鉴了电影的镜头思维,跨媒介的“出位之思”让马泽平的诗歌表征出更丰盈的艺术内涵。
以诗歌《湄江河上》为例。在建筑上,诗歌由三个诗节构成,它们之间的转换具备诗节应有的“转折”意义,即使不知晓这首诗歌身世的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障碍。但作为对电影《情人》的一次诗歌转译,诗歌的三个诗节转换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电影镜头,编辑、推位摇移的镜头语言与思维给了诗歌外在的构型依据。沿着诗中“湄江河”“西贡”“来自中国的木质器具”“他的妻妾”……可以顺利找到这首诗歌内容上的外祖母:杜拉斯的小说《情人》。钩沉这首诗歌的往事,就可以看到诗歌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小说与电影:电影、小说、诗歌相互叠映,生成文本复调的肌理。在细微处,小说的故事情节与电影的镜头等丰满了诗歌,也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与技巧;在宏观上,小说、电影在马泽平的部分诗歌中替代了现实生活而成为诗歌的母本与背景,在虚构之上再虚构。这也是马泽平这一代人与他的父辈们精神文化构建上的差异之一,也是使得马泽平诗歌最大化脱离了地理阈限与地域气质的重要原因之一,亦使马泽平的这类诗歌在一个数字化的、主要靠视觉传达的读图时代对读者呈现出了一定的亲和力。诗歌在化用小说的故事情节时,叙事的成分带给诗歌的不仅是叙述事件,也是一种口吻和氛围,尤其重要的是其内在的音乐性,这种内在的音乐性与情节的推进相生相伴,与诗歌外显的韵致相生相伴,共同完成了诗篇的交响与重奏,彰显了诗歌整体构架的内在张力。
沿着《湄江河上》指示的路径,一路途经《第176号梦境》《布拉格广场》……可以看到马泽平在不断开拓诗歌的疆域:梦境与现实、虚构与现实、写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时间的线性与空间的平面性都可以通过诗歌的魔幻术打破壁垒。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与一部小说中的植物学老师、阿伦娜教堂,电影《罗生门》中的活板木门,诗人自身常年乘坐绿皮火车穿梭的经历,通过镜头的切换糅合进同一首诗歌。如此繁复、琐屑的材料,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是一种冒险,稍有不慎,都会让瞬忽即逝的诗意流走。但诗集《欢歌》中几乎没有一首诗歌沦入那种危险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泽平诗歌造境的觉醒与追求,在造境中抟塑,显现出的是诗人心象的奇观。
又比如《湄江河上》具备了小说的一切质素:人物、情节与环境……但它最终还是以诗的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发出诗的召唤,道出诗的言说。它有叙事,但不为叙事而叙事,甚至也可以不依赖于叙事而成立;它既具有外显的音乐性,又具有情节结构内蕴的音乐性;它有虚构,但它的虚构是为托生意趣与情趣而创设。“河面上闲落着几朵浮萍”,诗歌始于这逝者如斯的流逝感与无依无系的漂泊感。在水天茫茫中,人物出场,“孤独的人没有出声”,人物的无声息应和了脚下“寂无声息”的场域,似乎人与江面都只是镜头中飞动着、发出声响的水鸟的行动场域构成,对水鸟而言,人无异于江面上的一叶漂萍。人的存在的寂寥感与孤独感漫衍过辽阔的江面,氤氲成全诗的意境。这层诗境的基础建设完成之后,人物开始行动,“点一支烟,看鸟翅擦过船舷”,有闲看落花的意趣,“鸟翅擦过船舷”的瞬间隐喻,预示着两个即将相遇的人物的危险关系与他们终将分离的命运,惊心动魄又让人怅然慨叹。“鸟翅擦过船舷”这类镜头作为隐喻与预示,也是被基耶斯洛夫斯基、李沧东、关锦鹏等等大大小小的电影导演谙熟的技艺。接下来的情节在细节并置、意象并置中展开,“他”手心里仅剩的几颗念珠、还没能下雪的西贡、精致的屋舍、来自中国的木质器具,有意识无意识的主体感觉关联着它们,呈现出诗人心象的奇观。当“他说起妻妾”,当“她说没有关系”的时候,“她像颤动着的烛火”,电影中珍∙玛琪诠释的简没有执著于地久天长,小说中“我”的叙述也没有纠缠于天长地久,此地的“她”亦不曾,她们过早地接受了作为此在者浮萍般的命运,在寂然无声又辽阔无际的场域中,在场者都是风中烛火,明明灭灭,到哪里去把握恒久?当然,诗歌并没有为此而降调,诗歌写作者对此也坦然地接受,甚至从中腾挪出自己,旁观。“风轻轻吹着”,是江面轻风,是人世轻风,是内心轻风;是慧能的轻风,是怀斯的轻风,是志南的轻风;是情节里的轻风,是镜头里的轻风,是诗思里的轻风。在以烛火呼应开篇的浮萍之时,这缕轻风以四两拨千斤的绵柔轻松化解了轮渡也载不动的那几多愁绪。于是,诗歌没有走向无力无奈的在世泥泞,而是超脱为了无踪迹的云烟,向无处去。浑然一体的诗境,应和了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神韵。
虽是应和,但这里有必要指出,马泽平并不着意在物象中打捞和撷取禅机,顿悟并非他的诗歌追求,他无心走禅悟的老路,提取和激发诗歌的情趣性与意趣性才是他心心念念反反复复打磨提炼的目的。而使这些情趣与意趣得以依托、得以浑然一体的最终指向是他对诗境的造设。
当然,马泽平诗歌也不是处处大动干戈才能装修出意中之境,他也捕捉瞬忽即逝的感觉,把握浑然天成的诗境,比如《赞歌》,放弃了功利性的意义,诗歌获得了诗性的审美意义,与顾城的《门前》可以媲美:“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欣慰的是,顾城的希望,在马泽平这里成为对实有的赞颂。
“往往一首诗的语言先于架构以及内涵带给我阅读的愉悦感……往往是一首诗的架构以及内涵超越语言留给我历久弥新的愉悦感。”的确,相对于句子迷,马泽平更追求诗歌营建的整体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泽平不重视对诗句的锤炼,只是他那些“盐水煎熬过的句子”隐伏于诗歌的整体诗境之中,有点汪曾祺小说所谓“不能切割”的水意。如果非要切割,也会撕扯出箴言式的诗句:“我总拥有同一只瓷碗/盛清水,也弹烟灰”,甚至《告诫》式的绝唱:“我的胸口藏有/劲竹与积雪/我不担心没有听众”。但总体上,马泽平无意于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窄路,他意在谋篇,志在诗境。为此,他更着意诗语的情趣与意趣,而那些情趣与意趣最终又落到情节与细节上、落在意象上。
“是的,我迷恋细节甚至多过语言艺术本身。”在他众多的带着叙事性与镜头感的诗篇中,他依持了细节的力量。当诗歌依持细节寸步前行时,细节上附着的故事感、细节上散发出的时光磨灭感、细节上漫衍的生之兴味、细节上氤氲的不能言传之意味给诗语带来毛茸茸的可生长的意趣与情趣。在细节描摹的同时,马泽平也注重意象的抟塑。比如他那些箴言绝唱,要在有限的诗句中传达出无穷之意,诗歌依持了意象:“我总拥有同一只瓷碗/盛清水,也弹烟灰”,“我的胸口藏有/劲竹与积雪/我不担心没有听众”。瓷碗、清水、烟灰、劲竹与雪,被编码进诗语中,既是实指,亦是意指,既是所指,亦是能指。瓷碗既是容纳之物,也是存在场域。清水与烟灰,劲竹与雪;前者是洁净与琐屑的选择,又是水与尘的不能断舍;后者是刚与柔,是猛虎细嗅蔷薇。虽然那些被人们熟知的意象,“在流传和解读的不断公约化提取中”,很可能“成为工具性明显的语词式的语言存在”,意象的诗性也可能会在生成典故以后消亡,“简单的移植不可能赋予它们生命力”。但马泽平有时创新,有时也恰到好处地移植。与此同时,他也让古典诗歌的流脉在自己的诗歌中得到遗存与传承。那些古典意境与意象借助异时代的语境生出错愕的花来,因时空流转的缘故生出了新意,激发了新趣,产生了新美。
正是细节的描摹与意象的抟塑,使诗歌既“有木石心”,亦“具云水趣”。这也正是马泽平有意为之、心向往之的写作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