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小说的文化阐释 ——由《湖光山色》说开去

周大新(1952~),河南邓州人。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历任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周大新文集》20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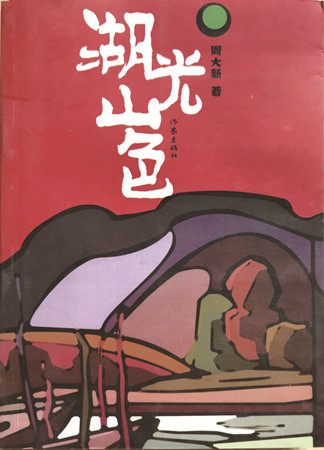
《湖光山色》
周大新是个文如其人的作家,这是当下实属罕见的品质。我们已惯于将写作与本人分开,那是小说、虚构,是职业与社会分工;作家在小说中“狂欢”、“放纵”甚至“穷凶极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一般不会为此愧疚、负罪或分裂。然而,这种“行规”却被大新破例了。他的“小说”与“我”说、虚构与行事、美学追求与现实轨仪,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当一致的底限、禁忌与内涵。它们和德性有关——比如“善良”,这是对大新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可谓直观、鲜明的“共识”了——却又远不局限于此。与其说那是有意为之、谨慎从事的结果(别忘了大新的军人身份),不如说它更多源于本色和天性。
大新是河南邓州(隶属南阳)人,邓州位于豫省西南盆地,南毗湖北襄阳(二者相距仅三十公里),境内山水俊逸,气候温润,宛然是河南的“小江南”。在当今豫籍作家整体偏于凌厉怪诞的风格背景中,大新属于少数婉约派。他的文字平实舒畅,却也自有一种秀媚劲拔之气。这跟故乡山水(尤其是水)的滋养与默默启迪不无干系。大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讲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水边的故事,小说中的丹湖即为南阳的丹江水库。不少读者还由《湖光山色》联想到沈从文的湘西书写,“水”在此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中介与桥梁,而不单单只是背景。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如果说山象征着坚毅、原则、厚重、男性,那么水则是灵动、和婉、多情、女性的自然教诲与示范。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河南作家大多写不好女性,其作品中的女子要么干巴无趣,要么纯粹符号化,写女性似乎是江南作家或南方作家的特长,但大新例外。他善于也属意刻画女性,道不尽诉不完;说女性已成为大新测度社会、构想历史的(价值)标尺和寄寓,这话绝不过分。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女性的命运史、关系史,包括她们与男性、家庭、同伴、自然的关系。大新写出了一道色彩斑斓的女性画廊:除了《湖光山色》里的暖暖外,还有荀儿(《走出密林》)、荞荞(《伏牛》)、环儿(《香魂女》)、盛云纬(《第二十幕》)……她们虽然大都遭际不幸、情路坎坷,但无不顾盼生姿,真性流露,光彩照人。这恍若“世外”、“例外”的书写,莫非得自南阳水文地理的“天启”、“真传”,就像江南作家写女性,一出手便不同凡响。无独有偶,大新的同乡先贤姚雪垠也是个写女性的高手,诸如《李自成》里的慧梅、费贞娥,《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罗兰等,均让人难忘。
《湖光山色》起首有个细节,大概能解释故乡的水文地理与大新的女性刻画之间的关联。那是关于暖暖的来历:娘在丹湖畔意外产下一个女婴,仓促中奶奶用湖水给婴儿洗身子,娘怕孩子冻着了,不停呻唤:“暖暖,快暖暖!”女主人公的名字即由此而来。作者还借当地一个法名天心的和尚之口补了一笔:“这娃娃特意挑在此处入世,怕是今生要和这丹湖相依了,命里注定多水,日后,会滋润土的……”这愈发强化了暖暖与水彼此映射互文的感觉,暖暖分明是水的精灵。不仅如此,水的明澈、润泽与灵动亦渗入了小说的肌理。《湖光山色》分六章,以五行立章名,首末章名都是“水”,一个生于水又终于水的文学世界。它亦可看作大新钟情于水、立足于水的文学告白吧。
一个人与故乡的牵系以及他受故乡文化影响的强弱,撇开潜移默化的方面,还有个主观态度的问题。相对来讲,后者更为关键。很少能见到比大新更具故乡情结的人了。自18岁参军离开河南,他的口音就没变过。到北京这么多年,大新最爱看的还是《南阳晚报》,问他为何不看别的报纸,他淡淡一句:“那是人家的。”普通话也未见长进,偶尔冒点阴阳平上的普通话,那个别扭!还是说家乡话吧。一口道地的南阳话,被大新讲得温煦而自信。
南阳处在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界地带。楚文化天马行空的浪漫精神与中原文化经世致用的理性内涵,在大新身上均烙下了印记。从1979年发表首篇作品《南方来信》以来,大新一直笔耕不辍。虽未大红大紫,也算收获丰富。有件事略可一提,20年前,大新耗时十载的三卷本长篇《第二十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入围茅盾文学奖,从初评呼声高最终却出局,他的反应很平静,就像无意间鞋带松了,系上再走便是。迄今为止,大新的创作按题材可分三类:南阳盆地小说、军旅小说和城市小说。这跟他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致、呼应的步调。其中一贯的现实主义不仅体现在笔法、方法上,似乎也体现了他对自我的交代、打理和要求,是一种坦诚、务实的本色预设。无论数量和质量,盆地小说在大新这里均居首位。《第二十幕》、《湖光山色》都属于盆地系列,前者记述古城南阳一个丝织世家在20世纪的沉浮变迁,后者聚焦曾在北京打工又折返南阳故里的主人公暖暖,从她白手起家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的奋斗经历与情感挫折中透视改革三十年来农村的变化得失。惹人注意的是,暖暖所在的村子就叫楚王庄,而她命运的起落波折也注定跟楚长城(一个显明的荆楚文化的借代)的现代发掘与重识认定绑缚一道。小说设置了一个外来的考古学家谭老伯来充当暖暖与长城之间联系的桥梁:谭老伯和之后络绎不绝的研究者纷纷留宿暖暖家,让她蓦地意识到巨大惶惑的商机,尽管她的第一感觉是,这墙头已经毫无用处了。
读大新的作品,第一印象是,碰到讲故事的高手了!他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依托于一个或几个完整的故事,故事就是他的小说立场与叙述原则,以不变应万变。对于作家时时面临的“写什么”、“如何写”的难题与焦虑,大新的表现要坦然笃定得多。在被他的故事拉近、吸引的同时,又感觉一丝不安、不足:如此写去,是否传统、老派了呢?讲大新文学“单纯”(另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评论字眼)的人,我想原因主要在此。小说不该仅是故事吧?但就大新这边亦可反问一句,撇开故事,小说还能是什么?是个性?是自我折腾的深刻?抑或捏腔拿调的出演?
此处涉及到大新文学构思的基础或曰虚构的边界问题。大新的创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和标志着“文革”结束的“新时期”并辔而行。事实上,这也是他创作随性发挥的激情时代。大新对复杂人性的刻画讲求,他的作家使命感,他对善的呼唤和顽强的理想色彩,无不与“新时期”倡导的人道主义、“大写的人”天然相应。或者说,是“新时期”激发了大新的文学“天性”。其时,各种现代思想、理念及写作技法纷纷涌入,作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恨不得有个百般消化的“铁胃”。大新按理也该沾点“现代气”,但他的汲取却相当克制。简单说,即“故事为体,技法为用”,上来就是洒脱沉稳的“拿来主义”。我很惊讶他对现代诱惑、传染的“免疫力”,不是一朝如此,而是一直如是。倘非出于思维的隔阂,这就当属于“内功”的境界了。我以为,中原文化中理性实用的基质——特别是讲求人情伦理、礼仪和合的一面——于此发挥了重要的镇定、过滤与净化作用。
如果说典型的现代作品会给人以分裂、痉挛、酷派的刺激,多少有些神经质,那么大新作品的底色则是健康、和谐、向善的。即便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仍不脱此底色。他明明察觉到了某种不安危险的人性因子,但却不会穷追猛打。像吕道景的性别错位(《银饰》)、郜二嫂与独腿老公及任实忠间的三角畸恋(《香魂女》)、暖暖丈夫旷开田在饰演村庄离别戏(一种用来招揽旅游的古装表演)里的楚王赀时所产生的角色恍惚和帝王欲望(《湖光山色》),等等,这些细节大可放手写去的,探入无意识的深渊,搅个天翻地覆;但大新的笔触却止于含蓄与暗示。这是审美,亦是为人。我们在此可体会到本能朴素的“善意”、切实温暖的“礼仪”以及中原文化的调谐与自律、体面与禁忌。说白了,人谁没个脾气?再怎么着,轻易也不要撕破脸揭人皮,以和为贵;那些下意识乱糟糟的念头,不是长性,写了也没劲,任它去吧……这种书写在文本局部可能牺牲了些“过瘾的深刻”与“沉溺的跌宕”,但观察的“视界”却由此廓大敞亮起来。各种关系、诸多力量均被观照到,那是古典、整体、有机的把握与呈现。感觉《湖光山色》具有历史的气度、格调,即由此而来,虽然此书篇幅不大。那个自称乡村拯救者、宛然是资本教父的薛传薪(省城五洲旅游公司的项目开发经理),就是一个新颖别致的力量发掘与形象塑造。薛传薪告诉暖暖,如今发展农村,关键看它有没有“被看”的价值。此话一度成为暖暖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理论依据。于是,丹湖的绿树青山、宁静的村落,相对原始的耕作方式以及当地的楚国文化遗存等,都被充作或妆点为“看”的材料。这仿佛是城市对乡村的格外眷顾与帮衬,系乡土跻身现代的绝佳方式,孰料“看”来“看”去,竟“看”出了皮肉生意,端丽的乡村(连同它的文化、历史)真要沦为娱乐现代的妓女么?
《湖光山色》写的是改革浪潮中的当代农村,这对作家来说属于难啃的骨头,因为离得太近,分寸不好把握,抒情、审美不好展开;更棘手的是,如何写出当代农村的历史?它的常与变体现在哪里?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大新的处理举重若轻,那就是故事。确切讲,他把常变探讨、历史压抑的紧箍咒化解为楚王庄年轻女子暖暖的奋斗传奇。一切都是在暖暖交往的可能性、可行性中自然照面、展开的:除了狂妄自负的薛传薪,还有地方权力的代表,村主任詹石磴、凌岩寺慈悲的天心师傅,那个曾经深爱暖暖最终又伤她极深的旷开田……等等。
就大新而言,文学对历史的感知、显现与传达,不是像茅盾那般通过阶级归类、各就各位的强悍运筹与概括,它取决于世事洞明的睿智、容让与承当。这是中原人的文学信条,既固执,又博大。熟悉大新的朋友常说“大新人好”,这里还可加一句:大新人好,笔法周到(道)。
在《漫说“故事”》一文里大新提到,他的文学启蒙得自幼时乡间老人们的“说瞎话”,那一个个多彩动人的瞎话故事开启了他的文学梦。“故事是小说的母亲,一个做儿子的,倘若他身上没有母亲遗传下来的任何特征,他恐怕就不是亲生儿子。”这略感过激、情绪的话表明,故事之于大新,绝不仅是叙述的手法、惯性或偏好,亦是存身之道,是一个作家被抛向世间的“天命”格局,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能如是,必须如是。在故事的运作与延续(包括那看似平实的讲述语言、节奏及向往)中,大新捍卫了对乡土记忆及地方文化的牵系与忠诚,这或可提炼、简称为中原“人情”、“人道”。当然,捍卫的目标与结果中,也包含了自我人格的统一、笃实与纯粹。
读大新的小说,常会想起古老、睿智的说书人。事实上,大新文学的存在,也的确为这种久违、传统的“中国之声”在现代续留了一脉香火与奇迹。有件事值得一提,大新的军旅作品比较少,这是本职工作、必须的文学任务,但他似乎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切入军旅题材,见诸文字的多为散文和短篇小说,最具影响的军旅长篇要属《战争传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了。从题目上即可看出,只有依托于传说、故事、说书人的语调,大新才能焕发出会心、独特的文学风神。小说开头的“告白”证实了这点:此书旨在研究明朝中期的北京保卫战,但“我”依据的并非通常权威的史书方志,而是从民间听到、搜集的口头传说,它们“有趣”而“逼真”。在记录传说时,“我”只做了些文字的加工修正,将其更换为常用的当代词语而已。这不正是说书人的形象吗?不仅是《战争传说》,大新的其他作品里亦能感觉到类似说书人式的主体在场与调度。小说整体叙述与人物内心独白在言语风格、口吻上相对一致的质朴明快,不断印证、加深着上述感觉。它们被“讲述下一步”、“说此后怎样了”的故事驱动融合起来。个性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整体”。对故事整体的优先照看不仅是文学审美的选择,亦透出中原人个体生存的文化“矩度”与“本分”,那是千百年来中原文化对有序、和谐、大同社会强调、熏陶的结果。对故事的圆满化诉求也是对社会的承让与参与,对他人的包容与呵护。它务实而内秀,理性而亲和,浪漫而有度。
其实,《湖光山色》又何尝不像“传说”呢?暖暖的降生,丹湖上的鬼雾以及那弥漫全书的楚王赀的幽灵,在在提示着“传说”的特质。小说明明写的是近在咫尺的当代史,却又带着传说的味道。这种杂色与斑驳本身,实为作家的地方历史感与文学感的标示与佐证。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当代”客体,历史是浑然的。对当代的追踪、记事,也是凝望、抚摸传统的契机。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能接通二者的“故事的小径”,文学的魅力与慰藉就在于此吧。对古老说书技艺的承继或借鉴(有意无意的),让大新在当下的职业承诺(军人)、文学创新以及他的中原素养、故乡皈依之间找到了平衡、安和与踏实感,写作由之延续下去。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