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在中国的可能
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前后由《人民文学》杂志倡导出场,区别于“虚构”,也区别于传统意义的“报告文学”。“非虚构”强调文学书写和反思当代生活现场的能力,也强调知识人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这就要求写作者即“行动者”。所以,所谓的“非虚构”是精神站位、进入路径和文体、修辞的合体。
而现在“非虚构”显然已经出圈,大众传媒把所有标榜“记录”的都增容到“非虚构”之中,包括日志、真实故事、 素人写作、短视频等等。国民以空前的热情记录生活投入于宽泛意义的非虚构生产,即便它们对真正意义的审美创造并无多少建树,但一些记录个人生活史意义的写作实践可以作为观察时代风习的样本。
在“非虚构”被增容和泛化的当下,需要重新回到2010年前后倡导“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原点,在“非虚构”的汪洋大海中澄清和强调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审美创造的“一种”非虚构。这是一种有难度和门槛的写作,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专业的深度调查为抵达真实和真相提供了精神、路径和方法,但它们对世界和人性复杂性的勘探,以及修辞和文体又是“文学”的。
更重要的是,以文学而论,被寄以厚望的“非虚构”能不能凿穿文学和中国现实秘道?能否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所谓中国“非虚构”既指当下中国现场,也是指一种进入中国现场的实践性文体;而“非虚构”中国强调的是立场和路径,就是以“非虚构”这种直面现实方式来把握、理解当代中国。在2020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郑少雄、非虚构平台“三明治”主理人李依蔓、媒体人吕正,带来了他们对这个主题的实践与思考。
——主持人 尹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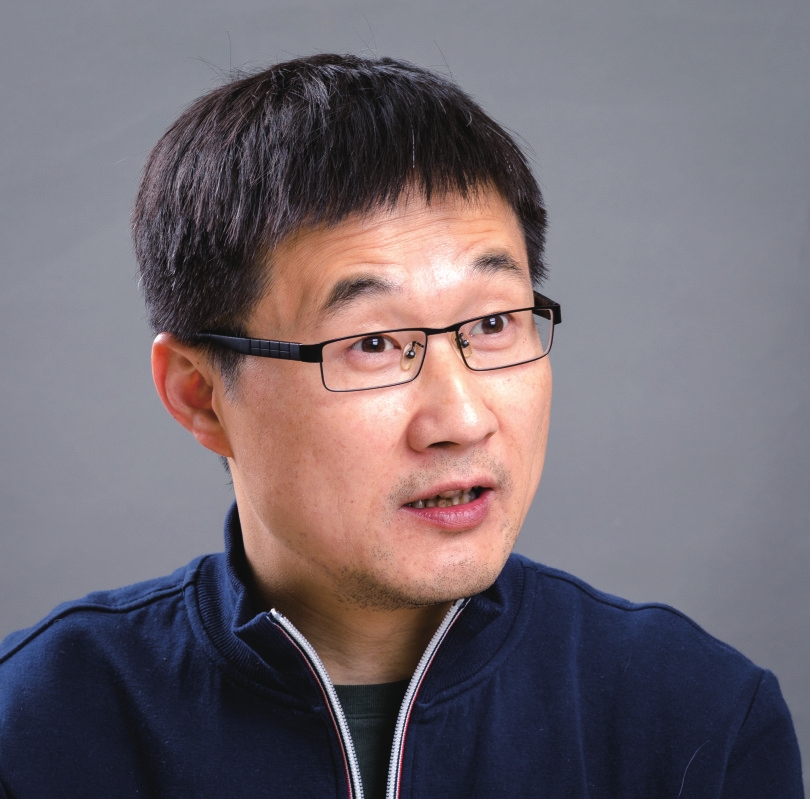
《瞻对》:关于非虚构文本的人类学见解
郑少雄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来讨论“非虚构”写作问题,和学科间相互启发的需要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关注阿来的写作。我自己做过康区土司研究,写过一本《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展开研究之前,当然已经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书稿完成后我意识到阿来很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框架。但在我的书里,阿来是隐匿的,甚至都没有作为参考文献出现过。为什么人类学者不能坦承文学的贡献呢?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我后来相继做过一些对阿来的再阅读和写作,算是迟来的致敬。更何况,阿来其实还是一位对民族理论、政策和实践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瞻对》出版后,他与一位主管民族政策的高级干部有过一场对话,曾经引起很大反响。
《瞻对》是阿来最著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2013年《人民文学》非虚构大奖的颁奖词说:“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申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这段话涉及了“历史”与“文学”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做是对非虚构文学之历史功用的肯定。
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到非虚构作品《瞻对》,在阿来笔下,康区土司除了在小的尺度上,相互之间合纵连横、征战杀伐外;在大的尺度上,既有依赖、协同内地征剿西藏的一面,也有与西藏联手,共同对付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面。简言之,土司及其追随者是一些钟摆人,善于在政治结构中间拿捏、回旋。民国时期前辈学者林耀华、马长寿、陈永龄等人也尝称嘉绒在汉藏之间“首鼠两端”。虽然这个框架并非阿来首创,但是通过虚构及非虚构写作,他把这个双向互动过程铺陈得非常磅礴、精细。可以看出,其一藏族内部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其二就像阿来曾强调的,“作家表达一种文化,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当然,近年来国内人类学也已经较多实践王铭铭等人所推动的“关系主义人类学”了,可见阿来的直觉和眼界具有学者式的精准。
阿来用近似纪年的手法记述了清廷发动的七次瞻对战争。从乾隆开始,就要依靠西藏地方政府助战,到了全书用力最著的贡布郎加叛乱时期,更是依靠藏军才最终平息,因为支付不起西藏军饷,而把瞻对赏赐给西藏,在康区地面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政治局势,一直到清末川边新政以后才由中央直接设县治理。我们看到贡布郎加既挑战西藏的权威,又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而受到贡布郎加欺凌的其他土司和百姓,在打箭炉清衙门告状未果,便又向西藏争取噶厦政府的干预。可见阿来写瞻对,包括余下很多篇幅写整个康巴,都是把它放到清代开始的整个区域性政治局势中、相互关系中来写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框架完全经得起学术检验。
有些评论认为,从《瞻对》所使用的正史材料,主要是清代官方档案文书的真实性上看,是历史的、非虚构的;而从对材料的文学化组织和运用方式来看,则是主观的,小说家言的。这个见解固然不错,但是他们还认为,因为阿来同时选择了地方笔记、方志、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材料,所以更显出虚构的特征。这个说法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在《瞻对》中阿来虽然努力深入田野、兼听兼信,但实际上帝国档案被广泛采信,民间材料则被贬抑;另一方面本质化了历史,对历史学来说,任何材料都是有意义的,核心在于如何展开“文本分析”,发问的落脚点在文本“到底想说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前后延续了200多年,但在当代瞻对口传材料里,几乎所有事迹最后都错误地叠加在贡布郎加一人身上,他也被称为恶魔或护法神,有各种暴力神异的传说。显然,这些材料并非事实,而且从叙事方式来说是反逻辑的。阿来将之称为地方的“叙事迷宫”,造成“时空交错的魔幻之感”,以此来说明藏区的落后、循环与历史停滞。但反过来,从藏族历史叙事风格来看,把恶魔收伏为护法神,意味着藏传佛教征服原始苯教、教化藏地全境的过程;与此同时,强调贡布郎加对佛法僧三宝的不敬,对瞻对来说,也是在表明一种宗教和政治意义上的地方性和多样性,这是一对永恒的纠缠和张力。本地材料显示,瞻对上中下三个土司家族都是从一个叫喜饶降泽的僧人开始,跟随西藏的八思巴去北京觐见忽必烈,由于在忽必烈面前展示了独特法力,受职回家,称为“瞻对本冲”,这是瞻对地名的来历。这个起源叙事相当精巧,隐含的真相是,既有佛教化过程,也有与西藏及中央王朝的直接关联,且这种关联是等级性的。这个结构也分明地显示了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说的“英雄祖先”和“兄弟祖先”历史心性的结合,加上关于瞻对“夹坝”(劫掠)的描述,反映了藏区较为恶劣的人类生态。而口传资料对贡布郎加传奇的反复强化,反映出来的现实是,在国家政治一体、藏区文化相似性之下,中心与边缘、民间与庙堂、朴蛮特质与文明教化之间的辩证距离。尤其在历史上藏区双重多封众建的背景之下,这种塑造地方强人和主体性的叙述结构就更明显。
理解非虚构写作需要分辨事实、真相和现实。王明珂指出,事实是真实存在的;真相是为事实所做的注解或进一步的描述,是事实与现实之间的交错关系,是主观、模糊以及饱含争议的;现实则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的、受政治权力建构与维持的人群区分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习俗、常识、社会规范以及审美观。现实让事实(或者非事实)产生社会意义。
一直以来,许多评论者都纠结于阿来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但评论者未必注意到的另一个维度是,阿来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变化。通过仔细梳理,我把阿来创作史约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作为藏族作家的阿来;2000-2008年退守到康巴、嘉绒本位上;2008年以后倾向于强调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些时间节点是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构成的,个人身份认同也并非瞬息剧变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对混杂的。《瞻对》是第三阶段的作品。从阿来自己的表述可以看出,写作本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并防止内部(族裔性)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削弱多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所以,阿来固然也批评王朝和国家的种种不足,但主要还是针对旧时代政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从而对比并反思新时代以来的成就。因此就文类的选择来看,采用“非虚构”形式是明确地表明历史是不容虚构的。在这里,非虚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进一步说,就论与“非虚构”最直接相关的事实层面来看,叙事尺度的选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阿来说自己连导演都不算,最多只算是舞美师,其实是暗指自己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他只设置时间和空间,而不干预人物和事件。但从空间尺度来看,写瞻对战争如果只写到康巴土司的内部关系,或只写到川藏之争,或者像《瞻对》一样最终放到中印英俄的区域世界关系中来谈,产生的历史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时间来看,正如王明珂举例的,美国“历史”是从印第安人、“五月花”、非裔、或是亚裔到达美洲写起,台湾“历史”是从原住民、闽粤移民、或是“国府”迁台写起,尽管都是事实,但其导致的历史记忆和对当下族群关系的看法,会大相径庭。《瞻对》叙事是截面式的,开篇第一句“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无疑已经奠定了笼罩性的帝国(国家)视角,自然也就易于最终推出一切都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总而言之,就如海登·怀特提出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或者后现代人类学所反思的“作为诗学与政治学的民族志”,既然历史学和人类学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关于真实性的质疑辩难之中,我们对文学非虚构与否的关注,可能更应该落脚在共情地理解文本背后的作者面对何种真相与现实、尝试传递何种历史观念上。

个人生活史的写作实践
李依蔓
10年前,三明治还是一个独立媒体平台和创新人群社群,三明治这个名字来源于“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这个发源于美国的文化概念,形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但我们把“三明治”的意涵扩大到家庭结构之外,指代一种像三明治一样的“夹层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同时体现在个人生活和时代特征上。
10年前,30岁左右人群出生于1980年左右,他们的成长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之后是国企改革或企业重组引发“下岗潮”,“铁饭碗”整齐划一和稳定的生活方式成为过去,技术引发的第一波互联网创业热潮刚刚开始,市场和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比父辈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可以选择相对安稳的生活,努力建立和维持“三十而立”的传统中产身份,但所受的教育和全新的社会环境又让他们不甘于此,于是很多人开始思考与父辈生活不同的可能性,并思考“我是谁”,要过怎样的生活,并尝试作出创新生活的实践。虽然这种实践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他们普遍处于一种“夹层状态”中,像一只三明治。当时,“三明治”提出的口号是“三十明志”,以个人生活史的写作实践,是用以“明志”的最主要行动。
最初4年,个人生活史写作的实践主要通过三明治独立媒体团队来完成。我们用人物报道、新闻特稿的方式,记录30岁上下人群探寻自我、生活创新和进行困局突围的真实故事和深度文化观察。但仅由团队观察并记录的人群和时代切片终究是少数,并且我们希望三明治成为一个“写作+行动”的充满变化和可能性的创新文化平台,让更多的青年人用写作来书写自己的真实生活。
从2015年开始,三明治的个人生活史书写实践从狭义的“我们写”变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我们写”,倡导每一个珍视文字和写作的普通人来写,试图呈现更多元的中国当代个人史和社会文化的切片记录。
我们通过这些写作者看到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面貌。有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比如中国人如何在非洲卖手机、缅甸华人的真实生活状况、一位跨性别者如何找到装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有关于年轻人生活选择的,比如两个年轻人决定合作生养孩子但不结婚、网络女主播的爱恨江湖;有关于家庭的,比如一位酗酒的父亲、一位和阿兹海默症斗争的婆婆、一个家庭20年的下岗人生。当这些写作者在写作时,就在进行一种温和的生活突围。
然而写一篇达到一定完整度的作品,对于未经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写作者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于是我们推出了更轻盈的、侧重社交的写作项目——每日书,每天记录300字,连续写30天。参与者可自由确定记录的主题,无论是写生活日常,还是写某一段重要的经历或故事。写作者们的背景非常多元,他们可能是媒体人、公务员、设计师、创业者、全职妈妈、老师、互联网运营、品牌公关、银行职员、咖啡师、医生护士……一位护士回忆2003年自己参加抗击SARS疫情的经历,一个民宿主人写下自己在家乡湛江硇洲岛开民宿的经历,一个妈妈写下孕期最后30天迎接孩子到来的心情,一个微信重度依赖者记录自己卸载微信30天的变化。
我们还发起了不同主题的写作工作坊,以及写作项目短故事学院,由编辑和写作者一对一地进行沟通并指导,帮助每一个想写自己的某段经历和故事的写作者,把一个想法落地成一个好故事。其中比较有话题性或者社会价值的作品,我们会挑选出来再进行编辑,在平台发布。
在三年来发表的短故事作品中,我们得以更系统地窥见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许多隐而未见的故事浮出水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作者们自我袒露和剖析的勇敢和坦诚所震撼。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发声,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故事都重要,有的对个体重要,有的有更大的在社会层面探讨的价值,让那些 “The Unrepresented Voice”(未被代表的声音)显露出来。写作这个行动以及它们汇集起来的声音,联结起了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面临着哪些困境?在三明治过去几年记录下的故事中,我们得以窥探到一些痕迹。
比如和10年前相比,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下更年轻的一代人,似乎拥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社会资源,有更多选择机会和可能,但他们更多地陷入一种原子化的孤独,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控制,这种控制来自于家庭,也来自于更强力、更无孔不入的资本和商业浸透。我们也面临着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撕裂,城乡的撕裂,阶级的撕裂。他们面临更频繁出现的无力感,虚无感,意义的消解,理想主义的崩塌,许多人缺乏爱与被爱的经验和能力。当被迫以成年人的身份面对社会时,很多人往往展现出一种未战先怯的姿态,典型的一些说法如“丧”、“社畜”,自我在社会的巨大齿轮之间变成了碎片式的存在,商业价值成了压倒性的成功标准。
写作者们在文字中展现出强大的自省感知力,通过书写去重新构建关于自我和生活的意义,去触发更多的行动可能。这些故事就是鲜活跳动着的时代脉搏。接下来,我们希望借助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个人生活史书写实践,继续对这一代三明治的心灵图景进行研究和分析,去不断提出问题,并尝试作出回应。
每一代人,都一定会找到和当下时代交手的方式。这一代年轻人也会找到不同可用的、好用的方法和路径,去达成对自我的梳理、确认、接纳,去和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连接,去生成更持久、更有意义和影响力的社会行动,去进行向内和向外的探索,去“突围”。而真诚地写下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形成一些相对完整而不是碎片化的叙事,可以是一切行动中一个有力的开始,也是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时间之河中身在何处的锚。

非虚构如何书写城市
吕 正
“非虚构”在中国这些年经历了横空出世到遍地开花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大家以前只喜欢看《动物世界》,人们在电视机前——隔一个安全距离看动物们厮杀、捕猎,一个画外音平静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很快我们变得不满足,要开始看《荒野求生》,看贝爷从飞机上跳下来,看人吃虫子……挺刺激的。
“上海相册”是一个很新的非虚构项目,首季创作在2020年8月间刊发完毕。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前,我刚结束在“武康大楼口述史”项目的工作。我在撰写“武康大楼”相关报道时,收到了老同事许海峰的邀请,他提议做一个城市写作与摄影交叉、跨界的“非虚构”项目,项目需要一位特约编辑,熟悉作家,懂图片,而他知道我一直在推动城市题材的创作。2020年3月,我们启动了“上海相册”,许海峰开始挑选摄影师的作品,而我开始向身边的作家发出邀约。
“上海相册”的第一期是作家于是的《天台造城记》和摄影师徐昕的摄影作品“the Metropolis大都会”。“上海相册”一共找了22位上海在地作家,根据22位上海在地摄影师每人一组的摄影作品进行创作。“在地”是指长期生活、工作、创作在上海的作家,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相册”也自带了创作者的时差感,摄影作品和文字是有对话和对望意味的。摄影师的作品本身创作跨越的年份非常大。有些作品是拍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也有些作品就是拍摄于2020年,包括新冠疫情中的上海。参加项目的摄影师普遍的年龄是“50后”,我们也有选择“80后”的摄影师马良、周仰,“90后”的摄影师徐昕。在挑选作家的时候,我有意识地选择“80后”、“90后”,也有“70后”。比如走走、于是、王若虚、吴越、栗鹿、陆茵茵、钱佳楠、三三、负二等作家参与“上海相册”的写作,他们中有长期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从事翻译创作的,也有专栏写作较多的。
这个项目没有那么多的官方色彩,更像是澎湃新闻和上海作协《萌芽》杂志艺术性的探索和尝试。描绘上海这个重要的命题,离不开摄影和文字共同的努力。许海峰和我一开始就想,一定要坚持盲写,作家是以“盲写”的方式进行创作的,作家首先并不知道拿到的摄影作品是谁拍的。作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理解或者想象自由发挥。有一位参加项目创作的作家叫btr,他本人很“跨界”,在后来的作家和摄影师见面会上,他揶揄“盲写”的行为很像在“相亲”,于是我们笑称我们的项目是“上海相亲”。而btr拿到的那组照片是关于上海的公园的,上海的公园非常出名的功能就是“相亲”,这是双响炮式的巧合。
我觉得,作家和摄影师的非虚构跨界合作,就像宇宙中的引力场,摄影师的作品先在那里,以恒星、星体做比喻,有光有热,那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需要意会的,那就像引力。作家的创作可以是如行星围绕,也可以如彗星,出发漫游。比如在面对摄影师朱锋的《上海零度》系列作品,作家王若虚写道:什么样的城市看不见呢?是未来的城市。城市会自我繁殖,自我膨胀,那些“生活开拓者”往往生活在都市的最外沿,你这一刻走过的荒芜和苍凉,几年后或许就是平地起高楼,或许就是灯火通明,就是交通拥堵。而过来人多半只会感慨昔日的苍凉,不会去怀念它。如果人类的基因里都有怀念它的部分,那么今天也就没有那么多城市,而是人人都想做个荒野猎人。这是他对摄影作品的个人理解。所以,在这个非虚构项目里,照片各有特色,文字也各有殊异,有的像读后感,有的像散文诗,有的像短篇小说。有些图文比较协调,有些似乎两不相干,谁也无法预料这个项目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然而这正是实验的应有之义:勇于探索,大胆尝试,用创造性思维打破画地为牢。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是“有趣”。几乎每个参加这个项目的作家、摄影师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尝试;其次是“距离感”,因为作家之前并没有看过这些照片,一些人觉得这是一次“实验”,更多的人说这是一次“冒险”。项目第一季收官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一场“握手会”,请大家交流创作感受。摄影师和作家相见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地试探。摄影师寻求的答案是:你读懂了我的照片没有?你是不是表达了我要拍的意图?当“解读”有可能等同于“误读”时,我想“有感而发”也基本等同于“跑题”了。正如作家三三在《异化,或时间秩序的重置》中说的:“这一瞬间不供应任何意义,仅作为一个停顿。樟树举着一身鳞片似的叶,由于风的参与,日光变得轻盈多动——当你凝视这一切时,你与这些日常景象的交流也投影到镜头里,而你的自我也留存其中。”
2018年上海双年展项目总协调、策展人施瀚涛先生谈到他对这个非虚构项目的理解,他觉得作家并不是以“评论”的视角去看待摄影作品,而是从“创作者”的视角进行再创作。“激发和刺激了不可预期的图片与文字的新关系,有着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虽然这样的跨界合作在其他地区国家有着很多版本,但落地上海书写上海城市文化,依然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希望“上海相册”可以成长为一个具有实验性的非虚构平台,给予读者开放性的阅读体验,让人各取所需获得更多的启发。我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有体温、有细节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