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耳《伐木之夜》:叙述者,声音和小说的真实
我一直坚信小说的真实性建立在叙述者的腔调上,而不是细节的写实。《伐木之夜》印证了我的想法。作者索耳曾在一篇创作谈《什么才算是“中国式细节”?》里提到两个具有等同性质的概念——“现实主义白描”和“中国式细节”,并区分了“中国式作者”和“译文读者兼写作者”的差异。他以“观看一件器具”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式作者’只注重其功用的现时性,而‘译文读者兼写作者’则深情款款地把目光回溯到它尚未被烧制好的泥坯的样子”。无疑,我站在“译文读者兼写作者”这边。
大部分以“中国式细节”构筑而成的小说,关键是“讲述”,而非“叙述”。叙述由叙述者引发并推进,是一种声音流,而讲述”则源自小说家的亲口发声,产生的是语意流。以某种程度上看,两者类似于能指与所指的差别。作为舶来品的小说需要一个叙述者,而非“讲故事的人”。这个叙述者既非小说家本人,也非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叙述者是由小说家创造、并区别于小说人物的抽象存在。小说的魅力源自叙述者,小说的真实性建立在叙述者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上。“中国式作者”写就的小说之所以凭“故事”及“讲故事的方式”论英雄,原因在于它发出的是小说家本人的声音。小说的“第一人称”讲述者是小说家本人的化身,这种书写方式类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模式,面向一群看不见的“看客”,小说家要做的是把故事讲得生动,足够吸引人,于是便产生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结构。它与“故事”最早的缘起——“围炉夜话”实际上没有本质差别。单纯靠“中国式细节”构建的小说很可能坠入为“写实”放弃小说本体论意义上无限可能的深渊。
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式作者”的小说如果在故事上不够精彩,讲述方式不够有趣,便有失却阅读价值的危险;“译文读者兼写作者”的小说即便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独特的叙述腔调仍然会吸引读者阅读,并令人为之着迷。贝克特的小说在多重意义上将传统西方小说的概念推进到消逝的极致,使用人物、情节等概念分析贝克特的小说,已经失去意义。如果说“马龙三部曲”的第一部《马龙之死》仍然具备可以辨识的情节——即便这些情节并不能带来阅读快感,已经减省到可有可无的地步——那么到了第三部《无法称呼的人》,情节彻底消失不见,只剩下自我反噬的叙述声音,沦为一部“无法称呼的小说”:一种从无中诞生又归逝于无的叙述,一种自我悖反的叙述模式:在句子的意义甫一生成的当下便否定它。于是整本小说只剩下一股声音流,一处虚无的荒漠。但是,贝克特的小说因此削减掉魅力了吗?没有。相反,因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放弃,小说变得愈加迷人。

索耳,1992年生于广东湛江,毕业于武汉大学。做过编辑、媒体人与策展人。 小说见于《花城》《钟山》《鲤》等刊物。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押沙龙短篇小说奖。
索耳的小说,其独特性正在于奇妙的叙述腔调。《伐木之夜》里的叙述者,我们对他的过往知之甚少——父母离异,与母生活,上海求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广东)看管荔枝园——但却极为迷人。角色的信息并不是支撑这部小说的必需,甚至具有推进力的情节也不是。索耳不惜用半本小说的篇幅打磨叙述者的声音,让读者持续不断地“忍受”他絮絮叨叨的折磨,他将精彩的叙事留到了后半部来展示。索耳似乎想以此辨认他的理想读者:那些只想读到一个精彩故事的读者因为忍受不了“我”的折磨早早投降,而那些挺住并沉浸叙述魔力的读者将在作品后半部中获得一个意外犒赏——原来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悬疑”故事,在陷阱与阴谋交织中,通过诸多谜团的铺设,借助主人公的行动一一破解。。
这种带有实验色彩的写法是对大部分读者的挑战,而将独有的滋味留给那些有着相同趣味的人。读者透过叙述者的棱镜望见了一处变形的隐秘角落,这个角落由小说家创造出来,里面没有所谓“中国式细节”的存在。同时,这也是训练读者,或者说培育理想读者的方式。《伐木之夜》前半部分基本上没有叙事的推进,但依然显出十足的魅力,那些用逗号分隔的长句子好似在优雅漫步。这种魅力来自叙述者絮絮不止同时带有自我反思意识的叙述,从而将平凡无奇的日常琐事和意念思绪变得意趣盎然。
《伐木之夜》依然给人感知上的真实,这种真实性源自叙述者对自我意识始终保持的真诚。可以说,《伐木之夜》里“对人类共性的厌恶”、“想逃离所有人”的“我”,仅对他自己负责。他没有向读者负责的义务。因此在很多时候,《伐木之夜》里的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但因为叙述者真诚地面对内心,从而感染了读者,读者愿意借用叙述者的感官和思维来认知叙述者眼中的外部世界,相信他提供并阐释的信息。这些信息无法被验证,与现实世界无关,只在小说文本中自洽。
《伐木之夜》不是那类复制现实、捕捉现实或反映现实的小说。小说虽然也离不开现实元素(词与物的关系),但从本质上看,小说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行,小说只需对自身内部的融洽性负责。这和电影如此相似,电影的真实性也建立在内在逻辑的融洽性上。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任何艺术都遵循着此条规律:在自身之内保持融洽。这意味着小说有时可以背离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譬如幻想小说或科幻小说,它们在对现实逻辑的背离中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某种的真实,原因正在于此。
现实所提供的无非是材料,艺术家的存在是再造可以令读者或观众感知、体验和思考的世界,从而让他们重新获得对现实的感悟。这难道不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现实世界中的人如同囚困于洞穴中的人,而一睹洞外风景的人之所以能获得新知,是因为他知道洞穴里的景象只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现实同样如此,无非看待外部世界的某种方式罢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无数种由感官触发的另类真实。这是艺术存在的价值,帮助我们更新在乏味无聊的日常生活中逐趋麻木的感觉官能。现实主义应该扩大它的范围,而不只局限于物像元素的写实。一旦说写实,似乎已经预先将现实世界设定为模版,但任何复制都无法超越原样。既然如此,为何不重新创造呢?
《伐木之夜》或者说索耳小说珍贵的地方在于,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并能够自我融洽的世界。思索诸如为什么荔枝园工人要和“我”作对,又是谁砍掉了荔枝树,蒋坤和蒋莎会是否同一个人吗,等问题便不再有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仍旧在借助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拷问小说家,由此取消小说创造奇特世界的魔力。况且,小说家实在也没有责任为小说是否“写实”做出解释。小说的真实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真实,这是小说为何一定要虚构和想象的原因:虚构为小说提供合法性,而想象为小说提供了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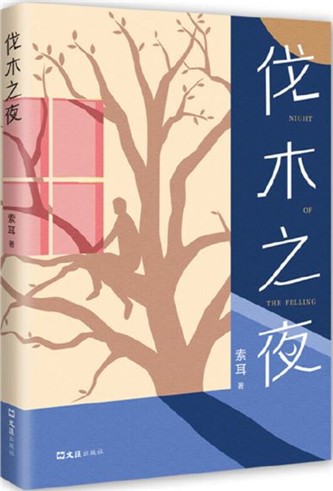
《伐木之夜》,索耳,文汇出版社,2020年7月
内容简介:我不能容忍别人侵犯自己,也不能容忍自己去侵犯别人,因此我远离人群,退出“当代生活”。毕业后,我勉为其难回到老家,为一个从无来往的亲戚看管荔枝园,尽管我对果木种植一窍不通。管理员的尴尬生活,在遇到钢琴师陆陆后起了变化。她才华四溢、神秘、孤傲,永远不可接近,她带来了一连串谜题,情妇、山洞、怪人……她让我意识到,这座荔枝园仿佛某个人窥视我的工具,只要置身于此,就会规训和改造这园子,同时不断被园子规训和改造。他无须时刻监视,这里每棵树都是他的监视器。一切都从踏入荔枝园开始,今夜,我要做点什么,让这一切在荔枝园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