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个虚化的家庭符号 ——读刘庆邦的《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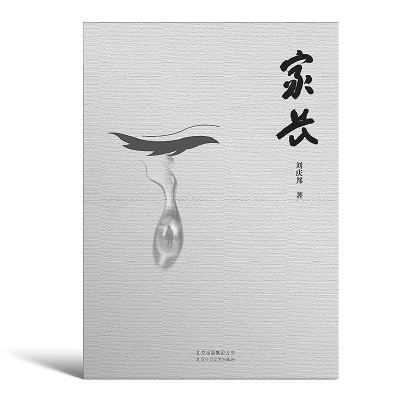
《家长》是一部有着痛感的小说,它将家庭的帷幔掀开,把教育的日常还原到个体身上,呈现了孩子身心的伤痛记忆。
在传统的文化视阈中,一个家庭的维系与发展往往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上。在这样的角色分工下,很多男性都天然地认为自己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是外出挣钱养家。因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很少会主动提供温情的陪伴与守望。
当我们度量与父亲的距离时,究竟该如何想象与诠释父亲的存在?刘庆邦的新作以《家长》为名,将视野转向当代家庭教育方面,揭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关系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小说中何新成一家从满是衰草的小屋走向视野明亮的现代高楼,这副光景的转变离不开父亲何怀礼在外不辞辛苦的打拼。父亲是何家赖以生存的保障,是座高大的、安全的、可以依赖的靠山。不幸的是,何怀礼不只是一座山不声不响地远远矗立着,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提供过正面的、具有父亲角色特征的家庭教育,他还将自己这座山横梗在儿子何新成的成长道路上,最终导致了家庭的悲剧。
在《家长》的开篇,何怀礼长年在矿上工作,“由于父爱的缺失,矿工的儿子总是跟爸爸有些生分,父子之间建立不起亲切的感情。”距离的疏远导致何怀礼退出了儿子的生活,对于儿子来说,父亲身份更像是一种威严的象征,一种既定的文化和心理事实,而不是一个有情感温度的形象。在这种疏远关系背后,还潜藏着孩子内心隐秘的跌宕。长期与母亲的相依为命,使这个家庭经历着“假性单亲”的境遇,孩子对于母亲有着更为依赖的情感,父亲的归来夺走了母亲的注意力和对自己的关爱,随之而来的是孩子会加深对父亲的排斥感。
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当何新成从封闭的乡村来到父亲何怀礼的身边,父亲本应带着孩子一点点感知广阔城市的模样,但在长时间的接触中,何怀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弥补因距离产生的亲情淡漠,仍对何新成的成长毫不过问。何新成的转学、升学、生活、情感,父亲几乎从未留意过,甚至连一丝涩重的柔情都没留给这个弱小的孩子,以至于何新成对于家长的定义也仅包括母亲一人。当母亲王国慧要求何怀礼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时,他着急地说:“孩子的事以前不都是你管嘛,开家长会的事干吗推到我头上!”何怀礼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完全将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妻子,拒绝主动承担、实施或者提供父性家庭教育。
《家长》是一部有着痛感的小说,它将家庭的帷幔掀开,把教育的日常还原到个体身上,呈现了孩子身心的伤痛记忆。何怀礼少数几次参与家庭教育,也只是以暴力的方式:归家探亲时,何怀礼因为学习的事将何新成痛打一通;搬进城里的新家后,将何新成视为朋友和情感寄托的猫咪从窗户摔下,使得何新成“精神的某个痛点受到了刺激”。孩子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关注,所得到的反馈不过是令人难过的训诫惩罚。
卡夫卡曾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说:“你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干成了一番事业,因此,你无比相信自己的看法。你坐在躺椅里主宰世界。你的观点正确,任何别的观点都是荒谬、偏激、疯癫、不正常的。”执着地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力似乎是很多父亲的通病,不仅仅卡夫卡的父亲如此。当父亲们成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力量标志,他们无法容忍孩子挑战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们常常用暴力手段来打压孩子。何怀礼也是如此,当他加入家庭教育时,更倾向于用“自己的意志”来判断对错。父亲以一种入侵者的角色进入何新成的生活,以“父亲的想法”来裁定他的世界,留下的恐惧、焦虑或者身体疼痛都成了何新成的心理创伤。
当孩子定义父亲这个角色时,总会想到父亲形象是代表力量和英雄的,也总会将这样高大伟岸的形象倾注在对父亲的崇拜和幻想中。对一个男孩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也更愿意将自己的父亲视为榜样。但在任何意义上,何怀礼都没有成为儿子的榜样,相反,在何新成走向疯癫的人生道路上,他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允许关系不正常的男女在家中短住,引起了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对男女关系的困惑。因为父亲的疏忽,何新成在未成年时期看到了“生活片”,但是父亲“不但没有感到内疚,没有自责,反而把这件事当成儿子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当成了儿子的一个把柄,他要抓住这个把柄,跟儿子交换点儿什么。”何怀礼并未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一再用错误掩盖错误,使得何新成对“性”产生了幻想,这种“性”的误区成了何新成爆发癔症的导火索。而当何新成撞见父亲“出轨”后,何怀礼竟然教儿子对母亲说谎;在儿子不经意向母亲坦诚后,又骂儿子是“叛徒”。何怀礼作为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却能够在儿子面前继续心安理得,他认为自己应该凭借“父亲”这一血缘身份得到儿子的无限宽宥,而从未考虑过自己早已把所有的不公和苦楚都推给了一个孩子去承受。
孩子的情感观念和家庭教育,本来就是一个镍币的两面。在家庭教育中,孩子的情感问题长期得不到关注,会导致他们的身心健康出现问题。而在错误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由于情感上的压抑与缺失,也更容易走向极端。何新成作为这种家庭教育的牺牲品,无法直面自己的父母,只能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压抑过去的不幸记忆,无意识中留下了许多心理创伤,这些创伤最终导致了他精神崩溃、癔症发作。
没有人察觉到大厦将倾。在何新成精神失常后,何怀礼也只是以宿醉来抱怨天命不公,父亲终究没有在黑暗中递给何新成一双温暖的手。而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承载着无数周围人羡慕眼光,也在表面泛着全家福欢笑的金光褪去后显出陌生的狰狞来,何新成的精神癔症和畸形的婚姻带来的苦果正在何家不断生长。当何新成的婚姻出现问题后,何怀礼将所有麻烦都丢给妻子王国慧处理,自己却守在矿上的小屋落得清净,父亲的角色被一次又一次的逃避彻底消解。
有意味的是,在故事的尾声里,何新成也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却不幸地成了上一代的复制品。于何新成而言,他的孩子也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他对自己父亲身份同样没有任何认知。他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毫无作为。最终,何新成在精神失常的焦虑中,因为儿子的哭声干扰了自己,亲手掐死了儿子,也结束了自己的父亲身份。
刘庆邦始终关注底层生活,他的笔下一直流露着极其敏感的人性关怀,当他把笔触伸入家庭教育问题中时,也能捕捉到这个时代里或隐或现的父亲缺席家庭的教育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从家庭到社会,大多将父亲的爱认定为一种内敛克制的表达,仿佛冰山只露尖尖角,或者有时甚至是在海平面以下。但也正是这种对父爱的刻板认识,让很多父亲以沉默来回应家庭内部发生的一切,殊不知这份无言只会加深父子关系间的沟壑。而文学的意义也正在于,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对人们所熟视无睹的一切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让更多的父亲和家庭重新审视对孩子的教育:父亲不应该对父子之间的割裂浑然无视,只有付出真正的爱,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幸福。
《家长》也再次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父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父亲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赚钱机器”、一个退化了的家庭符号、一个神圣而虚无的身份,我们不应否定父亲对一个家庭作出的经济上的贡献,但是孩子需要的远远不止于此。父亲角色应该是一个男性对于具体家庭成员抱有温情与爱意的存在,他的这份情感基于日常的陪伴和生活的琐碎细节,是一份任何时代都可以亭亭如盖的人类普遍情感。也正是如此,定义父子关系的应该是真实的情感,而非无法选择的生殖与血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