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边界”创作的活力 ——羊子新作《祖先照亮我的脸》及其诗歌创作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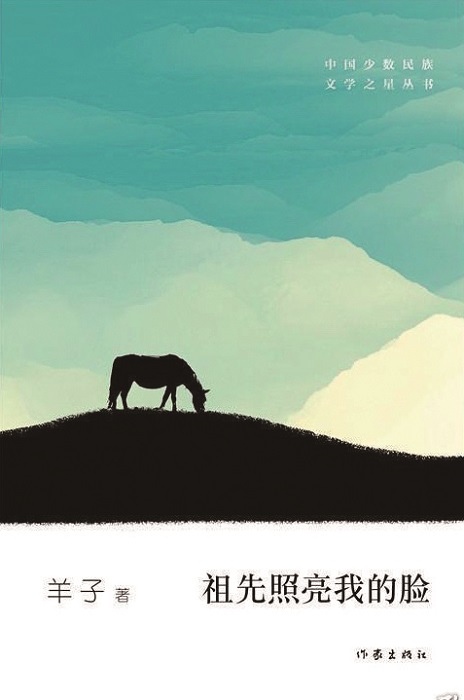
羌族,是中华民族中颇具边界特征与古代意义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华诗词歌赋中对“羌”的称名、写意、道具、场域的吟诵,可谓脍炙人口。“羌”既是古代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一种泛指,亦是今天川西北龙门山脉高原河谷与高山地带羌族同胞及其属地的确指。羊子是当代羌族诗人中的代表,曾以《神奇的九寨》歌词广为人知,出版作品多种,获奖多项,有长诗《汶川羌》,诗集《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一只凤凰飞起来》等。他曾代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等,不仅将羌族服饰形象展现于世界文学诗歌同仁眼前,更将羌族歌吟与史诗唱响到大洋彼岸。
《祖先照亮我的脸》(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是羊子最新结集出版的诗集。一如既往,他在歌颂羌族历史开拓与形成的同时,对当下羌族人民的现代性话题与生态描述,亦更多用笔倾心。羊子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双重属性,将诗体的自由率意与歌词的韵律整饬接洽融合,如《在雨中》的勾画和《梦见你》的遐情——
步步高升着海拔,接近一种可能的神话,/诗的培育,与世界的等待,/伴云升高的我是雨中开放的兰,/把心打开,盛装从天而来的甘露。/太阳的温度藏进心窝,/你跨出我的疆域,/你游入你的宇宙,/你在你的掌心喷薄光华。
他将地理边界感受效应尽情挥洒,亦将古老与现代、现实与禅意(神韵)熔为一炉,奋力追求一种创新的艺术境界与诗歌的大写意,如《岷江的高度》——
山峰因为海拔的剧增而躲进云层,/传说因为考古而深入历史,/岷江因为文明而牵动西南的神经/……/从掌心孵化的第一粒雪水开始,/注定了四海归一的使命。
在民族大融合、世界呈现同一化趋势质地的今天,羊子紧紧抓住他的“汶川羌”这一意象,把他的诗歌风帆驶向远方海洋,不畏急流险滩、断崖深谷,也不迷地平天阔、江流纵横。
有学者谈论道:“由于方言的日渐式微,民间提供给作家的只能是无限的新鲜出炉的词汇以及口语的感觉和腔调,而不可能是一种语言的形式。作家的地域身份已不再鲜明和确定,沙汀、老舍那样的方言文学家已不复再现。”羊子同其他当代作家诗人一样,无疑也有“语言焦虑”的问题,特别是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同胞,如何在非第一母语的抒怀中,独辟蹊径,保持长春树一样的生命新鲜体验激情与艺术感悟探索。这是羊子在诗文中亦多次流露的思想话题。他的《祖先照亮我的脸》,充分集中地表现了这一尝试努力,既不失民族自身的特色,又能与世界大潮接轨,从而达到一种“通畅”“广义”的语言艺术境地。
“素面朝天,群山感受着内心的灿烂。”在长诗《群山微笑》的结尾,羊子如此总结与收笔,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他的世界情怀与边界原乡意义。对于岩浆岩和沉积岩地域特征表象突出的昆仑山脉岷山段,“素面朝天”这一句形容可称神来之笔。他诗集中常用“海拔”这个修辞,从高处凝望历史、凝望现实、凝望世界,也是他这一部诗集的精神聚焦与会心所在。这恰好体现了如黑格尔所谓:“人类必须先有对于‘高等存在’的意识,他才具有真正恭敬的观点。”古羌民族从远古走来,披荆斩棘,战胜险恶的环境,定居于岷江高山峡谷,成为长江源流的坚强捍卫者与文明守望者,倘没有一种英雄气质与诗人的乐观恬静、大度情怀,不会有那么多赞歌,也不会有羊子这样的诗人、歌者。
无疑,岷江流域处于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民族走廊”之中,是南北多个华夏边疆民族的交会地带,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汇,彼此影响与融合,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等形态的文化质地,在羌族居属地得到充分表现,形成守真抱朴与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羌汉文化交流更为频密,中华民族的世界走向益加明显。羊子的创作相当具体地展现了“边界写作”的风范与典型性,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呈现共生、多元、交映的文化特点,从文艺的 “边缘”优势与生存空间方面实现革新、突破与扩展。他的创作手法往往骈散交替、歌诗互融、长短句不拘一格,恰到好处的地域物名、文化援用与想象,在现代汉语的表现体系中点染传神,突出表征意义,如前引以及集子中俯拾皆是的例子。
书写古羌民族,书写家园故里,更是书写人类。羊子的诗歌处处渗透着这样“直达人类”的愿景。正如丹纳《艺术哲学》所指希腊艺术:“一方面受着素材的性质与领域狭窄的限制,一方面这些限制也增加了塑像的庄严……使端庄和平的塑像在殿堂上放出静穆的光辉,不愧为人类心目中的英雄与神明。”赞美祖先,赞美雄山大川,赞美劳动,以及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新时代意义,羊子的诗,始终洋溢着“高地”与“静穆”的光辉。
从羊子恬静浪漫的《静静巍峨》《一只凤凰飞起来》到沉痛执著的《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再到着重歌咏民族精神、世界情怀的《祖先照亮我的脸》,羊子赤子之心、人间大爱,力求以多元素与多样性的诗歌形式呈现。有学者认为“边缘”的活力更多来自原始性、流动性和混合性。除此之外,羊子诗歌也多有现代性的追求,他不仅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诗歌题材中的危机意识包括人间灾难反思、人性异化焦虑、女性生存处境等,在他诗歌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与采写。羌族人崇尚“万物皆有灵”,地神、树神、火神、天神、山神等,无一不是他的书写对象与题材,这种“神性思维”与象征显然造就了羊子诗歌语言的特殊“灵性”,从而形成多重隐喻的关系,如诗集《一只凤凰飞起来》中《桃坪有水蜜桃》——
这一天,神龛上的祖先下来了/脚踩祥云的菩萨来了/房屋每一块石头,灵光四溢
人神合一,祖先也是羌族的守护神,对祖先的想象与追忆,无时不展现羌族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冀。古羌民族的集居地由河西大地而茶马古道,始终处于文化交汇、穿越联结地带。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的影响下,羊子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与世界知识追求,写作中博采众家,不设边界,技巧日趋圆熟浑成、得心应手。
每一部诗集,诗人羊子都争取以创新追求以及诗行的“陌生感”带给读者新的体验,正如《汶川羌》中《汤》所写:“中国的汤包罗万象。”在“边界写作”试验中提供超越性的视野,在民族文化寻根中把握民族精神发展方向,如《祖先照亮我的脸》中《请让开一下》:“你们成堆成堆的都市和类都市,/也请让一下,/请支持我满怀成就回到三千年前”。又如《不能让胯下的骏马失去主人》:“这一群让主人飘逸的骏马。/我看见。让主人失去了身份。/让方向失去了意义。奔驰。奔腾。”古今穿越、文体穿越、语言穿越、地域穿越甚至人神穿越,集中构成羊子诗歌显明的艺术风貌,即“我思故我在”的现代体验。
在多民族文化的“边界”地带,放笔写作歌吟,实现 “跨文明”“多样性”优势化的书写,呈现出羌族民歌多声部一样的特质,既是羌民族身份的自书与张扬,也是对时代高地多元文化的借鉴汲取和探索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