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儿科幻的“当代”观察
中国当代文坛上,科幻文学无疑是一个新崛起的热点。中国当代文坛上,儿童文学也无疑是另一个热点。近年来,二者正逐渐呈现出热点的“交集”。儿童文学视野中的科幻文学,被简称为“少儿科幻”。有观点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起点,就源于儿童文学,因为我国“当代”视野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即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幻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如郑文光 、童恩正等,最初都是被纳入儿童文学视野、参评并获得儿童文学奖项的。这一问题,此文中暂不追溯,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肯定的: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对少儿科幻的关注从未缺席。
一、中国少儿科幻的“当代”开启
1955年,是一个标志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健康开启的关键年份。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与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促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个蓬勃发展期。这两个重要文献中,都专门提及了少儿科幻的创作问题。《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中提出:“中国作家协会还应当配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组织一些科学家和作家,用合作的方法,逐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一些优美的科学文艺读物,以克服目前少年儿童科学读物枯燥乏味的现象。”《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中提出:“作品的形式和体裁应该丰富多样。不仅要有小说、故事、诗歌、剧本,也要有童话故事、民间故事、科学幻想读物”,并且专门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发展为广大少年儿童喜爱而目前又十分缺乏的童话、惊险小说、科学幻想读物、儿童游记和儿童剧本。”在这两个重要文献中,为少年儿童读者提供科学文艺读物,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前者使用了“科学文艺”,将科普读物涵盖其中;后者则专门侧重了少儿“科幻文学”这一文学范畴。50年代,郑文光、童恩正的科幻文学创作,高士其的科普童话、科学诗创作,都为中国当代少儿“科学文艺”的文体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文学样例。
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领域全面复苏,少儿科幻文学也出现了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掀动的巨大科幻创作热潮,少儿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幻电影、科学戏剧、科学相声各种文体百花齐放。叶永烈曾经撰文《儿童科学文艺漫谈》,对中国当代少年儿童科学文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的创作发展,以及逐步形成的文体分支,做了非常全面、非常有针对性的论述。但是这儿童文学领域内“科学文艺”的“繁荣”态势,也迅速陷入1983年“精神污染重灾区”论争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步走向沉寂。但是,从国家层面,广义的科学文艺或狭义的科幻文学基于儿童的意义,从未被忽视。以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历程看,自1986年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就设置了“科幻小说”奖项,郑文光的《神翼》获奖。之后,因受到科幻文学创作整体进入严冬期影响,科幻小说创作出现断层,优秀作品匮乏,二、三、四届的该奖项均空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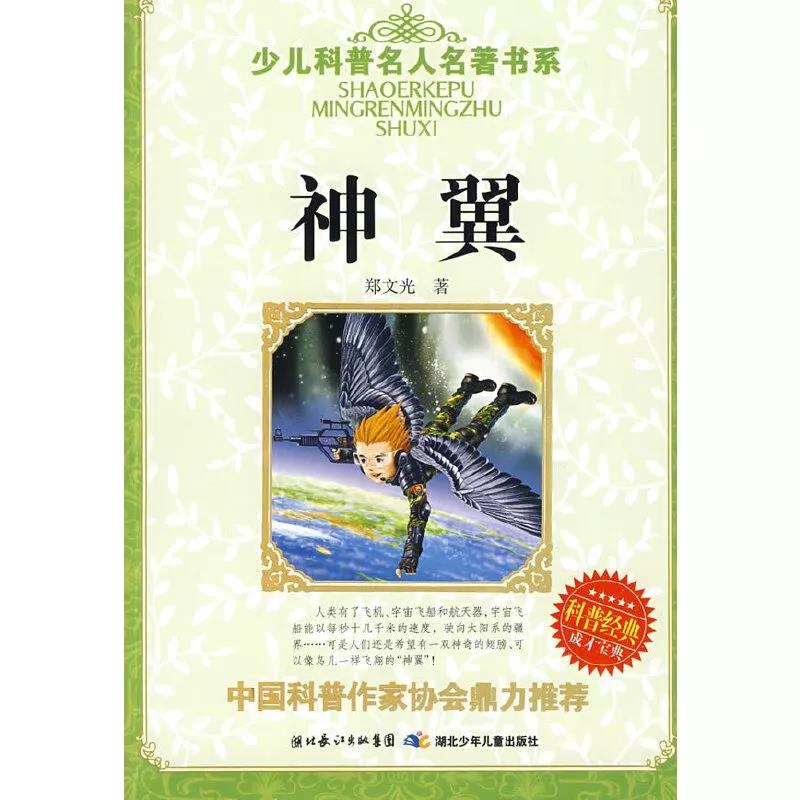
郑文光《神翼》
二、21世纪少儿科幻的“身份”之思
新世纪以来,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整体加速发展的时代相呼应,中国少儿科幻文学应进一步得到重视成为共识。2001年1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主席团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2001)》,十条具体举措中,就专列一条:“与中国科协密切合作,做好文学家与科学家优势互补的联姻工作,共同促进科学文艺创作的发展。”世纪之交,少儿科幻文学的创作样貌也逐渐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少儿科幻电影《霹雳贝贝》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张之路,在这一时期的少儿科幻文学创作极具代表性,他的《非法智慧》《极限幻觉》《小猪大侠莫跑跑·绝境逢生》先后在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1998-2000)、第七届(2004-2006)、第八届(2007-2009)评选中获“科学文艺”奖。第六届评奖中,还有赵海虹的短篇科幻小说《追日》获“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科学文艺”奖。
进入21世纪,世纪初的科幻文学研究具有了理论属性,这归功于吴岩教授在这一领域的专注研究与基础性深勘。科幻小说的概念阐释、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等问题,都以论文、专著的形式,构成了中国科幻理论体系的逐步建构。张之路在2000年全国科普创作及科学文艺研讨会上发言《繁荣科学文艺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4月17日),分析了阻碍科学文艺发展、造成优质的科学文艺作品严重匮乏的原因,既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场论争带来的创作桎梏,也冷静分析了少儿科幻创作自身对“幻想”的放纵。对于科幻的“身份”问题,尤其是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曾引起广泛关注。葛红兵撰文谈《不要把科幻文学的苗只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中华读书报》,2003.08.06),王泉根撰文回应《该把科幻文学的苗种在哪里?——兼论科幻文学独立成类的因素》(《中华读书报》,2003.08.27)。这一论争聚焦于科幻文学的未来发展,也显示了科幻文学圈内部对少儿科幻部分地存在排斥心理。
显然,将科幻小说的发展,放置在儿童文学的视域,是我国当代科幻文学发展极度“边缘化”时期的一种过渡性举措。但科幻文学的“常态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必然是少儿科幻。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外在呈现”的一致性,源自“幻想”的艺术形式,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内里”解决问题呈现出的一致性,则在于“朝向未来”的精神归属。儿童以其身处衔接人类世代代际传承者、维系人类生命与人类文明延续者的特殊身份,被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赋予了与希望、与未来的最密切关联与最决定意义。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拯救者或者说拯救的希望,均同一地指向了儿童。历代文学作品常常在极度的绝境中、在极致的恶面前,寻求以儿童的天真纯善的真童心,唤醒成人世界的浑噩与迷失,如泰戈尔、华兹华斯的诗作,诚挚赞美“儿童的天使”,感叹“儿童是成人之父”。科幻文学常常在假设了地球即将毁灭的绝境中,描绘如何保护儿童,如何保存人类文明。多代、多位作家的科幻作品中,绝境中的突围,也恰恰是靠突破思维定势的儿童、无惧无畏的儿童达成的。如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王晋康的《宇宙晶卵》等作品中,儿童是未来走向的决策者,儿童是可能灾难的突围者。因而可以说,无论是外在幻想色彩抑或内里精神气质上,二者都呈现着某种天然的、密切的关联性。
面对当代文明,努力与少儿科幻“撇清”,已经是一个“过去式”,就像努力与儿童文学“撇清”已经成为“过去式”一样。问题的背后,其实同样包括对待儿童、儿童文学的态度和认识。随着人类文明前行的脚步,对儿童文学的狭隘化、“小儿科”的界定已经逐渐驱离人们的头脑,儿童文学所独具的文学意蕴与价值已然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优质的儿童文学所标识出的儿童文学艺术标准与创作难度,也已然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为儿童创作科幻文学,也已然不是羞于启齿之事,而是如何驾驭之思。
三、新时代少儿科幻创作的多维拓展
新的时代呼唤优质的、丰富的少儿科幻作品。人类文明走入当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了儿童的日常生活,并构成他们生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有着与这一代儿童最为亲近的心灵距离,这就决定了他们紧密追踪的兴趣点不再是过去的田园、乡村,而是时刻与他们发生关联、带来改变、产生共鸣的科学技术。因此,少儿科幻“并成”为“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子门类,存在着巨大的阅读需求。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来,少儿科幻文学受到的重视度与实际的创作量,都呈现出加速度趋势。仍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考察,第九届(2010-2012)、第十届(2013-2016)两届儿童文学评奖中,均为少儿科幻文学设置了两个奖项份额。刘慈欣的《三体》,胡冬林的《巨虫公园》,王林柏的《拯救天才》,赵华的《大漠寻星人》这四部获奖作品的科幻样貌非常丰富,也表征了少儿科幻文学创作逐渐多点开花。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科幻类获奖作品
科幻文学领域内,董仁威、姚海军、吴岩等均已敏锐感受到了少儿科幻的应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开始在“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设立“少儿科幻”奖项,成都《科幻世界》承办的国际科幻大会开始设立“少儿科幻”分论坛,促成了在科幻文学圈内部,对少儿科幻的关注与聚力,一批坚持从事少儿科幻创作的作家有了创作归属感与交流的契机。另外,一个面向未出版作品的“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自2013年启动,至今已坚持6个年头。因其中专设“科学幻想”类型,成为一个“少儿科幻”原创力量汇聚的平台,6年间问世了多部具有标杆意义的少儿科幻作品,时间穿越、多维空间类型的如王林柏的《拯救天才》、马传思的《奇迹之夏》,生态毁灭类型的如左炜的《最后三颗核弹》、马传思的《冰冻星球》,人类进化、人机共处类型的如王晋康的《真人》、杨华的《少年、AI和狗》等,文化反思类型的如赵华的《除夕夜的礼物》、源娥的《时间超市》等,极大丰富了少儿科幻文学的创作样貌。
王林柏的《拯救天才》,以时间穿越的科幻模式讲述一系列拯救天才的故事,而这种穿越型幻想因为建立在了广博的文化史、科学史基础之上,因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穿越类故事,严谨,丰满而睿智。马传思的《冰冻星球》《奇迹之夏》,以饱满的信息量与具有信度的科学思索,既开拓着孩子们的想象视野,又传递了以科学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更藉此展现出了知识的魅力。王晋康的《真人》,以前瞻性的科学想象,假象了在科技高度发达并完全介入人体甚至参与到人类的繁衍的时代,“人”之为人的标准将向何处去。杨华的《少年、AI和狗》对少儿科幻创作“硬科幻”作品的尺度与技法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实践。作品选择了A.I.(人工智能)这一备受科技界关注的前沿科技之一写入少儿科幻,在少年与A.I.的人机对话中,A.I.传递了大量航空航天的科学知识,科学成分饱满扎实。赵华《除夕夜的礼物》,有着较为成熟的“科幻”思想方式,作品透露出来的对科学与人类、人类与可能的外星生物的“关联形式”的思考深度,是对少儿科幻普遍流于对科幻元素概念化植入的有力反拨,是对一些少儿科幻创作以科幻为“摆件”实则大展魔法类型想象的简单化操作的有力反拨。
上述作品,均以较高的品质获得了不同奖项的重复认可,包括王林柏的《拯救天才》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马传思的《冰冻星球》《奇迹之夏》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今年获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少儿短篇金奖的秦莹亮的《百万个明天》,作品推想了A.I.进入人类生活后可能面临的人类如何对待智人的情感问题。描写细腻,情感动人,既描绘了人与智人相处的百万种可能,也在人与智人的交互中,给予了“爱”的定义外延的百万种可能。该作品随后荣获了当年度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多维度的获奖,显示了各奖项与活动对少儿科幻发展形成的凝聚、推动作用,也印证了当代少儿科幻正在迎来文体的日益自觉与创作中的创新意识。
四、面对新的机遇更需新的警惕
在当下这种时代趋势和主流社会的关注下,可以预见,少儿科幻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潜藏、散在的创作力量正在不断聚集,“跨界”创作的趋势也已逐步呈现。但是于整体科幻文学发展与整体儿童文学发展而言,当下少儿科幻创作的发展仍是相对薄弱的。这就需要一种严谨的、努力的创作态度,去补充、拓展少儿科幻的艺术样貌。
在儿童文学领域对少儿科幻的屡次表述中,交替出现了“科学文艺”与“科幻文学”,实际显示了“少儿科幻”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儿童文学视野中的“科学文艺”,是广义概念,内含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普故事、科学诗、科学剧、科学绘本等。“科幻文学”则指称了狭义的少儿科幻,不包括科普类读物,单指文学类读物。二者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此处暂且不谈科普类少儿读物的创作标准,单就狭义的文学领域来看,当代少儿科幻创作在逐渐升温的同时,也呈现相关的、出需要警惕的问题。
部分少儿科幻创作对“幻想”的运用,存在“杂糅”。作品的“科幻”含量稀薄,而是杂糅了“奇幻”“玄幻”“魔幻”以及“打怪升级”等“类型”元素。这种杂糅,降低了少儿科幻创作的难度,也势必导致少儿科幻面目的模糊。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达科·苏恩文谈对科幻有一个界定,科幻是“以疏离和认知为宰制”的。“疏离”强调了科幻作品需营造陌生化的生存环境、科技背景,“认知”则强调了对所构成的陌生化的给予建立在科学前瞻性假想基础上的理论解释。“疏离”和“认知”并济,方可称为“科幻”。“魔幻”或“奇幻”等,则是可以摆脱因果链推导的非逻辑性幻想,因疏离而产生的陌生化是有的,但其中的幻想是不需要寻找某种科技理论的自洽,甚至往往不需要解释的,是所谓从心所欲,以“奇”制胜。摆脱因果链的幻想,在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童话创作中,是经常被运用的。

刘慈欣科幻童话《烧火工》绘本
科技理论在科幻作品中的支撑力与密度,将科幻文学区分出“硬科幻”与“软科幻”。科幻文学作家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速度,开始慨叹科技前瞻的难度,慨叹真实的科技有时甚至反超了科学幻想,一些新生代科幻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加稀薄的科幻密度,更多朝向某种人文性的思索,甚至有青年科幻作家用“稀饭科幻”来进行以自我指称。那么,以此类推,少儿科幻的科幻味儿,是不是可以再稀释一点,达到“米汤科幻”即可?于是,披着科幻外衣的魔幻小说、披着科幻外衣的童话故事,成为少儿科幻创作领域随处可见的作品样貌。
与科幻圈内曾经对少儿科幻的回避不同,这是另外一种对少儿科幻创作的“轻视”,是一种轻视“科幻”的创作态度。少儿科幻虽然因为面对儿童受众这一读者定位,在科技理论的密度与难度方面,需要有意识地做一些降低,以确保儿童阅读的可读性与适读性,但是,少儿科幻与科幻文学一样,同样追求幻想内里科学精神的灌注,同样应该承载对未来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走向、包括对宇宙命运、生命关系的前瞻与思考。少儿科幻应该始终对科学幻想与童话幻想、神话幻想等幻想文体的杂糅保持高度警惕,应该始终有明晰的创作分野。虽然上述幻想文体共同拥有想象的特权,但童话、魔幻等是可以随意驾驭因果关系的任意结合式想象,科幻却必须具有科学推演的认知基础。二者杂糅的创作,势必对小读者造成“误导”。久而久之,极有可能触发20世纪80年代“精神污染”论争的再度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