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一位普通读者的当代长篇阅读手札
毕业后一直在文学出版社工作,因近水楼台之便,着实看了许多当代长篇——从建国后算起至今不下百种,但自己亲手责编的却极少,除了一本张怡微的《细民盛宴》,以及与同事合编的几本外。加上自己也没写过长篇——无论经验、精力和时间都力有不逮。因此此处的发言,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毫无责编滤镜、也并无同行相轻之意普通读者的阅读手札。虽是札记,大抵也会有轻重取舍,比如已经有很多重磅评论逐项分析过的长篇,在此即使提及,也尽量从略;有些我觉得很好的长篇,但没得过什么奖项的,反而忍不住因私淑之心多说几句。
首先想说的是《看上去很美》。王朔这本书上世纪末被长江文艺做成了畅销书,我读本科时被拍成电影,我还暗自觉得演方枪枪的那个小朋友有点像我小时候——后来才发现更像王朔本尊。但上中文系读研才发现这本书业内口碑不高,包括自诩王朔忠粉的一位师姐也说“就这本看不下去”。2010年夏天,我无意间在帮忙整理仓库时翻到一本敝社版,当时就站在那里手不释卷地读完了,简直回到了初中时站在书店看金庸的瘾头——看完了还不算,还立刻匿名上豆瓣写了书评。

“关于童年我们都有话说,可是说的都不如王朔多。朔爷的记忆力真好,让人不能不怀疑他这部半自传真是一半一半: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现编。但编的是记不真切的,字里行间笼罩的却是一种确凿存在过却又极难再现的旧日氛围。能将光阴的颜色、温度、声音唤回一二,就具备杰作品质,正相当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里著名的马德莱娜小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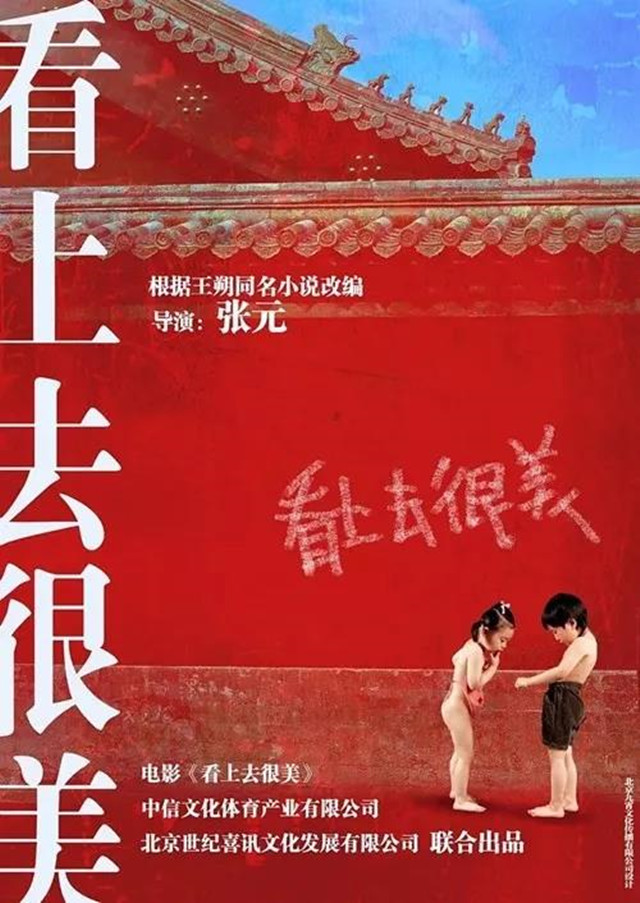
本书大概是王朔前后期风格截然分野的里程碑,也是他自认为一直最想写的书:“这本小说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或者干脆说一直用大脑细胞在写……当我构思第一个短篇小说时就同时构思这本小说了。这期间,发表了很多小说,但这本书一直在脑子里丰富、发展、完善,总也不想拿出来。有时似乎觉得眼下的一切写作都是为了这本书练笔、摸索技巧、积聚、寻找最佳结构和出发点。有时有些绝妙之念舍不得使在别处,就替这书存了起来。有时黔驴技穷一狠心用了这书的片段去支撑另一个已发表的小说,用过之后懊悔,痛不欲生,有如旧时代妇女失去贞操。这是关于我自己的,彻底的,毫不保留的,凡看过、经过、想过、听说过,尽可能穷尽我之感受的,一本书。”
即便是“普通读者”,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由作者自述牵着鼻子走:尤其小说家通常都被目为说谎高手。但王朔这段话说得太好也太恳切,实在舍不得不全文摘录。事实上,即便文学圈遇冷,普通读者却仍然买账:豆瓣《看上去很美》前后几个版本加起来有近一万五千条短评,综合给出8.1的高分。一个看似唯心的事实:多数写作者是清楚自己什么题材必须要写、不写会死、因此也最有可能写出巅峰水平的。危险却在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尤其是畅销书作家,“遇读者不淑”、口碑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更大。或许正因这本书的滑铁卢,对王朔彼时如日中天的创作造成了某种刺激:好比一生中最珍视的东西终于小心翼翼地端出,却被抛扔在地。此后,他似乎再没写出过影响力可与过去相比的作品,更完全地放弃了对所谓纯文学界的攻城略地;虽然之后的《与我们的女儿谈话》也相当真诚。但那样私小说意味太强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普通读者》里借约翰逊博士之口开宗明义:“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同时,我以为,也应该相信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自我判断。倘若多数普通读者的看法和作者自判不谋而同,那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
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我读第一部《人面桃花》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参加了由邵燕君师姐主持的当代最新作品论坛,诸多师友都说这本写得好,我却稍持异议;毕业后到人文社工作,才因借调到新闻出版总署,有幸在人教司办公室里读到当年出的第二部《山河入梦》,一路揪着心读下去,读到最后姚佩佩在流亡过程中给县长谭功达写信,情思缠绵悱恻催人泪下,又如鬼神附体长歌当哭,才觉得当真是好,读后久久不能平复。几年后又读《春尽江南》,虽技术更趋圆熟,却又失了当年《山河入梦》的惊心动魄。和好些人聊过这三部曲,发现中文系之外的“普通读者”多持和我一样的看法。有一次偶然有机会和格非老师闲聊,才知道三部中他自己最满意的也是这本。当下大喜。
同理还有金宇澄先生的《繁花》。这部沪上奇书我至少看了两遍半,两遍是看文艺社的纸版,半遍是上弄堂网试图比较在网上发表的原初版本,略做一点考证功夫。不上弄堂网则矣,一上则发现坛子里贴了书出版后《人物》杂志的一个访谈:“某日下午6点,金宇澄贴上来一大段,瞎眼老太太黎老师讲尽了年轻恋爱直到晚景凄凉的一生。一段三千多字,金宇澄当天下午在家里写完一下子就站起来,内心极其激动,暗自叹道,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了!看客和爷叔的反应同步,平时潜水的网民纷纷浮起来,大呼不得了,这个好小说要好好庆贺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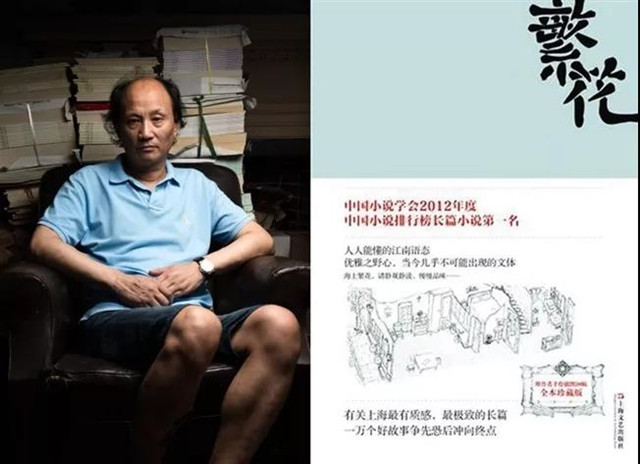
看到这段访谈时毫无预兆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无他,《繁花》成书后凡总35万字,开门见山:“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使人欢笑。”而后男女登场,机锋交错,高潮迭出,异彩纷呈,千回百转,但我全书唯独看哭的一段,正是瞎眼黎老太这段。
这当然是自己作为普通读者有幸和创作者的状态高度共鸣的两个最愉快的例子。其他时候,当然也并不比其他普通读者更了解实情,只能姑且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另一本读过两次以上并次次为之落泪、也同样众望所归地斩获“茅奖”的作品,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前几年一个中篇写到友情,还专门又翻箱倒柜把这书找出来重读。除了再次感慨于刘震云的确是最了解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的最聪明的当代作家外,更留意到小说呈现一种高度自洽的闭合结构,以及说中国人不信宗教,文本却以极接近宗教的虚无主义宿命论展开,最终却仍然缔造了某种坚实。上部“出延津记”里的杨百顺生来百事不顺,跟随传教士老詹信基督教改名吴摩西后境遇方好转,不料又痛失养女巧玲,后半生离开延津,寻亲漫无所得;下部“回延津记”,则交待了几十年后巧玲被三个人转手从河南卖到山西,嫁人生下儿子牛爱国,牛爱国同样是为了寻回与人私奔的老婆,宿命般从山西回到延津。这一出一回,正如批评者马云鹤所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中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语言。”也有很多评论者留意到这部作品的拟话本叙事方式,颇似河南话里的“喷空”,言语如水随物赋形,从一个人到十个人,一条线到百条线,看似千头万绪,实则成竹在胸,最后提纲挈领,一段锦绣遂成。同时,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炉火纯青的白描手法,比如“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平等身份中的不平等寥寥数语即跃然纸上,而这正是小说肯綮之所在:人与人相交,无非声气相投,一句话找得着另一句话。此外,书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诸事都有来龙去脉,“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看似世情小说典型写法,却又因为作者笔力强健,话题泼得出去也收得回来,虚实相继,有无相生,反而具备了不可多得的现代性。这本长篇的成功处第一在于语言,第二在于结构,第三则在于人物塑造: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百色千端,样样具备。但人人找不着那句最要紧的话,一个人的孤独遂变成千百万人的孤独,因此“一句顶一万句”。

女性长篇小说写作者,首先绕不开的,当然是王安忆。我从本科读《海上繁华梦》开始,渐渐习惯了安忆老师的声口腔调,那是一种看似去风格化的纯熟风格,就好像任何事都可以用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处理妥帖,并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说出,这种能力有一点像胡兰成转述张爱玲自叙:”我问爱玲,她答说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当然后半句就又跌入不知所云的“胡腔”:“她是使万物自语,恰如将军的战马识得吉凶,还有宝刀亦中夜会得自己鸣跃。”总而言之,意思差相仿佛,我反正是很少在安忆老师的小说里看到“为难”的,仿佛一切答案天然就在那里,一个上帝视角的人悲悯地俯瞰众生,诸事尽在把握。她是很少使用限制视角的,虽然技术也很娴熟。看她和张新颖老师的《谈话录》,写作生涯中也并非没有遇到过瓶颈,但终于极具有职业精神地将之克服,有生之年并仍然在不断拓宽写作领域。这种精神是后辈需要学习的。撇开几个极精彩的中短篇不谈,她长篇里我最喜欢的一本,却是《启蒙时代》而非获了“茅奖”的《长恨歌》,这或者也和我当初阅读它时的生命阶段有关:研究生毕业,刚接触到很多书,囫囵吞枣地读了,却又好读书不求甚解,只能靠将来的漫长岁月一点点克化这坚硬的精神食粮,有一点像这本书里的舒拉:“舒拉比舒娅小四岁,这样的距离正好够舒娅每一步都走在舒拉前面。以她激烈的性子,是感到不公平……这就已经不是她和姐姐之间的事了,好像是和时代之间的事,那就没法怄气了。其实呢,是成长的事,是舒拉特别的渴望长大。就因为这,舒拉给自己的成长造成了许多困难。她没有同年龄的伙伴,同龄的伙伴统统不入她的眼,她觉得他们幼稚。这只是她的看法,实际上,她可能比她的同龄人心智更不成熟。因为违背自然,不能顺畅发展,她就很孤寂,这孤寂促使她更加感到不公平。所以,她永远无法享受她的年龄里的时间,尽是不高兴了。就在这种孤寂之中,她的又一项功能则兀自发达着,那就是思想。……她还小,还没有开始生活,思想却已经预先工作。”我直觉这里面的舒拉,以及文革末期其他陷入青春期迷惘的年轻人,是比王安忆其他任何一本书里的主人公都更靠近她自己的,那种十几岁的“启蒙时代”如饥似渴地渴望知识,却又对波澜诡谲的外部世界迷惘胆怯的心情,没有亲历过的人绝写不出来。这样看来,无论一个写作者如何笔力千钧,她仍然有自己最可能写好的部分,那就是曾亲历过的,真实矗立的生命的房子,只有不吝拆毁这房屋,才能得到更扎实的人生材料用于建造更坚固的虚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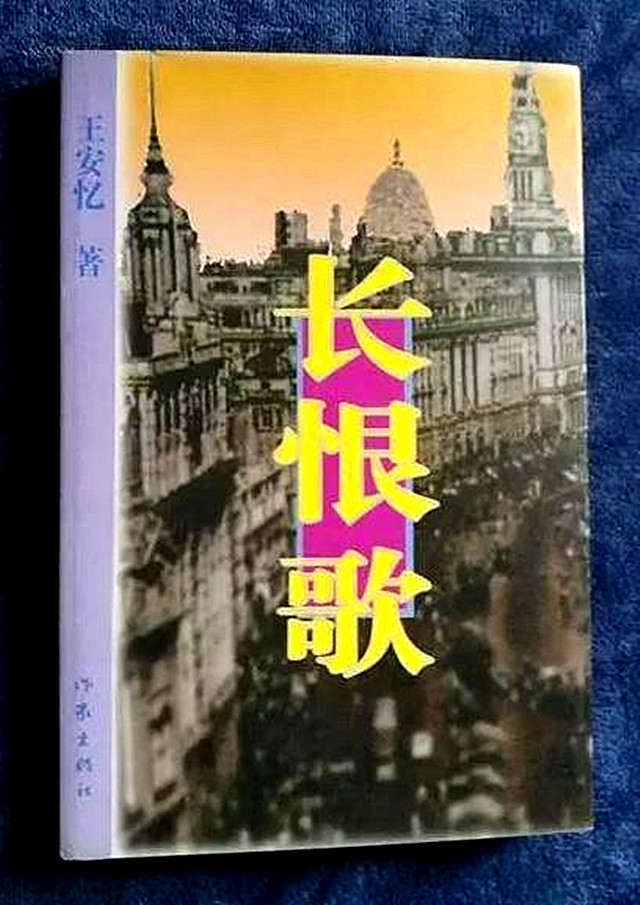
这样的例子,同样可见于严歌苓的写作。作为文学界公认的劳模,每两年稳定出产至少一部长篇小说,是唯一可以和贾平凹老师相抗衡的杰出女性代表——一支笔也是千伶百俐,写啥像啥,但读得多了仍然还是能发现,“穗子”系列是她反复思量至于烂熟、也最可能花样翻新的题材。我最喜欢的严氏作品是《小姨多鹤》,事实上,从《第九个寡妇》开始,严歌苓已试图走出“穗子”系列所处的写作舒适区,开始拥抱和处理更广阔的时代素材和涉猎更丰富的领域,当然也不是没有过明显的败绩:比如《补玉山居》和《老师好美》。《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不过不失,到了《芳华》,我才终于觉得状态上佳的严歌苓又回来了。今年她新出版的动物故事集《穗子的动物园》里,最动人的也是有关“穗子”的几篇,虽然基本都是非虚构——这是否说明了,长篇小说写作当真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生命经验?以血肉铸就、汗泪浇灌过的城墙砖石,才是拆不完也用不尽的;当然也不限于此,还需有力量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
说回建国七十年经典长篇。据说近十年来,每年都至少出版两千种以上长篇作品,委实浩如烟海,此处举例的当然都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都是曾给我个人带来过切实感动的作品,也就不惜挂一漏万——说着又想起了好几部喜欢又来不及说的。比如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徐皓峰的《武士会》,于晓丹的《1980的情人》。还有一部可能没什么人知道的,于仁秋的《请客》,我的同事杨柳老师是这本书的责编,封面上只简单地写了”美国生活,中国味道——夏志清教授生前为本书作序。《请客》:恒常的日常”。我总是极佩服前辈高手写文案的言简意赅,根本没有时下连篇累牍词不达意的腰封病。一部长篇最重要的关键词也许就那么一两个,最多一句话,像我这样百般譬喻还非得引文才能说清楚的,都实属能力有限。
还有一种长篇,思想虽谈不上任何现代性,甚至写小知识分子不避卑琐,作者和人物的距离贴近到近乎自曝己短,但叙事与人物塑造方面的才华却显著到教人过目难忘,实在是天生吃小说家这碗饭的人——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便是阎真的处女作《曾在天涯》。巧的是这本书居然也是半自传体。因字数已超过一千五百字,在此就不一一赘语介绍,如信得过,还请亲自下箸——这些书虽看似小众,市面上也都还是能找到的,很多也刚出了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