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珊诗文集:明亮的白光
袁绍珊的诗文,读之如各色光线汇聚,缤纷陆离,最终交织成明亮的白光。这种阅读体验也如同观一人或观一城,诸多维度和可能性被囿于一个整体,交锋,更重要的是交融。

袁绍珊
袁绍珊出生成长于澳门,其诗与文亦有着与澳门近似的品格。在散文集《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中,袁绍珊讲述了她所感知到的澳门。灵感的起点有些发生在澳门本地,有些则在异乡,内部关照和外部视角并行,从一丝一缕的所听所看、所思所想中,玉虎牵丝般地钩钓着澳门的街巷桥梁、节庆文化、市集山水。碎石路、超市、美甲店、小吃店、电影院……文章有追忆、有反思也有讽喻,琐琐碎碎地读下来,拼图般地构建出一座城,这“城”浮于现实的上空,成为生动可感的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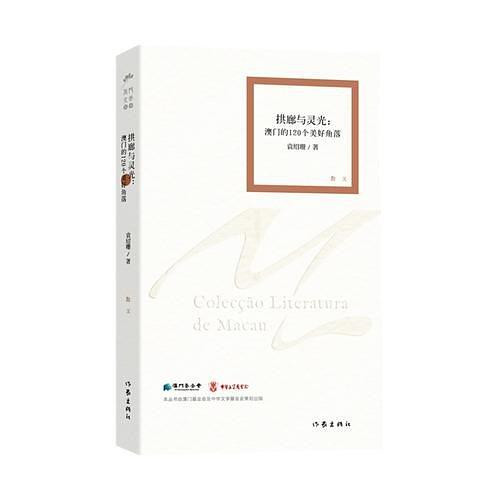
《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
澳门是一座多元并存的城市,面积虽小,但绝不单调。作者比喻澳门为“葡国鸡”,“杂中国、葡萄牙、非洲、印度等多种烹调特色于一炉”,其本土文化便是“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就地取材的再创造”(袁绍珊:《澳门,看得见的城市》,选自《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澳门包容共生的城市品格内构出袁绍珊诗文的独特结构,文化壁垒、时空界限、物与人的分野皆于其笔下被打破。
在袁绍珊的诗作中,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人与外部时空的互相建构,作者在描绘事物时,常与人的身体或情绪相映照,反之亦然。道教学说中有“身国”的说法,在诗人笔下,人的身体与空间魔幻地糅合为一,身体成了最复杂的空间,多样文化在此涌动合一。故而在此以“人”作为譬喻,从人与时空互文的角度试析袁绍珊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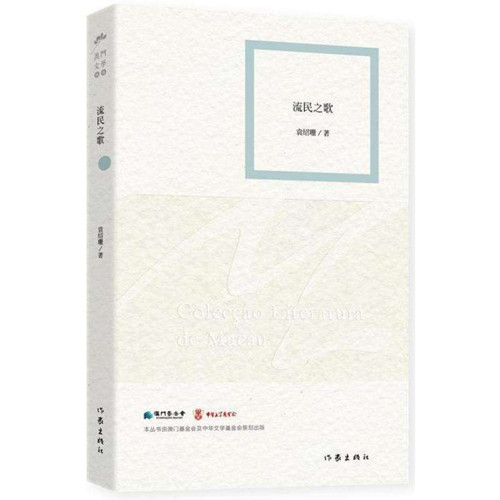
《流民之歌》
首先是名字。名字是外界了解一个人最初的标识,在袁绍珊的诗作中,人的名字常与地域身份及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如在诗作《流民之歌》(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中,人们叫“我”,有诸多方式:“小妞”、“外来妹”、“李家三顺嫂的灰姑娘”、“卡比莉亚”,每一个称呼背后都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我”到底是谁?这一场名实之辩恐怕难有定论。在《方舟纪事》(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中,作者写道:“神秘的船长,那自称诺厄(或张三或李四的船长)”,可见作者对于“命名”的用心。这篇诗歌的副标题叫做“记京广线上的三十三小时零四十八分”,中国的铁路线,诺亚方舟的神话,被放在同一文本之中,诺厄和张三李四被并置,产生了奇妙的化学效应。
其次是人体及与人体紧密相关的事物,比如“头发”。“染发”行为被赋予文化内涵,人们“抛弃花木兰而爱上洛丽塔”,在头发上无法固守“一个民族留给我的黄肤黑发”,东和西在头发上被混置,文化融合被具象化。头发被反复“拉直和染烫”,生命“易于折断,易于哀伤”(袁绍珊:《黑发时代》,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从头发的损伤折射生命的哀伤,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茫然之感瞬间显形。在《窝在那个窝里》(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5页)中,“留了一头乱发的城市被生活碎片/莫名其妙地击中脸”,城市被充分地拟人化,人和城在此融为一体。再比如指甲,一边向外,指向潮流与文化,在散文《指上风华》(袁绍珊:《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2页)中,讲到了美甲风潮和澳门多如繁星的美甲店,并提到美甲是一些行业里女职员的职场礼仪。这在诗作《指甲》(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60页)中亦有照应,“它们是低下阶级的——使我服务时/更吸引顾客//它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使我劳动时/更容易流血反甲。”美甲店遍城林立,审美趋向背后是复杂的文化变迁。此外,指甲作为身体的部分,也向内作用,是“关于无用、多余、有碍的注解”,手握拳时,指甲如蛰针,让人刺痛,却也驱使人与自己和解。内与外在隐喻的意义上相遇,人与外物的边界被打通。又比如“静看黑西裙渗入水泥、白灰”(袁绍珊:《狐狸》,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3页),衣物与空间互渗。而“感官像地平线一样舒展,远东和远西交叠”,“霓虹长出伤疤和疙瘩”(袁绍珊:《Wonderland》,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5页),“繁星般咳嗽”(袁绍珊:《沟通》,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页)等更让人与外部世界互为阐释。主体与客体的交合也会带来奇特的语言效果,如“窗外众生站如车站”(袁绍珊:《狐狸》,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3页),“你会再投掷自己如一粒骰”(袁绍珊:《愤怒不平诗,兼祭贝娜齐尔》,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站如车站,投如骰,名词为相应的动词作注,主体与客体在修辞里重叠,独特的音韵重复效果更让作品有了回环往复的艺术魅力。
在情绪与感觉的维度上,人与外部空间被更深入地融合。情绪可以被放置在城市而非人的身体里,比如“他把等值的爱养在城市之巅”(袁绍珊:《9月9日忆黑衣姐妹》,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76页)。外部的环境特征也成为情绪的一种,比如“潮湿”。在散文《潮湿的恒常状态》(袁绍珊:《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页)里,作者为自己的诗作《沼泽状态》作了注解,表明“诗的重点不是描写湿气,而是沉沦的状态。” 在诗集《流民之歌》中,有一个小辑就叫做《沼泽状态》,这一辑的诗作内向性更强,多呈现个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涌动,字里行间带有潮气。澳门是一座湿气终年不散的城市,家具会长霉菌,“湿气如此之重/那是一场多年的雨/在我们的心中一直下。”(袁绍珊:《沼泽状态——给Dear L》,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7页)潮气从外入内,雨下进心里,人和宇宙在诗歌中共振。
除此之外,作者还着眼于“食物”这一元素。“食物”作为一种“被制造”的物品,带有外部烙印;当食物进入身体,便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参与对人的塑造,也完成了外部与人的内在的沟通。一个地域的特色食物甚至成为人的名片,人如何介绍自己,无法规避自己的来处,那如何讲述自己的来处——“我率先拿出了杏仁饼/让它替我介绍自己。”(袁绍珊:《新生入学》,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6页)杏仁饼是澳门的特色食品,在作者的散文《手信二三事》(袁绍珊:《拱廊与灵光:澳门的120个美好角落》,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69-270页)中,也提到了杏仁饼,这种食物本地人不见得常吃,但作为带给外地朋友的礼品,却很有名。这种龃龉便让诗歌中的“杏仁饼”具有更深刻的内蕴。它代表了“我”,又和真正的我有一定距离,就像它代表澳门,却又无法完全贴近日常的纹理,由食物传达的讲述与倾听都有所隔膜,交流与认知的标签化带来的迷茫感呼之欲出。另一种惶惑体现在迁移中的身份认同,在诗作《Fortune Cookies》(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中,在提供水煮鱼、红烧狮子头、西湖牛肉羹的中餐厅,店主送了一份点心,却没有人能叫出它的中文名字。点心在母语中“无可命名”,一如吃着点心的人,根脉漂泊,身份驳杂,无可定论。但在《豆腐》(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2页)这一首诗作中,食物作为故土记忆的象征,成为一种遥相呼应的生命连接。全诗并没有直接描写豆腐,作者写的是在已逝母亲墓地前的光景,只在结尾时写下“让我于茫茫人海中/身携一尊豆腐如白观音。”豆腐藏在身体里,和神明等高,是流荡之中仍存的隐形根脉,把故土与异乡,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相勾连,导引人找到来处。作者也深谙食物对于记忆的特殊作用,在《不确定过他侧睡的模样》(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一诗中,曾狡黠地写道:“带他去我喜爱的食店/给他吃我喜爱的所有东西/单单是为着我离去以后,让他看见及怀念并思念终生。”食物便成为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通道。
袁绍珊诗作的多元互通性也体现在“通感”。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被一一打通,在与空间的互动中,感官不再是单一的线程,而是交织成一个网络。如“我抚摸着自己的喉头/颤抖着/再也无法读出远方的北斗。”(袁绍珊:《下一次众叛亲离之前》,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02页)北斗应该是“看到”,这里却用了“读出”。又如“有人伸出手,像一条蛇伸出舌头”(袁绍珊:《裸体野餐》,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页),手与舌,即触觉和味觉相遇,人打破感官界限,也打破与外物的界限。
另外在其诗作中,具象与抽象、实物与概念也常并置处理,互相阐释。如“民主的烟灰”(袁绍珊:《愤怒不平诗,兼祭贝娜齐尔》,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主义的泥泞”(袁绍珊:《沼泽状态——给Dear L》,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7页),共同构成更为复杂且寓意丰富的整体。
袁绍珊诗作中的时间也常是并置交杂的,时间并非呈线性,古典和现代也非继承关系,它们出现在同一个文本里,互相关照,各自纷呈。作者生活在文化多元的城市,又曾在国外求学,其诗文中,中国古典文化与西式现代表述常“撞色”。现代元素总勾连着古典韵味,而诗中的古典意象却终究是现代的,甚至西化的。在诗作《负面告解——在未来的新填海区写给三峡》(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0页)里,“我们渐退化成猿猴,在白帝城两旁奔走”,呼应了千年前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借古典意象完成对现下的反思。在诗作《雨后的樱桃》(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1页)中,开篇引用了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词句:“深巷卖樱桃,雨余红更娇”,而在古雅的基调下,讲述的却是雨中卖樱桃的女人面临城管突袭时的场景,时空两两对照,古雅情韵与现代语境下人的狼狈处境构成反讽。在诗作《娜拉的四重生命》(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8页)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歌谣体现了更明显的西化特征:“不要望天打卦,不等立春雨水/不怕惊蛰春分,不用纯如小雪,清明如无知/小满不是白露,不是玫瑰、香水、蜜饯/顺从不是原罪/它是系住炸弹的一条蕾丝。”一系列否定彰显了反叛,然而反叛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即出走后的回归。系住炸弹的蕾丝是十分现代且西式的意象,放在古老的节气之中,呈现出隔绝中的连接,构建出更为丰沛的诗意。
此外,袁绍珊的诗作中,有一个十分丰富鲜明的群体形象,即女性,诗集《流民之歌》中亦专门有一辑叫做《女书广场》。作者曾写:“所有男性和女性,原来都是只是女性。”(袁绍珊:《记雨中的国际酒店》,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3页)作者自身是女性,从女性视角出发,万物皆与女性相关。而女性形象的塑造在袁绍珊的诗歌中十分出彩,诗人采取偏小说或戏剧的方式来塑造女性人物,将女性放进情境和情节之中,有故事、有角色、有台词,十分生动。诗作《Wonderland》、《娜拉的四重生命》等是典型代表。在《娜拉的四重生命》(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8页)中,作者塑造了马姐娜拉、凤姐娜娜、女白领拉拉、朋克主唱NANA四类女性形象,探讨了“娜拉出走之后”的话题。她写各种各样的女性:卖樱桃的三个孩子的妈妈(袁绍珊:《雨后的樱桃》,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1页),“被绅士们的眼睛”给“拿下大衣”的“妹妹”(袁绍珊:《裸体野餐》,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页),不被理解又不肯妥协的“珍妮花”(袁绍珊:《珍妮花——给Prof.Janet Salaff》,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120页),说着“别人和世界无从把握,只能认清自己”的外婆(袁绍珊:《Wonderland》, 选自《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5页)……这些诗作传达了她对女性处境的彷徨、反思以及期望。在《自由神像》(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中,作者似乎透露了这份期望的具体样貌:“连无名英雄也不想做/只想长在高处,像木棉花般摇曳”,想要化成水滴,“滚来滚去/完成自由的目的”。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描写对象,更是自身的一种映照,写作者和被写作者达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一体性。而这女性形象,和作者诗作中的其他元素一样,都衔接时空,囊括万物。在她的诗作《羊》(袁绍珊:《流民之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里,“我”与“羊”对话,让“羊”把“我”放牧,主客关系颠倒,造成陌生感之余,更有一种缱绻的互为指引、互为譬喻的悲悯。最终,“就找一个土堆/予我俩以合葬”,在此,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象征与被象征,归而为一。这也正如同袁绍珊的诗文风格,彩色炫光汇成一束白色光芒,复杂而简约,锐利又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