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纳:诗意氤氲的《青色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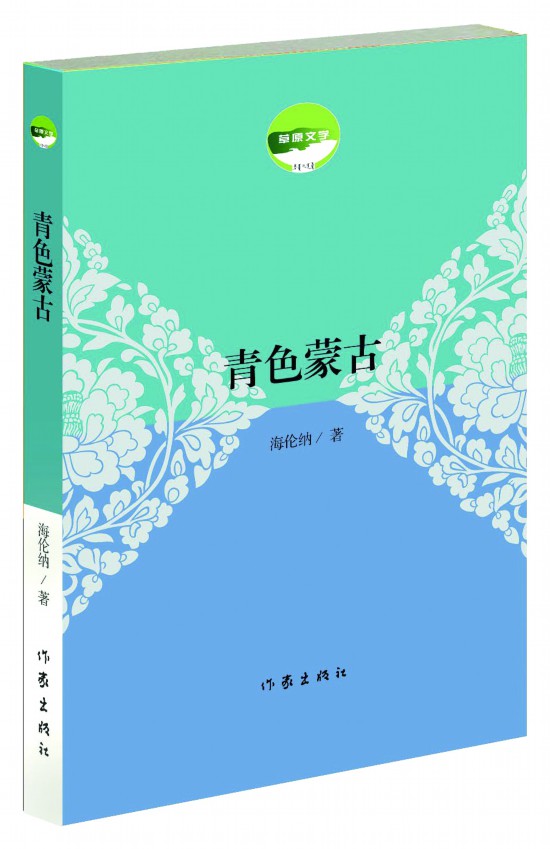
海伦纳的长篇小说《青色蒙古》用草原上“潮尔沁”的叙事思绪,为我们讲述了科尔沁草原上“潮尔沁”世家孟克巴图一家人的故事,草原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金戈铁马的时代背景、蒙古民族心灵世界图景徐徐呈现,在深沉浪漫的诗画描述中,展现了草原上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情感之美与残酷历史条件下的悲剧命运。作为“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过程”之一,《青色蒙古》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浓郁的草原叙事风格,史诗性故事建构的诗性美学意蕴深厚,是草原文学园地里一部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景外之致,晕染了《青色蒙古》的时序之变、时代更迭、人物情绪情感活动。静态景色描写,是《青色蒙古》环境氛围描写的重要方式,作者用诗歌化的优美语言描写草原,有夏季草原百花芬香、牛羊驼马悠然觅食、河流蜿蜒的美丽,有卷起黄沙、吹过广袤的旷野的春风,有静默雪原各种顽强生存的生灵,有秋季雄鹰搏击蓝天白云的金黄草原,还有日落月升、星月当空、清晨静谧、黄昏牧归、炊烟缭绕、琴声回旋等。作为小说的因素,这些自然景色描写是有叙事功能的,发挥着推进情节起承转合,铺叙事件发展、渲染人物心境的作用,通过景物之“静”,烘托时世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动荡,季节变化、景致变化都是人情绪情感活动的镜像,是人性的外化,使小说的叙述有了绘画的直觉和诗歌的韵致,化动为静,“一切景语皆情语”,铺设出一道人物命运的风景,是有深度的风景。这道风景与人物之间并非修辞意义上的比拟或象征,而是一种“异质同构”,即阿恩海姆文艺心理讲到的,事物外在形式与人的情感通过审美活动建立起来的内在对应。海伦纳在小说中的这一艺术表现方式,来自他早年草原生活的内心体验,深潜在草原人与大自然旷世生死相依的生命密码中。
虚实之韵,使小说《青色蒙古》宛若一曲悠长婉转的科尔沁叙事长歌,舒缓的叙事情境中回旋着忧伤的情致,对人物多舛命运的述说与浪漫情调的抒发共鸣,一部长篇的叙事结构就是一位“潮尔沁”老人用说唱方式在演绎自己族群的故事。
《青色蒙古》的情节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写实性的明线,即孟克巴图和他儿子纳钦两代人的故事,“人们传说,孟克巴图的祖先创造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把潮尔琴,随之也就诞生了他们这个潮尔沁世家”;另一条是若隐若现的辅线,即作为孟克巴图家族精神符码的民族史诗《呼和蒙古》,孟克巴图的父亲嘎拉僧“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智者,敬重地称这位潮尔大师为‘达尔罕·潮尔沁’”,在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现过程中《呼和蒙古》不是事件的焦点,对人物行为和处境似乎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青色蒙古》与诸多草原小说一样,对于马的形象描写、人与马须臾不可分离关系的表现占了很大比重,这应该是草原文学的文化“图腾”。对于马形象的处理,海伦纳也设计了两种情境中的白马,一种是现实生活中孟克巴图家的白马群和纳钦心仪的小白马,是具象的马,与主人生死相依,纳钦生命危机时小白马救出了他,实写的小白马是纳钦生活的忠实伴侣和生命的守护者,它与纳钦的关系是草原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活方式;另一种白马是传说的“神驹”,《呼和蒙古》中圣主的白骏马,是意象的马,它以神魔之力吸引着孟克巴图,让孟克巴图魂牵梦绕,生活在白马的幻象世界里,每在事件的关键时刻或人的命运发生转折之时,这匹神马如烟如雾飘然出现,带给人希望和力量。这匹虚拟状态的白马与孟克巴图之间形成了神秘的隐喻关系,孟克巴图“蒸发”般失踪很耐人寻味。
实写的故事事件和事物形象,是作者描摹的草原生活图景,虚设的隐线和意象,则是草原人的精神图像,象外之象的意蕴空间更丰厚广阔,需要用读者的想象和理解去充盈。如果用文学原型理论解读认识《青色蒙古》虚拟化叙事背后的内容,也许能走进一步。加拿大著名原型批评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指出: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荣格认为,原型意象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普遍存在的各种确立性的形式,文学艺术之所以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原型的影响激动着我们(无论它采用直接经验的形式,还是通过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现),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这种原型意象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草原文学中,以表现英雄主义﹑自然崇拜、骏马精神、母亲情怀等母题时,衍生了许许多多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神化的意象。我想,《青色蒙古》细腻逼真的情境背后的意味更耐人寻味,海伦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潮尔沁”代言人,深情地回溯自己民族先人,他以寻觅者的姿态讲述,并以讴歌者浪漫的低吟把读者带进一个诗意迷蒙的王国,一种难以用感官捕捉、用语言表述的精神气息萦绕在字里行间。
哲思之境,将《青色蒙古》叙事的景外之致、虚实之韵推向了较高的美学层面。小说通过普通草原人的悲苦遭际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内涵,在个体爱情悲剧与民族命运兴衰之间建立起深层关系,从而建构出意味深长、哲思深沉的意境空间。《青色蒙古》不以故事情节的奇特和人物性格的独特而取胜,引发读者阅读期待的是故事深处隐约闪现的思想火花,是融解在情感话语中的哲理思辨。海伦纳说:蒙古族是英雄的民族,也是忧伤的民族,民族精神的底色在老百姓身上。选择普通人,通过底层人物形象表现民族的苦难命运,是海伦纳创作的初衷,他认为这样的文学形象更贴近民族性格本质特征。《青色蒙古》所构筑的意境空间是他反思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表达。蒙古族在铁血战争的磨砺中成熟壮大,英雄主义是蒙古族的精神品格,但不意味着蒙古族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英雄主义,更不意味着穷兵黩武。热爱和平、敬畏生命、慈爱悲悯、包容豁达、隐忍顽强等都是蒙古族固有的心理素质,《青色蒙古》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这种民族品性的典型形象,特别是一组女性人物:曼德日娃、朵兰、索伦高娃、乌云珊丹、乌尤黛……都是美丽善良、宽容仁爱、勤劳坚韧优秀品质的化身,她们在不同的境遇中显现出蒙古族女性共同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个性特征比较突出,如孟克巴图执著、纳钦机敏、朝伦巴根忠厚、苏和乐观、小喇嘛扎木苏聪颖……但他们都有着包容豁达、坚韧不拔、关爱生命、守望幸福的品格和情操。小说中各种人物共同诠释了蒙古族的共性。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把他们一次次推入命运的深渊,结尾时纳钦经历九死一生就要看到希望的曙光时,又以不可挽救的悲剧告终。草原上的人们在一次次的天灾面前经过顽强的抗争,经受住了雪灾春旱的考验,但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却无法摆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运,善良悲悯抗拒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与和平、勇敢与仁爱、苦难与幸福,是人类历史的循环往复的悖论组合,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用各种方式探索着世界的奥秘。海伦纳的小说《青色蒙古》虽然没有直接切入这样的哲学之问,但留给了读者这方面的遐想空间。
仅就《青色蒙古》中的情爱描写而言,所体现的深意就很值得读者玩味和思考。作品中这方面的文字占有不小的篇幅,有夫妻之爱,也有情人之爱,都是十分纯洁真挚的情感。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唯美的描述,像一首首赞美诗讴歌来自生命本能的欢愉,赞颂艰苦生活中人最基本的幸福与快乐,表现与自然相契合的蓬勃生命力。与唯美浪漫相对应的残酷的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死亡和残缺成了这美好情境的结果。除了战争的苦难,还有宗教对人性的扭曲,仁钦喇嘛和乌云珊丹真情相爱,多少年“他们在快乐中送走了黑夜”,但仁钦必须屈服教义束缚,带给了乌云珊丹慰藉也不断地增加了她内心的苦痛。从小当了喇嘛的扎木苏,面对爱恋他的姑娘莎茹拉时,他丧失的不止是爱的权利,似乎也丧失了爱的能力。人美好的爱情被毁灭,纯情的爱欲被摧残,人性被扭曲,这是小说最忧伤的悲剧旨意,它潜藏在诗意化的叙事情境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