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泰松谈“从影”四十年:从《电影手册》到戛纳影评人周
在刚刚闭幕的First青年影展上,《春江水暖》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值得一提的是,评委中亦有可以称得上“发掘”了这部电影的人:夏尔·泰松。几个月前的戛纳电影节,他将这部电影选入了影评人周作为闭幕片,影片在戛纳亦颇受好评,这也是他就任影评人周艺术总监八年来所选择的第一部华语长片。
2019年也是夏尔·泰松(Charles Tesson,一下简写为CT)“从影”的第四十个年头,在他动身前往西宁前,笔者再次采访了他。“谁是夏尔·泰松”是贯穿访谈的线索:曾经的《电影手册》影评人、主编,亚洲电影的研究者、大学电影教授,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艺术总监;访谈的方法则从“个人史—影迷史—电影史”角度逐步进阶,因为这种方式也许能够获得更多的真实性。他自然是一个四十年来电影史的见证者,个中的启示,也希望能够通过他个人的微观角度得以放大。

夏尔·泰松(Charles Tesson)
成为影评人:从德莱叶到《电影手册》
澎湃新闻:夏尔,我们试着来一起聊聊电影,角度我已经想好了,那就是以你的个人经历来串联起一部分电影史。整整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在《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上你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影评,以前你也曾告诉我,是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将你引入了《电影手册》。
CT:是的,那是1979年的夏季刊,第302号。那时我在巴黎三大念书,出于兴趣跟听了很多当时《电影手册》影评人在学校中所教授的课,有达内,帕斯卡尔·博尼策尔(Pascal Bonitzer)以及塞尔日·杜比亚纳(Serge Toubiana),其中听的最多的就是达内的课。那时我已经是杂志的忠实读者,习读他们的文章并且非常喜欢。也是这样我逐渐认识了达内。同年四月,我为《幕前》(L'Avant-scène)杂志整理出版了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吸血鬼》(Vampyr,1932)的分镜头剧本。我送给了他一本,达内告诉我说很喜欢我为不同版本《吸血鬼》所写的注释。
澎湃新闻:《幕前》可能是世界范围内仅有的现在仍定期出版电影剧本的杂志,但“技术性”和史料性要远大于评论性,或者说那并不是个影评人的工作。
CT:当然,那不是一个评论性的杂志。但达内看过之后告诉我,应该为《电影手册》写文章。有一天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张纸片—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话,上面只有一句话:“有两三部电影,手册的下一期很有可能都不会提到,你来看看怎么办”。这三部电影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两部:《帕特里克》(Patrick,1978)和市川昆的《雪之丞变化》。
澎湃新闻:达内的纸条是一个进入杂志的邀请,最终你写了关于后者的影评。
CT:是的,当天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一鼓作气写了一篇,达内立刻就接受了且没做修改地刊登了出来。因而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达内也没有作为影评人的我。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当你学习电影的时候,成为影评人并不是你的志向?
CT:但我也对此感兴趣,毕竟那是一种写作;《电影手册》当然也很有吸引力。之前的1972年至1976年当我还在南特念书的时候,后来创建了南特三大洲电影节(Nantes 3 Continents)的贾拉杜兄弟(Alain & Philippe Jalladeau)已经开始组织一些放映活动,他们与手册相近,经常邀请一些影评人来参加,也是那时候我开始读这份杂志。
澎湃新闻:你开始接触《电影手册》的时期,也恰好是达内“整编”这份杂志,出离极端政治性毛主义的时刻。
CT:是的,我读的第一本《电影手册》应该是第257期,里面有一篇《法国电影的某种趋势》(Une certaine tendance du cinéma français),是标明杂志重新“开放”的一个信号。
澎湃新闻:在达内主导下向电影开放,重回电影的信号。
CT: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因为那时他们恰是想招入年轻的影评人作为新鲜血液改变杂志的面貌和风格。主要的范围是大学中的学生,尤其是他们作为老师所教授的学生,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也是。
澎湃新闻:达内是一个怎样的大学电影老师?
CT:特别有趣,很自由,他几乎都是临场发挥,毫无正式感,大家都可以随时自由发言。他不放电影也不放片段,只是讲,讲好几个小时,我们也不用记笔记,只需要听。也会问我们最喜欢的导演或者电影。
澎湃新闻:我时常将你们这一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杂志的影评人与五十年代初新浪潮那些未来的导演相类比,但这里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之处,如果说当时的“新鲜血液”来源主要是以电影资料馆为中心的影迷文化,你们这一代则是来自于大学。一方面,电影进入了学校;另一方面,影迷文化经过新浪潮一代的跃升后开始回潮,这是我的总结。所以你当时是个“影迷”吗?
CT:从对电影情热的角度来说,是的。
澎湃新闻:但也不是“影迷文化”诞生时的那种偏向“原教旨主义”的影迷了?我指的是比如“电影资料馆的孩子”之类的?如果不说那个我不想说的词的话(笑)。
CT:别忘了,影迷文化还是有点精英意味的巴黎文化,对于不在巴黎的人来说,电影的渠道并没有那么多。当我从外省到巴黎的时候,因为对电影史的认知有太多的欠缺,也是在电影资料馆狠补了很长时间电影。也是在那里,我看了所有德莱叶的默片以及之前从来没看过的格里菲斯(D.W. Griffith)。
澎湃新闻:那个时代外省影迷的经典电影观看渠道往往是不定期的电影俱乐部,以及电视。
CT:电视上周五和周日晚间会放的经典老电影,的确很多的来源都是电视。到巴黎之后自然就是电影资料馆,但也必须提那些会组织电影回顾展的一些艺术院线。
澎湃新闻:第一篇影评就被接受继而加入杂志成为一员还是蛮幸运的,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就很想问你是如何逐渐学习着开始写作成为影评人,或者说找到自己的风格。
CT:首先就是达内作为良师益友给予我指点,尤其是文章有问题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不要泄气并帮我做出修改。也记得有时他也会故意发出“挑战”,比如让我写《婚姻生活》(Scener ur ett äktenskap,1973),但电影是如此地厚重导致我书写不能。还有另一点,其实也是拜此所赐我和阿萨亚斯才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那就是达内经常会提醒我们,手册刚刚经过了一个远离电影又极其政治的十年,错过了很多优秀的电影和作者,比如从未和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做过访谈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损失,我们没有权利任由这样的疏远发生,应当从记者这个角度入手重回电影;以及,他会问我们:“你们这一代新的年轻人,哪些电影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需要你们找出来并告诉我,这也许是杂志的新方向”。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不要重复生产和写作那些我们(这一代)喜欢的或已写的”。不要模仿博尼策尔、乌达尔(Jean-Pierre Oudart)或者任何人,带给我新的东西”。这是他对新一代的期许,对于我们来说则是有趣的挑战,因为我那时确实很喜欢乌达尔、纳尔波尼(Jean Narboni)或者达内、博尼策尔的文章,如果他不如此提醒我们,确实会发生那种模仿复制的情况。因而我们刻意地向别处走去,从我们所喜爱和捍卫的电影上来说如是,从写作风格上来讲亦如是。也是依照这样的意愿,我们“找到”了乔·丹特(Joe Dante)、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或者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电影,这些在当时都是处在边缘的类型和风格,也不是他们那一代打心底里会主动愿意去看、去发掘的—甚至包括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电影。回头来看,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幸运的时期,杂志需要改变,我们也被信任,电影新空间得以被开辟。
新作者策略的养成:从美国制造到香港制造
澎湃新闻:这一点又是你们这一代与五十年代那一代相似的地方,为了创造或者再找回杂志的身份认同,从捍卫那些边缘的电影开始,那些之前不被正视甚至遭受歧视或者说不被认为是严肃庄重艺术的电影开始—从“正名”开始。
CT:完全如此,这是一条仔细思考下最正常的道路,目的是为了找到新的“作者”。
澎湃新闻:会不会也有一部分的影评人的姿态(posture)在其中,姿态性的选择,甚至是为了挑衅和煽动...
CT:这因人而异,与性格和经历都有关系。于我来说,关注这些当时所谓“边缘”的电影主要来自于兴趣,比如念大学期间我就在南特看过贾拉杜兄弟组织的巴西以及其它相对不是主流国家的电影展;当我进入手册之后,也报道过马克·穆勒(Marco Müller)在都灵和佩萨罗组织的大陆电影或者香港电影回顾展,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并让我逐渐从心中确定需要亲自去这些地方,因为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澎湃新闻:阿萨亚斯曾经告诉过我,他们那一代几乎所有人进入《电影手册》当影评人的目的都是成为导演。这也是和五十年代相似的地方,但我感觉你并不是。
CT:他说的是对的,大部分人的确都如是,但我倒从未有过成为导演的野心和欲望(笑)。卡拉克斯(Leos Carax)和我是同校学生并差不多时间一同进入手册,都是年轻自由撰稿人的我们互相聊过很多,除了电影之外,“你写的那个文章/短评被接受了没?”是我们之前最常互相问的问题(笑)。但他只待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后来他自己意识到,我们其他人也继而知道了,他进入《电影手册》的唯一原因和动力就是...认识戈达尔(Jean-Luc Godard)!而一旦成功地作为影评人探班了《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 (la vie),1980)的拍摄现场,梦想既已实现,他也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澎湃新闻:如果《电影手册》是跳板的话,卡拉克斯可能是过渡最快的,他似乎一共就待了五六个月。
CT:你知道吗,达内后来对他还有些怨言,并不是作为导演或者电影作品;而是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影评人”希望他为杂志写作,但这个人却很快地跨过了或者利用了这个“桥”或者踏板。对于达内来说,他希望找到的是“可信任”的年轻人并培养他们成为影评人。
澎湃新闻:但无论如何,达内还是很支持卡拉克斯后来的电影,不是吗?
CT:是的,这也是之前很多人认知有模糊的地方,在评论界达内非常支持作为导演的卡拉克斯。他不满意的就是之前我说的,有种被“利用”的感觉,不像同样抱着成为导演想法的阿萨亚斯,兢兢业业地将自己投入到评论工作中,为杂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澎湃新闻:确实在那一代年轻的影评人中,你和阿萨亚斯是投入最多也写的最多的。但那时在《手册》内部你们也是作为“边缘”存在的年轻人—没有报酬只有稿酬的“计件工”,那么具体是如何分配工作的呢,我指的是电影评论的分配,比如你那时就很少写法国电影。
CT:是的,很少很少,几乎不写。内部是有分配的,可以说是按资排辈。比如说贝尔加拉(Alain Bergala)主要负责法国电影,或者说将加莱尔(Philippe Garrel)作品“带到”《电影手册》的阿岚·菲利蓬(Alain Philippon)。所有别人分配完毕之后剩下的电影,则是我们需要在其中找到那些能够引导电影潮流的作品。因此你看,所有这些也都是“因缘际会”的产物。很多的美国独立电影或者较低成本的电影,阿萨亚斯主要在其中寻找,我也有参与。
澎湃新闻:感觉他更倾心于卡朋特,而你主要是乔·丹特以及柯南伯格。然后你们“共享”的则是亚洲。
CT:很少有人说的是,那时我们转向亚洲也是某种程度上从内部加入试图改变《电影手册》的非欧洲电影策略。在之前,编辑们对这些电影感兴趣的要么从纯粹的美学上,比如沟口健二;或者就是纯粹的政治上,比如巴勒斯坦或者北非的电影。转捩点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夏因(Youssef Chahine)的电影:他所拍的不是政治电影而恰相反,属于大众流行电影的范畴。当达内开始捍卫夏因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借此捍卫其它的所谓流行电影,香港的功夫电影——武侠片,等等;或者印度电影。
澎湃新闻:想到你刚刚所说的,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当然是(你们的)口味引导着你们的“写作”,但其实你们(需要)写的,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你们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影评人工作中不太为他人所知的一个细节,当然这完全又不局限于影评人...
CT:后面一种情况(我们需要写的)也在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口味,无形中的奠基工作。具体到自己性格的话,我自小就被那种来自远方的文化所吸引,电影对于我来说就是这种来自他处的他者艺术:与我一样的人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却又共处的世界,这就是对自己世界的拓展,地理性的和心理上的,这种延展性是我喜欢的,也是我觉得电影与文学、艺术和音乐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我很早就意识到了。电影是第一个让我个人世界变大的艺术表达方式。我长在旺代(Vendée),几乎从不旅行也没去过外国,人生中第一次出国还是因为《电影手册》的工作,甚至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笑)。瞧,所有不同的延展到现在都是因为电影。1981年,进入《手册》两年后,我被擢升为编辑部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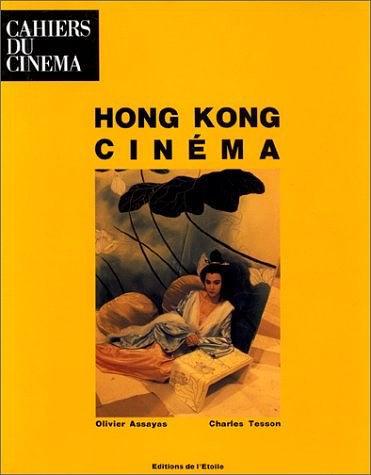
《电影手册》1984年特刊《香港制造》
澎湃新闻: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杨德昌的那句话“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以前延长了至少三倍”。好了,让我们讲一讲亚洲和华语电影,1984年特刊《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是应《美国制造》(Made in USA)的巨大成功顺势而生。
CT:但在当时《香港制造》却是一个失败,无论是销售还是评论,我还记得《世界报》(Le Monde)上那尖酸刻薄的文章(笑)。虽然现在这一期成了经典,当人们讲到手册或者亚洲,想到或者提到的都常常是这一期。事情还是要追溯到马可·穆勒在佩萨罗组织的回顾展,托尼·雷恩(Tony Rayns)在那里注意到了我这个来自《手册》的年轻影评人对亚洲电影感兴趣,就请香港电影节于1984年对我发出了邀请。编辑部讨论的时候,就有了做这期特刊的计划,阿萨亚斯和我一起去,我们会在那里待四月一整个月。我们写了很多东西,特刊上并没有完整发表出来。
澎湃新闻:这一次,又是对的时机和对的人。
CT:是的,就香港电影而言也是新旧体制、系统变化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两个对岸,尤其是台湾那边的新浪潮。香港就成了整个三地的交汇路口。
澎湃新闻:有一件轶事我经常将其想做一个关于你们两人之后经历的“隐喻”,那就是在香港期间,阿萨亚斯去了台湾亲自结识了新浪潮的诸位导演;而你则去了大陆的广东。
CT:是的,他去了三四天台湾;而我则去广东以了解更多的左派电影,和夏梦的访谈等等。因为我们带着发掘新浪潮的想法去了香港,到了之后那边的人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新浪潮正发生于台湾,需要去那儿。但《香港制造》之后我就没有很经常地去中国了,直到1999年《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特刊。那时候我已经是杂志的主编了,有一个做亚洲国别电影特集的想法,虽然最终并没有实现,最终只推出了关于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的特刊。
何谓影评人:回顾与反思
澎湃新闻:作为《手册》影评人的二十四年间,从外援记者到进入编辑部再到成为主编,你大概写下了约八百篇文章或者影评,但感觉你从来不是那种尖酸刻薄或者说以攻击性著称的影评人,在法国或者巴黎评论的语境下,那样的方式是最容易出名或者立名的,大家都知道。
CT:我从来都不是,而且那也不是我看待电影的方式,虽然有时候被分配到写一个讨厌的电影,但说实话这样的写作并不是我喜欢的事。逻辑大家其实都知道,写那样的文章会有更多人阅读,得到的反馈也更多,写作者往往会变得飘飘然继而更乐于此道,并会创造出一种偏向于“恶毒”的口味,说到底满足的还是自己,或者说被讨论的对象不再是电影而是写的人。我也写过这样的短评,但更喜欢的还是解释自己为何喜欢,以及一部电影是如何将我打动。作为影评人,我选择站在发掘、喜欢、分享的那一边;做一个发现者、开垦者。
澎湃新闻:我自己的思考是,确实也有两种类型的影评人,一种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发掘型的,而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演绎型,两个角度都能出现非常优秀的影评人,但同时能够结合两者的,其实少之又少。
CT:对于后一种,它总是让我想到自行车赛中的扫帚车,或者另一个意象:一个在网球场上盯着球跑来跑去的人,一个达内式的意象(笑)....
澎湃新闻:一种被动的接球者...
CT:我自己更倾向于做那种可以让影史而不是评论史得以丰富的影评人。
澎湃新闻:当时在手册,也是你们几个是最积极的旅行者。
CT:阿萨亚斯和我,是的。年长的那一辈有的人不愿意走动,也有的人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不便经常旅行。的确,坐在电影厅中看电影之后评论是一回事;到达“前线”,与创作电影的人结识、见面、聊天,了解一部电影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对前者的极大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
澎湃新闻:你作为《电影手册》前主编在杂志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告读者书》中有一些地方很打动我,你说到影评人要有一个写作的元动力,那就是自己的文章要像是写信一样有一个收件人的存在,或者说他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写作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个另一端“他者”,不管是谁:电影的导演、其中的演员、不知名的读者甚至是自己爱的人;也不管文章所要传达的是什么:说服别人、分享某种情绪或者感受…
CT:是的,我认为这种意识是极端重要的,不管这个“他者”是谁或是怎样的人或是再私密的人。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人写的影评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练习也很优秀,但却是极其自我封闭的。电影的本质就是分享和对话,这种写法是与电影之本是相悖的;同理,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第一次从电影中获得的强烈感受一定都不是美学上的,这个事实里面也有着很多的电影真实性。我们不该忘记电影的本源。同理,我也不喜欢那种自我封闭、一切都指向创作者自己的电影。
澎湃新闻:除了我可能还不知道的成文前因后果,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从影二十四年影评人内心信条的自白。自1998年至2003年,也是你作为主编的最后五年。
CT:《电影手册》自1998年被《世界报》购入后,就经常与东家发生策略上的冲突,主要是选择捍卫的电影上;而同时《世界报》也不太满意当时电影版面的主编付东(Jean-Michel Frodon),觉得他的口味对于这家大报来说有些过于先锋和偏激。大家都知道他很向往手册,于是这就成了一桩很好的“买卖”。我于是离开了《电影手册》。
澎湃新闻:经过此番“政变”,付东成了第一个并非来自于手册影评人的主编。而《世界报》于2009年转手至费顿出版社(Phaidon)后,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在这份杂志的历史上,电影策略多次变动,而每次的变动都是一次“政变”的结果,所谓多变。
CT:付东也是第一个由杂志的投资大股东而非写作团队决定出来的主编,这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自此之后,好坏自由历史来评断,但无论如何《电影手册》进入了一个相对僵化的时期。付东作为一个并非来自手册传统、之前从未在杂志上刊登过任何文章的主编,反而比之前所有的主编都更“手册化”—我指的当然是僵硬、“刻板”的那一面。而《电影手册》的传统就是在于不断变动,跟随潮流甚至赶在潮流之前,发现新作者和新电影,改变电影批评的风向和潮流,在内部总是有不断的小型革新甚至革命,导致杂志一直在变,但也是这么变化造就了杂志的身份和认同。相比较来说,《正片》倒是个坚持自己电影策略一直不怎么变的杂志。
澎湃新闻:确实,认清这一点只需要稍稍了解一下杂志的历史,从历数《电影手册》内部的一场场策略性“政变”开始...巴赞(André Bazin)有限度地接受新浪潮影评人进入杂志并在随后改变了杂志的策略...
CT:这种不间断的革新甚至在这之前,创刊不久就开始了:巴赞(André Bazin)与卡斯特(Pierre Kast)之间;“作者策略”(La politique des auteurs)与巴赞;里维特(Jacques Rivette)“赶走”侯麦(Éric Rohmer)引入他所认为的“现代性”(modernité),极左转向政治以及之后达内“政变”重回电影,杂志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裂变的过程总和。断裂并重生,恰恰这也是这份杂志的伟大之处。这也解释了历代更迭时候(人性之间)的背叛、出走...
澎湃新闻:但无论如何,套用达内的话说,这样的练习总是让人受益的(l'exercice a été profitable)?
CT:是的,而且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未想过在其它杂志或者报纸做专职的影评人,对于我来说,在《手册》写东西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家园,也许有些幼稚,但当我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继续在大学里教授电影。
澎湃新闻:在我们转向下一个话题之前想问你,二十几年手册影评人中最难忘的时刻是哪些?
CT:在香港的那些日子,写作有关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和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 (Manoel de Oliveira)电影的时候;以及很多做访谈的时刻—我很喜欢做访谈的,那是与人的相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
影评的延展:从《电影手册》到影评人周
澎湃新闻:2010年你成为了戛纳电影节平行单元影评人周(Semaine de la critique)的选片人并在两年之后成为了艺术总监。
CT:在之前导演双周(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也曾经找过我,但因为个人原因我拒绝了。接受影评人周的时候不无忐忑,因为没有预想到会是如此美妙的经验而且会持续这么久。我很热爱这份工作,即使它让我有些远离了写作。
澎湃新闻:除了形式上之外,影评人和选片人之间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按照你之前说的逻辑,发掘—捍卫—分享的这个过程是不变的;我觉得选片和评论在书写电影史的角度上并无多大相异,只是步骤上的区别而已。
CT:是的,但也要掌握两者的区别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选片人,虽是同样的过程,也就是说依靠自己的眼光“笃定”一个导演。影评人主要是需要有好的品味,选片人则不仅如此,如何靠十几部电影“搭建”一届电影节,也需要其它的能力,有时候与品味甚至毫无关系的能力。
澎湃新闻:一届电影节的选片,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口味?
CT:恰恰需要避免的情况就是让一届电影节的选片成为彰显选片人个人口味的产物,而要使它成为一个对“电影是什么,电影会走向何方”的回答。确实选片人的工作会使得一个影评人变得务实甚至更实用主义。因为两者面对的现实或者说接受的挑战还是不同的,选片人所面对的更加现实也更有风险,即使背后的口味(不论好坏)都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那选片中最大的危险呢?
CT: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看到一部电影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但也许我的片单中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又或者说比如按照类型来填充选择,我不会对自己说,“需要一部动画片,需要一部类型片...等等”。我们需要的是直面每一部电影。
澎湃新闻:自2012年执掌影评人周已经八年,你怎么看待八年间自己工作的变化或者通过自己的工作所观察到电影的变化?
CT:需要通过最初几年的观察—观察自己所选的电影在戛纳是如何被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影评人、记者、电影人所接受的,继而懂得戛纳电影节的运作机制,一部电影是如何在戛纳存在的,毕竟这是个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电影节,与其它所有的电影节都不同。让一部电影在戛纳“存在”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面对着官方单元—主竞赛和一种关注,以及另一个平行单元导演双周。我认为选择一部电影对于选片人来说就像是与制片人和导演签署了一纸协议,内容就是让电影在戛纳得以存在。
澎湃新闻:电影在“存在”是一回事,而之后的历程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不同的电影在戛纳期间和上映时往往有着不同的境遇...
CT:的确,在戛纳巨大的光环下,有时候一部电影迅速就存在了并开始了自己非凡的旅程;也有的电影只是得以存在,历经慢慢的酝酿过程之后在上映时候才得以绽放。想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就需要提醒自己,宁愿选那些需要时间才可以绽放的电影也不要选那种只会在电影节期间大造噱头,“爆”了的电影,因为后者只是短暂的海市蜃楼而已。而且恰恰选一届电影节影片最妙的地方就在于让这些电影在不同的时候绽放,拥有不同的开花期。比如去年的《居伊》(Guy)和前年的《小农夫》(Petit Paysan)都是典型的慢热型电影。
澎湃新闻:有让众人一见倾心的电影以造就选片的高光时刻,也有让人放慢欣赏,逐渐酝酿的电影。
CT:是的,这就是一届电影节的构建以及这份工作与影评的最大区别。但这些都是需要做过几届电影节才能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了解到有些电影我们很喜欢,但它们太脆弱了,在戛纳展示甚至会对电影不利,也许最好是洛迦诺或者威尼斯。具体到选片的细节,我还希望七部竞赛电影各不相同,但互相之间也能有联系,这个联系,就是影评人周的印记和我们的电影信仰。
澎湃新闻:选择一个导演,在戛纳创造他们电影生涯的美好开端,是一件令人激动和幸福的事。但也是一个冒险,八年间,曾经你选过的导演有很多肯定都已经拍了第二部、第三部电影,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当初的笃定是对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出现,甚至是让人失望和泄气的。
CT:当然当然。选择了一部处女作在戛纳获得了成功,之后的作品却差强人意,这是会让我失望的。当然我可以自私地说,自己选择的是这个导演最好的作品,但我笃定的其实是他们的未来,我也衷心期望他们电影创作上的美好未来。有像那达夫·拉皮德(Nadav Lapid)那样的完美例子,也有《午餐盒》(Dabba,2013)导演那样让我有些失望的经验。
澎湃新闻:选片肯定也有地理上的考量,你曾和我说过,一届电影节的选择不应该是地理上国度的累加,虽然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但被认为是亚洲电影专家的你,直到今年才选择了一部华语片进入影评人周。
CT:是的,它不应该是地理上的叠加。我希望自己今年所选的这一部是正确的,是好的(笑)。这些年间我确实看了很多华语片处女作,但大多都是模仿贾樟柯电影的作品,对于我来说,不够强也不够独特。

《春江水暖》电影海报
澎湃新闻:我们就以这部华语片《春江水暖》为例来做分析,为什么选择一部纯中国制作的处女作作为今年影评人周的闭幕片且非竞赛,我认为这是个颇为奇观的选择,从选片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什么原因?
CT:首先是现实的因素,我们看到电影的时候已经是选片的最后阶段;还有电影时长的原因,七部竞赛片中已经有了一部相对较长的《阿布·莱拉》(Abou Leila),出于排片以及综合因素,我选择将它放在闭幕片的位置,也是一种保护,放映次数相对少,但来看的反而都是一些更适合的人,虽然不在影评人周竞赛却可以竞逐金摄影机奖(Caméra d'or)。如你所说,这确实是一次很罕见的选择。但我确实对这部电影一见倾心,并认为它会在戛纳造成一个轰动的“效应”。
澎湃新闻:我记得你有说过这部电影让你想到了杨德昌,但我在看的时候却觉得类比侯孝贤仿佛更合适,抛开这些不论,是不是选片人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尽量避免与电影史上作品做类比反而是更好的方式?当然我说的是理想中的状态。
CT:的确也有一些八十年代侯孝贤的印记。类比是出于工作的方便,主要方便于观看的人有一点参照物(笑)。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一个像是我们在贾樟柯电影中看到的中国,但是展示的方式却是传统中国画的,同时又避免了对于国画的草率模仿,而是从中提取精髓,甚至有一些道家的风范。
澎湃新闻:还剩最后一个我想简单与你聊聊的事,因为你同时也是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世界电影基金”(Aide aux cinémas du monde)的主席,这是一个专门金援法国联合制片的外国电影的项目。越来越多的华语年轻电影人和电影项目也开始了解这个“法国人的野心不在于做法国电影而是世界电影”的代表性基金。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CT:当然是把真诚地做自己的电影当做最重要的事,跳脱一些既定的主题和美学方式。自由地创作电影,不要想太多的外部因素。“世界电影基金”的成功申得会帮助电影多一点能见度,但非常有限,对于入选电影节的加权更有限,因为每年得到这个基金的项目并不少,最终的选片终究还是看电影的质量。多试着跳出一些既定的框架,或者说做一些我们没有设想到的中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