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乡关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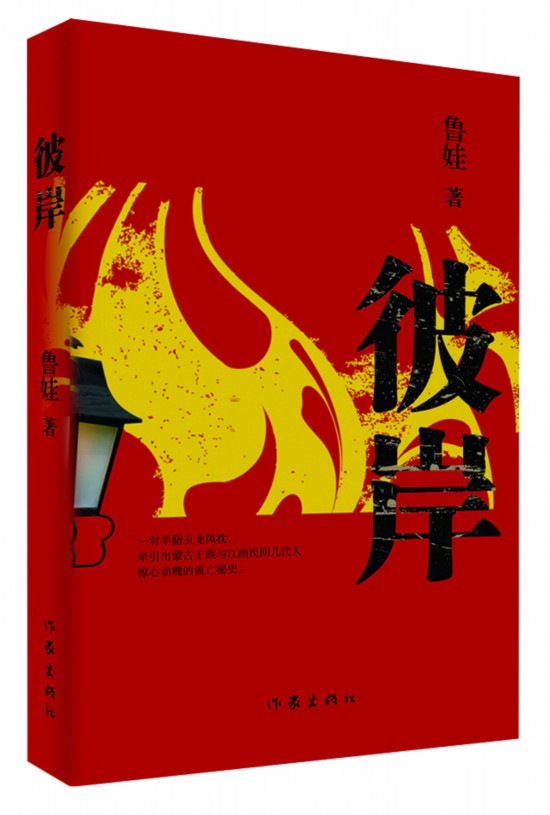
神秘的法国女人,稀世的古物珍玩……鲁娃的长篇新作《彼岸》,用冷峻中饱蘸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三个华人家族在一个动荡世纪中的生命挽歌。
从清廷盛世的鞑靼东归到华夏民族陷落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格局下连绵不休的人性浩劫……庞大的时空布局,复杂的“混血”身份,无论是从文本中直观领略历史的说不尽,还是从故事背后意会命运的道不明:海外华语文学,文化历史寻根,政治风云写实,女性写作……每一个视角,都可以在小说里找到多义多解的可能。
探痛于历史罅隙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人创造的工业技术以不可阻挡之势侵袭华夏古国沿袭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进化的历程必然裹挟着创痛的蜕变,并具体而深刻地施痛于历史车轮下每一粒渺小的微尘。
在硝烟弥漫的世界里,查理家族的显耀史诗戛然中断,昔日荣光渐次暗淡;吕伽父辈的南城食肆被迫远渡重洋,去异国开垦前途未卜的生机;林一舟的书香世家陨毁于和平国度的群体狂欢,终以家破人亡给出魔幻时代的悲剧注解。
书写近代中国历史褶皱中的烟波风云,书写异地漂泊的华人族群的流亡史,构成了《彼岸》基本的叙事主题。
《彼岸》的书写对象——王室贵胄、知识分子、尘土百姓,分别代表中国社会里三个不同阶层,但对于这些在时间长河里真实存在过的众生赤子,历史洪流哪怕轻易拍出一朵浪花,便足以让他们在盛衰消长中体验剧痛。于是,在历史遗留的罅隙里拾捡残片断瓦,寻找流逝的记忆,不仅需要有直视真相的勇气,更需要有对镜自照的理性。
《彼岸》的独特,在于以法国女人夏洛蒂的视角,在难以跨越的地理文化疏离中,在脱离国人自道的语境中展开具有特异性质的西式解读,以期让历史观察的视域得到全景式的拓宽。或许如此包容了别样角度的诠释,有利于让我们在历史真实与虚构旷日持久的悖论中获取纾解和新知。
浪迹于命运巨流
如果说以西化的史观展开对近代中国历史场景的思考,是《彼岸》的一大创作意义,那么将目光锁定于一群终生漂泊的客体,观察巨流里的“不系之舟”如何在命运的旋涡里载浮载沉,则可视为作者的笔触向人性方向的纵深探索。
《彼岸》中由夏洛蒂做线头,牵连起查理、吕伽以及林一舟三人各自独立又互相勾缠的故事,意在三段浪迹天涯的殊途中“寻找家园”,追求一个属地的同归。
查理的家园地标明确,蒙古草原、北平古城,都曾是土尔扈特王族画下戎马壮史的高地。然而家国离乱,关山难越,当整个时代都沉浸在掠夺和杀戮的疯狂中,当血肉横飞的猩红成为一个少年成长的底色,将注定终生都抹不去记忆的惶恐不安,让心灵压铸沉重的负载。
而吕伽穷其毕生寻找的家园,不是地理意义的某个坐标点,而是在身世迷雾的包围中,寻找对自我身份的确证和认同。随父辈越洋而来的南方风物即便能在异域勉强落地生根,吕伽的人生却始终架在来路不明的巨大诘问之下,关于血缘,关于文明,关于价值……当尘封的往事随着“四根金条的交易”暴露在惨烈日光下,“客从何处来”的永恒追问,却吊诡地促使了吕伽精神世界的崩塌。
至于林一舟,家园于他而言则是承痛记忆的象征。父亲坚守的圣贤之道,尚能在战乱和饥馑中助他躲进小楼,独守一份乐道安贫的君子之风。而在政治风暴中被冠上欲加之罪,受尽肉体与灵魂的双重侮辱后惨然失踪,却是荒谬时代里属于儒生的群体性宿命。林一舟千里寻父,却眼见父亲在自己的家国死无葬身之地,回望再三决然远去。
查理的戚然凝视,吕伽的焦灼四顾,林一舟的果断背离……是失落灵魂追寻家园之未果,也是不系之舟遥望彼岸而无终。前路在何方?天地玄黄,没有应答,唯有行路人漂泊于洪荒。
退归于此岸的救赎
上帝未曾兑现过应许之地的承诺,而停泊彼岸的精神家园也苦觅无踪,如何在无意义的生存迷思中点亮前路的灯炬?鲁娃在《彼岸》里,开出一剂“人道主义关怀”的救赎药方。
查理的生命里背负着过去时和现在时的双重重负,灵魂的举步维艰是终其一生的笞刑;吕伽的身世骗局又如同深不可测的旋涡,不容抗拒地拽他沉入绝望的涡底;林一舟则为一时摇摆的欲望,背起了不惜代价捧璧归赵的使命……当法国女人夏洛蒂缓缓走来,她既是三个华裔家族前尘旧事的旁观者,也是这个族群后裔们今生个人史的参与者。在共时的岁月里,她追逐查理的脚步,从仰望到平视,再到目送他离开世界,结束痛苦一生的自我缠斗,并完成女性自我的蜕变成熟;与吕伽同行,她用坚毅而不失柔情的女性关怀拯救遇溺挣扎的苦儿,也一同接受命运早就布下的惨淡结局;而与林一舟的邂逅,当“虎皮子”与“秋梨子”跨越山河阻隔奇迹般的重逢,华裔流亡者们整个世纪的颠沛失所,也终于在夏洛蒂的见证下,结束对彼岸的无望漂泊,得到了退归此岸的柔性安慰。
从《彼岸》里观察鲁娃笔下的救赎,设置女性角色给予情感上的慰藉并不是传递人道主义精神的唯一方式。比如晚年疾病缠身的查理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解脱肉身折磨,抵达无痛的极地乐土;患上躁狂型抑郁症的吕伽反在教堂每日肃穆的钟声中,以一种类同于宗教关怀的形式,获得了灵魂的洗礼超脱;林一舟则是在“物归原主”的持久奔忙中,达成了自我内心交困后的和解,也完成了更宏大意义上的民族历史文化经历痛苦考验后的世纪性救赎……
可以说在思考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和终极意义上,鲁娃的《彼岸》做出了大胆超前的尝试,虽然求解的答案未可见之,也许这一探索也是没有终点的漂泊,但张开前行的风帆,本身就意味着与虚无的勇敢对抗。
关于历史真相,关于社会规律,关于文化碰撞,关于命运意义,关于人性价值……时代的风雨需要诚实的记录,而鲁娃的《彼岸》无疑用风骨作笔,以柔情为墨,叩响了宇宙深处细节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