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给增殖的现实放置意义 ——关于写作的一些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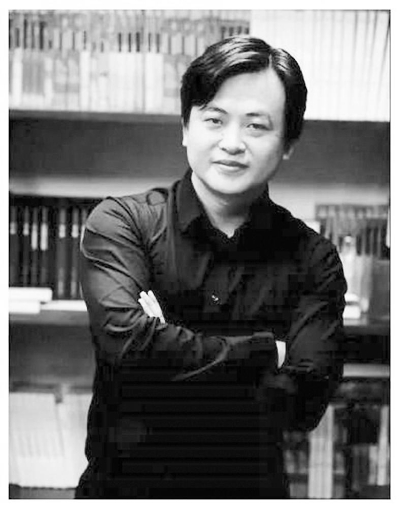
王威廉
一个作家应该凭依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
技术化时代的“准未来”
在我看来,今天写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现实。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家不需要刻意去理解现实,因为彼时人类还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改造现实,但如今,人类已经获得了更强的改造现实的能力。除了声响、影像、信息传输等二十世纪的技术变得更加完善和便捷之外,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以为现实的疆域正在抵达边界之际,VR、AR技术又诞生了,影像摆脱了平面的囚禁,产生了对人类大脑而言“真实”到足以无法分辨的人造现实。
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也惊人,机器可以精准识别事物,包括人类的脸部以及其他物理特征,但我们并不知道机器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只知道对机器这样“训练”便可以做到。这已经有点儿接近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不知道。但有一点无可置疑: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影响一切,而是技术成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从传统的人文学范畴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令人惊悚的事情,因为人类灵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人文学的前提与假定。技术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灵魂的领域?想想电影《黑客帝国》里边的悲壮场面:人类被一种虚拟的假象所笼罩而又全然无知,人类的真实不仅被重新诠释,而且变得不可接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距离这部电影首次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所谓的赛博空间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之中,是一种“准未来”的状态。
有人也许会说,哪个时代不是过去时代的未来呢?但很显然,情况要复杂得多。建构关于未来的想象受制于当时的文化意识,唐代人可以想象明代人的生活,而明代人却无法想象今天的生活。这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关于未来想象的文化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人类发明了未来,这种未来又变成了类似毛驴头顶悬挂的蔬菜那样的东西,不断诱惑着我们。
科技现实主义与深度现实主义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做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1984》《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已经不仅仅包含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以科幻为视野的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那么进而推论,充满想象力热情的科幻小说与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其实有了越来越多弥合的可能性。
因此,所谓的科幻小说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科技现实主义”的作品。科幻这个词语中的“幻”字,会逐渐失去其梦幻般的色彩。我甚至不免想说,其实传统类型意义上——比如以凡尔纳等作家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已经终结了。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会跟其他文学类型一样一起走向融合与创新。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的写作能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难以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
我曾经提过“深度现实主义”,想说明今天现实的复杂性。在文学的语境中使用“主义”是一种表示强调的修辞,尤其在我自己的行文中更是如此,正好特此说明。“科技现实”只是“深度现实”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已。之所以重提“深度”,是我坚信现实主义一定是关乎人的存在的,与文学的创造息息相关。一个作家应该凭依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记忆、建构与心灵,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
鲁迅先生曾说文学的起源,是因为先民们“天地变于外,则任情而歌呼;心志郁于内,则只畏以祝颂”,其实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听到这么密集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几乎都是单向度的,它们指涉到我们的身体与精神上,却并不在意我们的表情与反馈,就像我们天天用微信朋友圈看着别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人的存在感依赖于精神之间对话、交流的呵护,当心灵的内部被外部泛滥肤浅的言辞占据之后,生命的危机便出现了。那么,只有文学,它提供的话语既可以是柔软的抚慰,又可以是深思的哲理,既可以是决绝的宣告,又可以是犹疑的对话,而在它的这一切品质当中,关键是它一如既往地承认这个世界与人生当中那些晦暗不明的部分。那是被分门别类的现代学科剔除掉的部分,那宛若游魂的部分却牢牢关切着我们生与死的全部细节,这就是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
文学的本质之一,便是它对于世界本身的持续命名。人类其他的知识类型总是希望和世界之间有着稳固的假设、概念与解释,但文学是对处境的鲜活映照,是属于心灵的特殊知识。它追求的是鲜活与流动,所有概念化的僵死之物都是它的敌人。因此,好的文学既可以囊括技术带来的求新求变的那一面,也可以将这些新与变引领向那些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事物。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正是在文学精神的烛照之下,让我们即使与他人耳闻目睹了同样的事物,我们的心灵体验也不会相同。这种不同正是个体得以保全自我的唯一途径。好的作家就是在竭尽一生去寻找这种不同,并让别人相信总有“不同”的存在,救赎的可能性就在那样的“不同”当中。是的,这种“不同”就是心灵的自由,就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由。
文明叙事与声音诗学
在这样的语境下坚持写作,必须得更加地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这是一个将全部事物连根拔起的时代,它的根基不在静止的大地上,而是在运动的加速度上。“现代”与“技术”已经成了同构的事物,它们密不可分,交融在一起。所以说,技术时代的风险其实就是现代性的风险。世界那不可见的晦暗在不断加深,每个个体面对的都只能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局部侧影。面对如此语境,文学的力量究竟何在?
我认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丰富的载体,没有失去它的关怀、责任与绵延不绝的力量。
为什么中西两大文明,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最终都选择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表述自身?当然,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这和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成熟是密切关联的。但这只是一个前提,背后的精神史值得我们探讨。
以中国为例,明清之际出现了“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历史心灵在小说中的诞生。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了中国人作为个体的觉醒,它是一部完全根植于个人经验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作品,其实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它们不只是施耐庵、吴承恩个人的创作,它们是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反复加工而成的。而《红楼梦》只可能是一个人的作品,也许后面四十回是他人增补。即便不论作者是集体还是个人,只看作品中的精神品质,我们在《红楼梦》中终于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形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不是乱世、江湖和神话。因此中西两大文明传统以小说为最终表达并不是偶合,这是成熟文明的一种内在冲动与需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认,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技术时代阐述自身的方式,与历史的其他阶段一样,都依赖叙事。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人类精神的顶峰处,对人类的前景抱有光明的希望。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悲伤彷徨的困境,那些伟大的作家写尽了对黑暗与绝望的体验。二十一世纪,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经历迷失,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
文学的叙事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它源于人与物的本质不同,它坚信灵魂的存在与崇高,是灵魂最为隐秘的细腻言说,是具备史学品格的雄辩自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还觉得文学只能描述(再现)现实了,尤其是只能描述某一种“给定的现实”。我相信文学的能量几乎是无限的,它当然可以创造现实,而这种“创造”涉及到的是我们对于何为真实、何为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这个让我们惶恐迷茫的技术化时代,究竟何为真实、何为本质,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说出它的判断与思想。
在这里专门提到声音的诗学,再宏大的文明也需要借个人之口说出,否则便是没有生命的僵死之物。作家的声音,便是生命融进语言的踪迹。语言创造了主体,主体借助语言又在创造着自我。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不可避免也改变了主体,主体与语言在彼此异化着对方。语言的艺术,便是主体对语言异化的搏斗。何为准确?便是要驯服语言,使语言准确对应于主体的存在状况。作家的声音越独特、越清晰、越迷人,便是语言被生命驯化得越到位。
越是经验同质化的时代,越是需要鲜明的音色。小说的表层似乎是在复制经验,但小说的本质其实是在创造经验。小说家与传统说书人是完全不同的,他无法取消自己,他自身最独特的声音,是支撑起作品的脊椎骨。最伟大的小说家,可以让所有人的声音都出现在自己的声音中,自己的声音并未消失,而是成为一个基本的场域,它迎接着他者声音的到来,并凸显出自我的声音与他者的声音,赋予他者的声音以活着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