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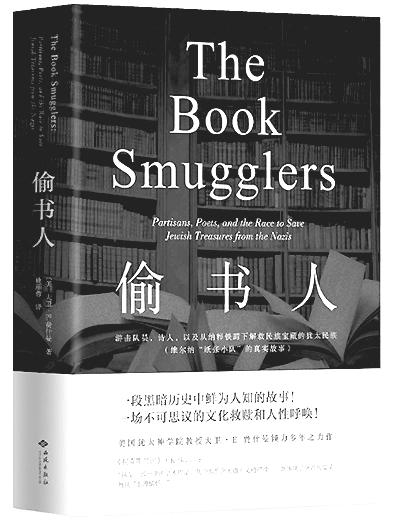
《偷书人》讲述了犹太平民如何从纳粹和苏联手中,通过藏匿、掩埋等方法而拯救出无数罕见的书籍和手稿,最终偷运出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它关于英雄主义和斗争,关于友情和浪漫,关于坚定和奉献,其中包含着这些平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文学和艺术的无畏。
作品由犹太人、德国人和苏联人的文件资料,包括当时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和作者对曾经参与过这起事件的数位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共同形成,重现了一群在维尔纳(“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诗人和学者走上游击队员和“走私者”道路的勇敢行为。在黑暗的年代,前途叵测的他们尽自己所有的力量保护着生命中的那点微光,也迸裂出最辉煌的人性光芒。
1
1942年6月,针对书籍和文件的销毁工作开始之后,赫尔曼·克鲁克开始争取“纸张小队”成员的帮助,把书偷出工作场所。
很多人立即表示支持,他们想:“反正我都活不长了,不如做些好事,救下这些资料。”
克鲁克对于大家的快速回应感到开心:“大家都在尽力救书。他们不顾性命救出每一张纸,他们是伟大的。每一片纸都可能使他们人头落地。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者们总能巧妙地把书偷走。”
挑出要最终偷走的书不是难事。整个大楼有一堆又一堆的书籍和文件,只要避开史波克特和ERR(注:特遣突击队,专门负责文化搜索和掠夺)队员的监视,把贵重的书籍、手稿藏到一堆书里,之后再捡起来转移就可以了。如果德国人不在房间里,甚至可以在地板上新弄一堆“待偷走”的书。
每一个奴隶劳工都在一时冲动下做出过决定,要带走什么书。虽然他们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但是有几条准则是明确的:
1.图书:分出要偷走的一本,其副本可以被送到德国或造纸厂。“纸张小队”负责处理几个图书馆的馆藏,因此一书多本很常见。
2.图书:相比于大的对开本《塔木德》或文集,小本的图书和册子更容易藏在衣服里偷走。大的物件需要分开放在YIVO(注:1925年在维尔纳成立的意第绪语研究中心)大楼内,直到可以安排车辆进入聚居区。
3.手稿:对施默克和肖兹克维拯救文学手稿和著名作家信件的工作,给予高度优先权。两人都是诗人,可以意识到保存文学财产的重要性。信件、诗歌和短篇小说都不是长篇作品,藏到衣服里相对容易。
4.档案资料:大问题。每个档案集太大,不适合贴身偷走,也不能在一个集子成千上万张纸中挑选出“宝石级”文件。“纸张小队”安排将大多数档案资料运到德国。几个散放的集子被分出来,等待交通工具运输。
5.艺术品(画作与雕塑):利用交通工具偷出。
小组成员相信存放书和文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聚居区内部,也就是在犹太同胞中间。但是德国人将“走私”物品进入聚居区看作重大犯罪行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从工作场所“走私”物品。约翰内斯·波尔与史波克特曾明确指出,这栋楼里的所有图书和文件都只有两个目的地:德国和造纸厂;其二,绝对禁止任何人从任何工作场所,将文件和书籍带入聚居区。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们会将文件包裹在身体外面,再在衣服里面塞上物件。漫长的冬季最适合偷书。小队的劳工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衣服也穿了好几层。他们还做了腰带和尿布,在里面装满了书和文件。但是在“装满”自己之前,他们需要先取回放在YIVO大楼附近小木屋里的大衣,小木屋里住着他们的克星——YIVO的前守门人。这个女人有时发现劳工们在大衣里装了文件,就向当班的威尔布里斯告发他们。幸运的是威尔布里斯从来不把她的话当真,因为这个前守门人是个内心充满愤恨的女人。众所周知她喜欢编排别人,他可不想将她的指控转达给ERR的官员。
小队离开YIVO前往聚居区时,每个人心里就会浮现以下问题:今天是谁在大门口检查?如果犹太聚居区警察和立陶宛人在大门口,一般就没有问题。他们的检查不严格,搜身特别松懈。警察知道小队成员带的只是纸张,不是食物——食物是更严重的罪行。有的警察甚至要求成员们下次下班回来给他们带本有趣的小说。
但如果是德国人在门口站岗,比如安全警察的头儿马丁·维斯、犹太人事务副区域长官弗朗兹·穆雷尔或者党卫军二级小队长布鲁诺·基特尔,就没有希望了。德国人会无情地殴打偷运各种东西的居民。穆雷尔常常出现,进行突袭检查。如果他发现回来的工人在衣服里藏了面包或者钱,就会把工人的衣服剥光鞭打,再把他们扔进监狱。如果罪犯被送到犹太聚居区监狱,他们可能还能活命;如果被送到路基施基监狱,那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波纳尔(注:维尔纳郊外的大规模屠杀地点)。
“今天谁在门口?”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2
从韦乌尔斯基街18号回去时,奴隶劳工会问其他刚刚离开聚居区、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大门口的情况。如果德国人在站岗,小队成员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绕着几个街区走几圈,等德国人离开,或者暂时把资料丢给住在距离YIVO不远的、“凯利斯”劳工街区的犹太人。但是也有几次小组成员距离大门太近,无法不被察觉就折返,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德国人的检查。
施默克的大胆行为总让人为他捏把汗。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带了一本巨大的、有破损的《塔木德》。到门口时,他向武装的德国守卫解释说:“我们的长官史波克特让我把这本书带回聚居区图书馆的装订工厂重新装订。”盖世太保认为这个矮个子的男人肯定不敢编造一个如此明显的、可能让他丢了性命的谎言,就让他通过了。
有的时候这些偷书人只是运气很好。一次,穆雷尔从瑞拉切拉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银色的红酒杯,每个人都以为她完蛋了,但是瑞拉切拉对穆雷尔说她想把这个银杯作为个人礼物送给他;她还在杯子里扔了一双贵重的皮手套送给他的妻子。不用说,犹太人事务副区域长官相信了这个故事,或者说他接受了这次贿赂,让她安全通过。他那天的心情应该不错。
作为一个偷书人,肖兹克维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他曾经从史波克特那里弄到一张手写的批准单,允许他带几捆废纸进入犹太人聚居区,当作炉子的燃料。他在门口将文件给守卫看。他带进去的“废纸”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姆·阿莱汉姆、拜力克的信件和手稿,夏加尔的画,还有维尔纳加恩的一份独特的手稿。还有一次,他成功地利用友人的关系,把马克·安托柯里斯基、伊利亚·金斯伯格的雕塑,以及伊里亚·列宾和艾萨克·列维坦的画,全藏在交通工具下偷走。
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圆满的结局。有几次,警察收到命令要“加紧”调查,施默克和一些队员就在大门口被殴打。殴打他们的有德国人,也有犹太聚居区警察。但是没有人被送到波纳尔。他们是幸运的。
瑞拉切拉·克林斯基记得,虽然偷书需要冒风险,但是“纸张小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了进来。许多“技术小队”的运输工人也制作箱子和纸盒将书籍打包运走。一个技工的工具箱里有暗层,他就将书、文件藏在锤子、扳手和钳子下面的暗层里。
泽里克·卡尔曼诺维奇改变了看法,也开始加入大家的行动。他知道即使有30%的定额图书会被运到德国,但是如果不偷,很多珍贵的物品都会被毁掉。他将小组的行动看成是一篇精神的乐章,是小组成员们的道德反抗,他像一位虔诚的拉比一样祝福偷书人们:“工人们尽力拯救所有东西,不愿它们遭受被遗忘的命运。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的行为受到祝福,愿他们被神明的力量保护。愿上帝……怜悯我们拯救的剩下的书,让我们可以在和平时代再见这些被埋藏的信件。”
3
施默克后来回忆:“犹太聚居区中的居民都把我们当作疯子。他们都在衣服和靴子里藏食物带进聚居区,我们却在偷书籍、纸张,偶尔还有手抄的《妥拉》或门柱圣卷。”“纸张小队”的有些成员确实遇到这样的困惑:到底是偷书,还是为了家人“走私”食物?还有居民批评“纸张小队”在这个生存都困难的时候,还忙着关心纸张的命运。但是卡尔曼诺维奇坚定地认为书是无法替代的,“树上可长不出书来”。
一旦资料通过了大门,它们就需要被藏到相对稳妥的地方。最简单的安排就是把它们交给克鲁克,他会把罕见的书籍放到藏书地,非罕见图书放到犹太聚居区图书馆。
克鲁克自己保留着一个文化宝藏的卡片目录,在上面记录物品的来源。在ERR工地上“偷”的东西,被列为“来自机构”。如果写“来自ERR”,那么如果有一天库存卡片落到德国人手中,可能会成为偷书的罪证。
但没有人可以保证聚居区图书馆,还有克鲁克的藏书地会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如果德国人突然搜查大楼并且收押所有库存该怎么办?将宝藏分放在多处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据肖兹克维回忆,一共有十个藏宝地点,他记得的地址有七处:德意志路29号(在他和施默克、丹尼尔·费恩施坦住的楼里),斯特拉舜街6号(聚居区图书馆),斯图拉舜街l号、8号和15号,杨斯卡街西南地区,以及沙沃尔街6号。
从德国人手中救下的两件最珍贵的东西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日记,还有维尔纳加恩的祈祷室的记录本。肖兹克维早就发现了它们,并将它们偷进聚居区,分别藏在两个地方。
除了把书藏起来,还有其他的办法。施默克和肖兹克维将很多书籍、资料交给在午饭时来拜访的波兰和立陶宛友人。威尔诺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欧娜·施迈特捡起了一捆I.L.佩雷茨的手稿,并安排同事将手稿藏在大学图书馆中。立陶宛诗人卡基斯·博如塔在立陶宛科学院的文学机构藏了好几包资料。肖兹克维把珍贵的资料交给与波兰地下党有联系的维多利亚·格米莱夫斯卡。当肖兹克维把18世纪波兰自由战士塔德乌斯·科希秋什科曾经签署的一份文件交给她时,她跪了下来,亲吻着文件上的名字。她后来在报告中说,这份文件到了当地的波兰抵抗团体中时,团体中成员的反应就像是火花跳进了火药中——炸了!
4
往返造纸厂的运输逐渐频繁起来,显然易见,“纸张小队”确实赢得了小型的战役,但是输掉了整场战争。只有一小部分宝藏被救了下来。1943年春天,肖兹克维想出了一个新的对策。他要在YIVO大楼内部建立一个藏书地。这个新藏书地点出现后,可能会省去偷书的风险。
在检查了大楼的结构后,肖兹克维在阁楼的柱子和大梁下面发现了很大的洞。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分散波兰守卫威尔布里斯的注意力,这样肖兹克维和其他人就可以在午饭时间将资料迅速搬上阁楼。成员们很幸运,威尔布里斯对于战争打断了他的正式教育感到很可惜,他兴奋地接受了工作组两个成员,费恩施坦博士和戈登教他数学、拉丁语和德语的提议。当学生和老师全神贯注地学习时,“纸张小队”的其他成员就将资料转移到阁楼上。
故事说到这里,让我们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这些图书和文件?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为做一件事,不惜用生命犯险,除那个高于生命价值的信仰之外,概无其他理由。这个信仰就是:文学与文化具有终极价值,这种价值超越了任何个体或团体的生命价值。死神就在不远处,他们选择将余下的生命,贡献给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施默克来说,书籍在他少年时使他摆脱罪恶与绝望,现在是他回报的时候了。亚布拉罕·肖兹克维怀有一个神秘的信仰,他相信诗歌是使万物拥有活力的力量。只要他一直忠于诗歌,写诗、读诗、拯救诗,他就不会死去。
这些偷书人都相信战后一定会有犹太人需要这些文化宝藏。会有人活下来,并且追回这些宝藏,然后重建犹太文化。但在维尔纳犹太聚居区最黑暗的时候,谁都不清楚光明何时会来临。
维尔纳骄傲的犹太市民们、“纸张小队”的成员们,他们相信团体存在的意义就在图书与文件中。如果斯特拉舜图书馆的书籍、YIVO里的文件还有昂斯基博物馆的手稿被拯救了,那么即使犹太人灭绝了,“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也会长存。卡尔曼诺维奇说:“也许战后还会有犹太人,但可能没有人可以再用犹太语言写书了。”
肖兹克维用一首名叫《麦粒》的诗表明他在“纸张小队”中工作的信念。诗写于1943年3月。他写自己奔跑在聚居区街头,“犹太文字”在他臂膀中,像抚摸孩子一样,他抚摸着文字。羊皮纸向他哭诉:“把我们藏进你的迷宫!”把资料埋在地下时,绝望灌满他的身体。但他被一个古老的寓言安慰:埃及法老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并命令他的仆人在棺材中放上麦粒。九千年过去了,棺材被打开,麦粒被发现、播种,最终长成一片美丽的麦田。有一天,肖兹克维写道,他在维尔纳聚居区的土壤中种下(而非埋葬)的麦粒,也会发芽结果。
也许这些文字会等待,
并且重见隐现的光芒——
在注定的时间
出乎意料地盛开?
就如同那史前的麦粒
长成了麦子——
这些文字将会滋养
这些文字将会拥抱
它永恒之路上遇见的人。
5
不久,小队成员得到消息,YIVO的战前主管马克思·温瑞克在美国生活得很好。这给了“纸张小队”力量和鼓舞。1940年温瑞克在纽约定居,并且将YIVO的纽约分支转变成总部。克鲁克和卡尔曼诺维奇听到YIVO在美国重生的消息时喜不自禁。讽刺的是,这个消息来自波尔。
波尔经常阅读《意第绪先锋日报》,还会剪下展现了犹太人道德堕落和仇恨的文章。(他认为任何对迫害犹太人的公开谴责都是反德国的“仇恨”实证。)在细读《先锋报》中的一则消息时,他看到一篇文章介绍1943年1月8日至10日YIVO在纽约召开会议。读完消息后,他把报纸给卡尔曼诺维奇看。这篇文章报道了卡尔曼诺维奇战前的几位朋友和同事的讲座,他们都是从华沙和维尔纳逃走的难民学者。消息还提到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正式将YIVO总部转移到纽约。快乐在卡尔曼诺维奇的心中蔓延,他冲进聚居区图书馆,与克鲁克分享这个消息。两个人相拥,喜悦的泪水流下脸庞。克鲁克在他的日记中说:
如果你从没到过维尔纳聚居区,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没有见过这里的YIVO现在的样子,你就不会明白,获悉美国YIVO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尤其是得知他们所有人还活着,在美国,并且在重建犹太学术研究的主体……
卡尔曼诺维奇和我彼此祝福对方能够活着,直到我们可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YIVO的这一部分。虽然命运待我们如此残酷,让我们承受如此悲惨的聚居区生活,但是我们在得知犹太文化与意第绪文化还活着,并且继承了我们共同的理想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纸张小队”的成员们现在确定“立陶宛的耶路撒冷”没有被完全摧毁,它幸存的部分在纽约继续生长。有一天,纽约的学者们将继承幸存的书籍与文件。这个想法是照进黑暗中的一抹亮光。
(《偷书人》[美]大卫·E.费什曼/著,姚丽蓉/译,西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