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养宗《去人间》:现实之重 魔幻之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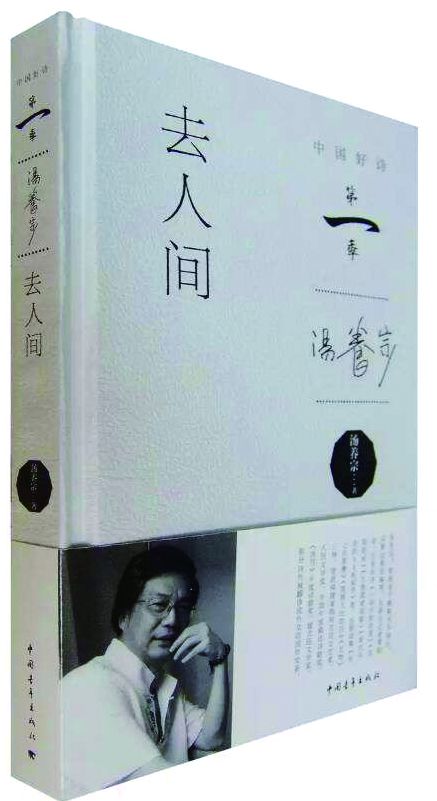
诗歌创作意味着“在着意为之的晦暗中,借助暗示性的、永不直白的词语召唤沉默不言的实物”,而诗人是“字母魔术师”。汤养宗将经过高度反思的诗歌与魔幻而古老的灵魂层面相结合,使他的诗句具有语言魔术,集反常性、神秘主义和先锋性为一体。他发现“人与万物间的隔阂其实是光”,以诗人的敏锐和颖悟,“打通过无数的事物”。在诗里呈现他的“凹与凸,因与果,对与错”和“呼与吸,隐与显,拒与纳”。他的生命意识、生存经验和道德判断以及诗歌中体现的他的气息,他遮蔽了什么彰显了什么,拒绝了什么接纳了什么,这些共同构成了汤养宗诗歌的繁复、精约和奥义。
读者和作者二者的关系,在汤养宗《房卡》里被比喻成“房锁”和“磁卡上的密码”,这是读者通过阅读完成的“还魂术”,也是作者通过写作完成的一次“密码设置”“穿墙术”“虎跳”“飞翔练习”。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是通过诗歌文本的中介来完成的,二者之间的默契“相当于一句黑话通过了对接”,然后,门开了。汤养宗在诗里写到:“不要光/这里只凭认与不认。但黑暗/显然在这刻已裂开。”在《圣经·约翰福音》里有这样的经文:“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来比较阅读,有种互文性的感受。这会不会是另一种通过了对接的“黑话”?
汤养宗的诗歌中有一种打破固有秩序的力量,有反常性和打破常规而形成的张力。打破的过程也是一种重新确立诗歌美学和秩序的过程。秩序就是“蛇走蛇路,牡丹想开花就开花”“无路可走的汉,身上已长出穿墙术?”(《我想去天堂一趟》)作者显然对秩序是心存不满的,作者应对秩序的“捆仙锁”,用的是自己的“读心术”,穿墙而过或是飞翔。他用魔幻之轻来对抗现实之重,“长羽,长翅膀,却隐忍地用着木质的蹄掌”(《云中散步的大象》)。从诗句中,我们似乎可以从反常性的举动中窃取到事物之美,从无望之中生出希望。
汤养宗心中所在意的人是“子虚乡乌有人”,想去的地方是“圣城。或者荒域”,这些都与现实有点格格不入。“一个人愿意痴迷地/在同一块石头上让自己被绊倒多次”《红豆诗》,“同一块石头”譬喻着同一个现实,“让自己被绊倒多次”,看似愚不可及,也是一种大智,是希望用“执念”来破除“现实”的坚硬与冰凉。“我不是百足虫,又能去哪里”“每天用假腿跑步,假的塔,假的桥,还假惺惺说”,汤养宗用“假”来弥补“不是”的不足,造成了一种“以假乱真”的心理满足感。汤养宗在《某年某月某日,致某人》中写道:“某年某月某日,小雨,空茫,十个指尖又布满修辞。”可见他的第11根手指是用来反修辞的。他所期待的不是“蛇走蛇路,文字出现别的脚印”。他在另一首诗里颠覆了一首诗里所建立的哲学和准则。“相当于一句黑话通过了对接”,已经替换成了“更没有土匪窝的黑话或晦暗的对接”(《声声慢》)。汤养宗不再考虑外部世界和他者,而是更多的潜入内心世界,他在意的是“我心头的雷声已赶不上一阵雷声/是我这张嘴再难以接近大地的声母。/是我再没有/隐身法”。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契合,口中的言语与真实事物的触摸、还原和那一种血脉关系,只能依靠“声声慢”来逐步接近和实现。“那么,再慢下来,让语言继续变黑/只剩下我对你的手势。只剩下,不知如何是好。”从充满无奈和悲凉的变黑的语言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只剩下我对你的手势”是一种V字型的胜利者的手势了。
汤养宗的一首诗绝非“一首诗”,对他的一首诗的深入阅读离不开他的其他诗的佐证。一首诗是另一首诗的引子和注解,或者说,所有的诗都是一首诗。他的所有诗是连贯的,互文性的,他在写一首“大诗”。他自己在诗歌中说,“就像这首诗遇到了真正的黑夜/而另一盏灯,点在另一首诗里,另一个/好命的人,正在那里与一个鬼谈笑风生。”(《掘井者》)如他写《一个人大摆筵席》《虎跳峡》《穿墙术》,用一首诗立一个意象,再在另外的诗歌里用这一意象,“它”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使用了,已被汤养宗赋予了新的内涵。汤养宗多次写到穿墙术,如在《欠条》里说:“往年立下的界定,穿墙术,去与不去。”又在《夜深人静时你在床上做什么》里写道:“有时不是这样,类似要穿墙而过”,又在《三个场景时间里的一个叙述时间》里写道:“而另一个时间,我还写穿墙术”,还在《我还没有到老,我已认下什么叫垂暮》里写道:“也问过别人/穿墙术的要诀,得到的回答是,出手易/变回来难”。汤养宗反复提到的“穿墙术”,实际上是作者“破障”的一种企图,“不群”的练习,一如他在多首诗歌中提到的“练习倒立,练习腾空翻”和“像在午夜间作一次莫须有的飞翔”。
《总是一而再地拿自己的自以为是当作天大的事》,与其说这是汤养宗的一首诗的题目,不如说是他的一个诗歌观的体现。“总有意外的裂变之力被我找到/谢天谢地,反常理的人没有遭受刀棍”,诗歌中提到的“自以为是”,“裂变之力“和”反常理”,应该说是汤养宗诗歌的三个特性。“把夹竹桃养成了大红大紫的玫瑰/改过闪电的线条,教会了两三块石头开口说话/有一天,还责令落日分别用三次降落于三个山头。”密集的“反常理”的诗句同步造成了“裂变之力”,汤养宗的“自以为是”,实质上是甩开了众多追随者和模仿者,在众多的诗人里,彰显出一个独绝的自我。“反常性”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故意将开水瓶的塞子拿掉,为的是/让什么早点变凉”(《越来越想损坏自己》),“富翁与穷光蛋要公共抓住悠悠白云的技艺/这里在研磨,反向着工作/从黑磨到白”(《戒毒所》),“深夜的镜前,我独自伸出一条长长的长长的舌头”(《万古愁》),“先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再变成石头/再日久月深地在海滩上听潮,之后就成佛了。”(《捡一块石头当作佛》),“蚂蚁伸出了一条小腿/砰的一声,被绊倒的大象便一头栽在半路上”(《坚信》),等等。
“象征不仅是诗歌与经书共有的修辞方式,不仅是神圣启示所得以传达的方式,还意味着一种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秩序,象征所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它建构了一种关于意义的伟大链条,建构了世俗世界与道德根基的联结形式。那是用纯粹的能指说话而意义却能够被一个想象力共同体所普遍感知的时代”(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汤养宗的诗歌里寻求重新确立人与世界之间的象征的意义关系,旨在修复词与物、语言与自然之间疏离的关系。他是“没有确定信仰的炼金术士,其诗作就是没有神秘的语言炼金术”。
在《星云图》这首诗里,“十个指尖”成了联结“天上的星云”与“心”的纽带。诗人汤养宗握有“一些星光的轨迹”,握有消弭词与物,语言与自然之间的沟壑与距离的神秘力量。“指尖上的乱云”,形成了一种人不是外于物的感觉,事物与人本为一体,神秘的符号隐藏着人类返回天国的奥秘,“说不定就是今夜,就随同白虎沿那些弯道逃遁”。诗人,终其一生所摆弄的词语,也只不过是模仿整个星空,让词语像星星一样各归其位,让词语获得肉身。“那些叫做簸箕和斗笠的图案”暗含着簸箕的扬弃和斗笠的接纳,也在呼应着诗人《房卡》里说的“呼与吸,隐与显,拒与纳”。
汤养宗在《与某诗人谈心》中写道:“当神委托把它写出的人/写出它,没有第二人可以插进来指手画脚/将一块石头改换成另一块石头,说这座建筑/不是这样,应该那样”,这与胡戈弗里德里希的著作《现代诗歌的结构》中的论述不谋而合,“诸神满怀恩惠地赠与我们一句诗,但是之后就要靠我们来制造第二句,这第二句必须与它的超自然长兄相称。而这唯有起用经验与精神的全部力量才能刚好达到。”《与某诗人谈心》是一首以诗论诗的诗歌,类似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面谈到了多条诗歌的秘籍或者诗歌的特性。第一,诗歌自己有嘴唇,独自地呼吸。第二,有时是棉,也是铁(诗歌的柔软与坚硬)。第三,每首诗都有无数次往外走的可能,但最后只能是这一个(诗歌的唯一性必然性)。第四,处子的血(诗歌的独创性,戒他人染指)。
他作为诗歌上的异类,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人群作对,同时他也是自己的“异类”,左手与右手对抗,我与“反我”的对抗。“我无群无党,长有第十一只指头/能随手从身体中摸出一个王,要他在对面空椅上坐下”《一个人大摆筵席》。“我一直是你们的另一面/用相反的左边,对决你们的右边/在反方向,隐姓埋名,肉身在石头里/侧转着身子,睡成与谁作对的逆子模样”(《私章》)。甚至在一首诗里也会出现左右互搏和悖论。在《私章》一诗里,一方面写“纸上加盖印章,将一纸如麻的文字/确认为命中的确认/这等于是要我交出自己的反骨”,另一方面写“一个人的反面,再不能确立/多像是,一颗人头终于落地/白纸上,映出了一滩喷出的血。”到底这“私章”是盖还是不盖?一个我对另一个我是不是确认?这不是单纯靠语言形成的张力,而是依靠复线的结构形成的内容的张力,诗意的张力。为与不为反倒退居其次,而所为的“内容”变得“举重若轻”了。一纸如麻的文字,变成了一颗颗人头。白纸上,映出了一滩喷出的血,既是印章盖出的红印,也是诗人用血给“诗”进行的洗礼。
(《去人间》,汤养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