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枯叶返绿,传来开花的声音 ——忆满族诗人徐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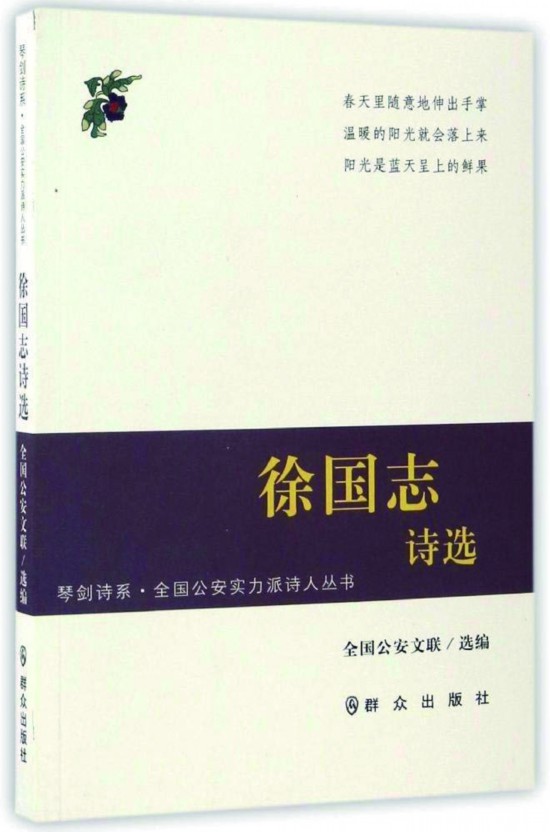
那天见到白瑞兰姐姐,她说自爱人徐国志走后,她还在懵懂之中,忽然不清楚生死的概念了,似乎每天依然对话,依然谈诗,依然创作。她说她现在每天都要把他以前每天必看的《满汉大辞典》《满族通史》《承德满族》三大卷书认真拿在手里翻看一遍,这是他这两年的习惯和心结。他总是说,作为满族后裔,他太应该在创作中去寻找作为满族“根性”的东西了。白姐姐没有流泪,看起来那样平静,又那样理性,但总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心疼,我的心总像有根针在刺一样。这三册书,我的书柜里也摆放着,国志兄的诗集和小说也摆在旁边,回到家抽出来看,泪不觉间已打湿书页。“传神文笔足千秋”、“几回掩卷哭曹侯”,此刻,深味赵翼的心境。一为痛,一为惜。
当初听到噩耗的时候,我正在故乡上塞罕坝的路上,我几乎怀疑我的耳朵,有一刻的恍惚,直到电话那端传来啜泣,我才明白昨天那个在《诗刊》社“青春回眸”会议中给我发短信要我到后座说事的徐国志真的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眼泪不听话地在眼圈里打转,不听话地落下。为了不影响车上的其他外地同行诗友,我尽力克制着,抬眼望向窗外,正是一条不断向上的道路,高接云天,蔚蓝的天空大朵大朵的白云,像舒适的床,又像温馨的仙境,那样安详,那样素美。路两旁的树葱茏蓊郁,青松挺拔,白桦玉立,还有不知名的花朵,汇合成一片一片的花海,在远方如诗如画。我想,国志兄一定是走向这样的生态之中了,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相邻,风土气候植被颇类,这样的山川草木、蓝天白云都是他的栖所。他是心梗突然离去的,尽管这令人难于接受,但如此安详而去,也是一生做好人修来的善终。念及此,总算有些慰藉了。后来在承德文联主席王琦和承德作协主席刘福君的操持下,承德文友和全国诗友以诗送别,在追悼会的当天出版了专刊《诗送国志》,共162页,收录75首诗作。因时间匆促,很多诗友还没有看到相关消息,很多纪念诗作还没有来得及收录进去,但一本《诗送国志》已足以看到国志兄的为人和口碑,这是他的谦和、宽厚、峻洁和美好的人格呈现。
我和徐国志的亲近,源自伊逊河的哺育。尹逊河流过我的家乡木兰围场,也流过国志兄的家乡隆化,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我们常常谈论这条河流,谈论这条河流岸边的文化,也谈论像河流一样绵延无尽的文学。谈彼此作品的得失,谈经典作品和身边朋友们的佳作,那个时候,我们像河岸垂钓的孩子,既天真又成熟,既安静又激荡。我们更像两个兄弟,家乡风物总是彼此说不尽的话题。国志兄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位自然之子,一位尹逊河的赤子。他对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近年来,他的足迹走遍了承德的名山胜水,甚至常常驱车百里回到隆化乡下,遍访山山岭岭。他春天采野菜,秋天采蘑菇,不仅识得曲麻菜、人行菜、苦麻子、婆婆丁、猪毛菜、山韭菜、山蕨菜、黄花等各种野菜,还知道哪里的蘑菇长势好,哪一种蘑菇更适合什么方式的存放和烹调,他更通晓它们的药性和营养价值,他还常备着一个红桶,采摘的专用桶,这样在漫山遍野的碧绿中不至于遗失。他谈这些的时候,更像是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过日子的山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全国知名的公安作家。他的身上没有锋芒,他的锋芒就是他匍匐于土地、谦卑于自然,他的身上也没有坏的习气,他的习气就是他的土地情怀、山水理念。这些足迹和喜爱,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素,他写山,写草,写花,甚至成系列来写《雪落燕山》《拜访杏花》《再写杏花》《燕山杏花》《高于风的树叶》《热河水草》《白桦树》《探访不知名的黄花》《一棵草经过的地方》等,特别是他的《燕山草木》和组诗《云过草原》,是他重要的代表作。《燕山草木》中说:“注定我是恋家的人/离不开燕山的一草一木/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可以说,国志兄一生都在践诺着这一诗行,他最终埋在燕山脚下、伊逊河畔,生生世世与草木为邻,与自然相依。
徐国志是我的鲁院学长,我们一样以曾经是鲁院的一名学子而骄傲。每每谈及鲁院,谈及鲁院的讲座、鲁院的老师和鲁院的同学们,我们依然像个孩子,兴奋之余更多自审和自省。同样作为满族人,我们都有着同样热爱民族文化的情结。他写《额娘》,写《新姐》,他把他理解的属于满族民族的特征写进了山里、水里、人心里。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们曾在会场外聊天,他兴奋地谈起他刚刚跟石一宁老师的通话,他说要请老师来承德,要和北野等人一起商量一下《民族文学》创作基地落实的问题。他又嘱咐我,身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要充分立足高校平台,打造全国性的满族文学研讨会和满族作家驻校制度以及全国性满族文学大奖赛。他侃侃而谈,胸有成竹,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片纯净的湖水,那是满族文学的辉煌理想。我被深深感动,并立即自责,这么多年,我想得太少了,而国志兄已经筹备了很久,已经扎扎实实努力了。我们握着手道别,彼此郑重相告,我们为满族文学做些事,谁也不能落了谁。后来听白姐姐说,他写字台上最后存放的资料,是丰宁满族剪纸传承人石俊凤的资料,原来他一直在筹备他的下一部报告文学,他要以满族人的情结写满族人,以男人的视角写女人。听完,我们久久没有再说话,内心翻涌着松涛的喧响,那样激越,那样粗犷。
徐国志是我尊敬的兄长,他始终有着美好的憧憬。他做人谦恭有信,他常说,活着都不容易,但凡朋友的事他能帮上,他都会尽心而为。他做事认真严谨,作为承德市看守所副所长,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曾多次受到单位和政府嘉奖。他的创作坚守着真实的品性,他曾这样描述他的真实生活:室内养花,键上敲字,楼后看押几百名犯罪嫌疑人,每天情绪在几样事物间流动。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一天。国志兄向往美好,他的创作始终都在为人性的真善美而歌,为民生的疾苦而书,为自然的天籁而颂。作为公安战士,他创作了献给为国家安全、战斗在反恐一线的公安民警的长篇小说《奥雷一号》,获得“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三等奖;他曾七上丰宁小坝子,认真考察从小坝子的风沙灾难到绿化治沙的民生生态工程,写出了3万字的报告文学《狙击黄沙》,刊发在《民族文学》2017年第4期上;他也几次赴东北考察,写出了以描写东北虎生存状态为主题的3万字报告文学《大雪深处》,刊发在《民族文学》2018年第4期上。
在朋友们的心中,徐国志最难得也最让大家爱戴的,莫过于他对亲情的珍重。国志兄的爱人白瑞兰大姐,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文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是河北一位颇负盛名的诗人了。伉俪二人情感极好,创作上彼此激励,成为承德文坛的佳话。曾广为流传这样一个段子,有一天清晨醒来,白姐姐第一句话便是:昨晚梦中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诗集中带山字的句子有21处。国志兄不信,翻书核对,一数还真是,便疑惑相看。白姐姐哈哈一笑说,天替我数过了。白姐姐的父母都已经90多岁了,老人家一直跟着女儿女婿生活。前年,白姐姐腰间盘病犯了,一直住院,国志兄一面照顾着家里的老人,一边服侍着妻子,任劳任怨。两位老人也将徐国志当成亲儿子,国志兄还常常陪老人下棋、打牌和听戏。我在承德市文联组织的“潮河情·滦水行”京津冀三地作家记者大型联合采风活动中,和白姐姐住一个房间,当我听到白姐姐说起这些家事,我总能够感受到白姐姐从内心里洋溢的幸福和敬慕。白姐姐对国志兄的评价是:我嫁给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和我一起生儿育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和我一起赡养父母。这是多么朴素的美德啊。徐国志对自己的兄长也是极好,竭尽所能给予帮助。国志兄小姨子的女儿一直在他们家里长大,国志兄视其为亲生女儿一样。她在18岁突发顽疾去世,国志兄为她写下了无数的悼念文章,他的那组诗歌《写给子溪》感动了很多人:“现在子溪再也不应声了/只有病还活着,在亲人的心里肿胀十八岁的病,比夏天还绿还茂盛/跨越了生命的边界,现在/只有求助大地的力量,划出界限/我们将子溪栽进泥土,连接地气/期待枯萎的叶子返绿,期待某个/清晨,传来开花的声音”。
国志兄,当我再读这些句子,我的悲伤和当时的你一样,我的期盼也和你一样,待叶子返绿,你一样会在某个清晨,传来开花的声音。
会的,一定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