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岩:传奇如何虚构历史——读贾平凹《山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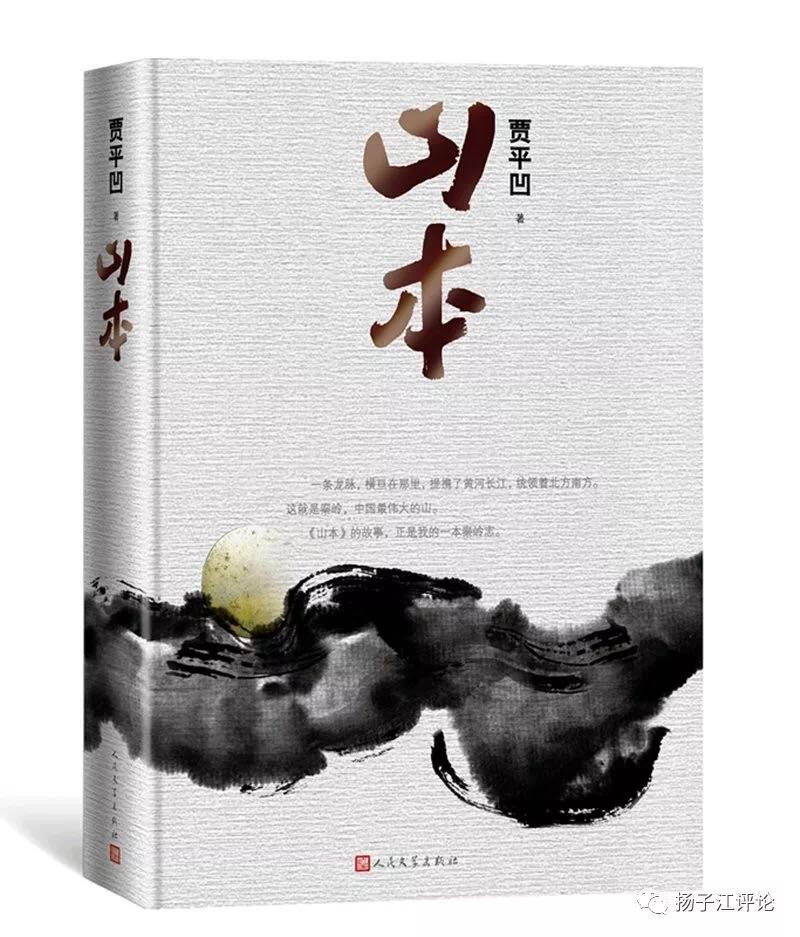
一
“历史”终结的时候,我们方能回溯其过程及其意义的复杂性,正如“虚构”的发生,也只有语言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地谈论起其形态和意图。只是,当《山本》这样的文本出现的时候,“历史”与“虚构”在其中相互纠缠,既彼此成全又相互消解、掩盖,描述、谈论其中的涉及问题都变得尤其困难。
所以,当一切都尘埃落地,从结尾谈起,未尝不是一个合适的办法。可能是突然降临的死亡,造就了《山本》仓促而稍显生硬的结尾:
这日子破了,心也破了。抬起头来,而安仁堂的那几间平房却安然无恙,陈先生和剩剩,还有一个徒弟,就站在大门外的婆罗树下看着她。
……炮弹还是不停地在镇里落着……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迭嶂,以尽着黛青。[1]
城池灰飞烟灭,历史也似乎停滞,幸存者意味着什么,便成了一个问题。安仁堂的主人陈先生是位“瞎了眼的郎中”,他不仅疗救涡镇人的身体疾患,而且还能纾解这个地方的街坊纷争和人伦纠葛。这个试图把群体的肉身和精神复归健康状态和良好秩序的人物形象,难免使人想起那个在古炉村游荡的“善人”。善人认为身体疾患源自心病,所以大部分患者都是通过与善人聊天而被治愈的,同时善人又喜欢用疾病的发生和治愈来描述人心和外部世界秩序的崩塌、错乱及其复位。与陈先生一样,善人同样是个能够同时修补肉身疾患和伦常失序的人。于是,他们都成为了“革命”的幸存者……
贾平凹对幸存者的偏爱与执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会在《后记》中刻意地引导读者对这些形象的理解。关于陈先生,他强调:“我需要书中的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2]对于“善人”,他则评价到:“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3]但是就实际的美学效果而言,这些形象因其高蹈、漂浮而缺乏基本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为意图压垮了技术。贾平凹念兹在兹的是儒释道混杂而世俗的实用观念之于人心、社会的干预和疗救。他对这些前现代思想的效用有着近乎宗教般执迷。这份执迷会驱使他有意识地忽略或者无意识地跳过“血肉之躯”的丰富性、可能性在技术上的要求,而制造出一个“扁平”的人物。我想,大概是因为“扁平”挤压了思想的复杂、语义的缠绕,可以较为直白、纯粹地传达意图。
另一个与此相关问题是,从叙述的角度来看,幸存者陈先生的行为从未构成任何推动叙事进程的动力,善人亦是如此。但是,他们的身影又几乎穿梭于与叙事进程相关的场景中。在场的时候,不提供动力,不在场的时候又以缺席的方式提醒存在感。这一切无疑是作者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正如陈先生,他参与了涡镇的日常,救死扶伤,抚慰人心,其行为却无法与叙事情境、故事发展形成张力关系。他的存在更像是舞台上的烟雾,制造氛围,烘托气氛,却不构成动力。
这样看来,故事里的幸存者竟是作者观念凭借权力意志运作的产物,在作者观念、意图与技术以及美学效果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幸存者更是胜利者,尽管这个依凭权力意志制造出的文本中的克里斯马(Charisma)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存在。我想,作为讲故事的高手和老手,他并非不清楚这种处理方法的简陋之处。但是,他依然铺排了三个“需要”来强调合理性。所以,这种“需要”,可能真的是贾平凹个人的“内在”的需要。对此,可能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带着“同情”来看待这个问题。需要补充的是,如何看待贾平凹在前现代问题上近乎宗教的执迷态度,是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比如说,当有人用“传统”及其相关的概念和表达形式来描述这个问题时,价值判断一定又会是另外的样子。对此,我只是暂时搁置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4]。当我使用“同情”这个词的时候,是想强调,当我们站在某种思想的对立面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平等的态度、移情的方式,去理解贾平凹的这种内在需要,从他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贾平凹的困局”。
《古炉》直面了“文革”,《山本》则面对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5],两者面对的都是动荡的大历史,简单说来,皆为“乱世”。《古炉》里的故事是乡村里的文革武斗,并混合着宗族械斗;《山本》里故事则是山沟里的革命和背叛,以及落草为寇或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皆发生于封闭的乡村,主体皆为对外界信息接收滞后的农民。所以这些故事的基本进程就是,乡土社会被迫卷入大动荡的时代,秩序中断,伦常崩坏,简单地说,就是“乱世”冲击、摧毁了“安稳”。由此,混乱和秩序构成了叙事进程中对立的两极关系。考虑到贾平凹关于“安稳”和“秩序”的理解相对简单和直白,那么,如何描述“乱世”之“乱”则成为贾平凹书写历史的难题和困局。所谓“乱世之乱”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以《山本》所依托的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中国历史来说,绕开可能的话语禁忌和具体的史实描述,仅以观念及其代表的利益诉求来讲,几乎所有重要的价值观冲突和利益纠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暴力为手段作为“沟通”问题最主要的方式。面对历史的迷乱和狂暴,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困局,只是贾平凹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解决方式。他选择了一套朴素、恒定、简单易操作的价值系统来作为它描述乱世景象的平台、视角和参照系,我们可以将之通俗地理解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为此,他不惜以简陋的技术手段去牺牲故事里“乱世”所可能带来的充沛、复杂的审美张力和思想景深。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面提及的贾平凹的三个“需要”其实是具体的、直白的:风水宝地里出土的“铜镜”,其模糊的镜面中折射终究是晦暗的宿命之光,一切意外和断裂都因命定而失去讨论的必要;同样,历史的原罪和生机、血污和进步等复杂的辩证关系在“庙里的那个地藏菩萨”普度众生的目光里也只能被化解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廉价叹息;陈先生更像是一整套伦常秩序和价值观的拟人化的随从或向导,是他在历史迷局中穿行的陪伴和拐杖,是他觉得他可以轻松撬动大块历史的阿基米德支点。所以,幸存者确为贾平凹的“内在需要”,这不仅在技术上能够减轻他书写历史的难度,更是在心理上构成了他从“现代历史”中从容撤退的后花园。
二
指出《山本》在技术、审美和观念等层面出现的“症候”,并不意味着要去否定贾平凹书写历史的真诚和雄心。因为,这些“症候”的出现,与讲述和这段历史有关的故事的难度,是有关的。如贾平凹所言:“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6]这样的表达再次令人想起《古炉》。《古炉》的英译名为“china(瓷器)”,所以,通常的理解是,那个以烧制瓷器为生的村子里发生的故事,也就成了关于“继续革命的中国”的隐喻。这样的理解正确而直白却也没有多少值得继续讨论的空间,因为作者的历史观一直在牢牢地牵引着故事进展。但这样的思路未必适用于《山本》里的涡镇故事。因为,情境的变化使得雷同的表达则有了不同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话语空间的边界问题,我将尽可能地使用中性或略带抽象的词汇和表达形式来谈历史问题。这便意味着,这种谈论历史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限制、阻碍乃至曲解我对于这些历史的真实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判断。
如果把“文革”理解为,一个政权相对稳定的现代主权国家依凭非制度化的权力意志自上而下在国家内部发动的继续革命[7],那么就国家政治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或被迫卷入的深广度而言,局部经验与国家历史的整体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同构性的,因此,局部的历史也就成为总体性历史的某个例证。所以,古炉村的故事也就有了隐喻中国的可能。
用“一地瓷的碎片年代”来描述19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不是用心良苦的隐喻,更像是力不从心的写实性白描。因为,除了具体的碎片和局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任何层面,都无法找到对这段历史进行总体化描述的有效途径。比如说,当时的各种形式的政权、各种军事力量占据着地理上的不同区域,却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中国”统治的合法性,长时间、大规模地四分五裂;各种政治势力鼓吹不同的意识形态及其支持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为了取而代之而不知疲倦的斗争,此消彼长,胜负难分;国际政治势力彼此之间的结盟、分裂参与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中,任何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皆是千头万绪……
所以,虽说同为中国“现代”历史意义上的“乱世”,但是《古炉》中的乱只是国家内部秩序暂时的失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可控范围内的失控。因此,前文提到的现实中局部与整体之间在某些经验上的同步性、同构性,便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搭建了一条宽阔的路,隐喻的生成顺畅而直接。当然这也可能导致隐喻含义的单调而直白。
而《山本》里的“乱”,却是一种无中心、无方向意义上历史景象的胶着、混乱和壮烈。想象一下在这样情境中讲述故事的困境和可能。特殊历史时期四分五裂的时局和地理空间,以及交通、信息传递的滞后和阻碍,很容易造就地区经验的特殊性。过于执着于经验的特殊性,很容易忽略其与开放性、可交流性的之间微妙的张力关系。顺着特殊性经验所鼓励的震惊、兴奋和好奇走下去,小说很可能会走入传奇、异闻的“歧途”。封闭时空里的故事,往往是会切断历史维度的。但不可否认,这也是小说的一种写法。但是,贾平凹偏偏是个企图书写大历史的人,“龙脉”“秦岭”“黄河”“长江”“黄河”“南方”“北方”这些负载着宏大意义的词汇占据了50个字的《题记》的大部分空间。设若贾平凹想在《山本》中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或者说复调的历史隐喻,那么,“虚构”里的涡镇就不能仅仅是秦岭的化身,或者说,涡镇不能仅仅是装载贾平凹所珍视秦岭里的那些草木鸟兽、人事传奇的容器。因为,时空的封闭性要被打破,经验的特殊性才能在比较中得到区别和确认。同时,不同类型的经验相互抵触、影响,不同的视野、感觉交汇、叠加,方能激发故事的丰富性,由此,意义的多重性和历史隐喻的复调方有发生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我们不妨将把“涡镇”理解为一个场域,影响1920年代、30年代中国历史的各种因素,包括贾平凹念兹在兹的与秦岭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在这里相互激荡,交织成的错综复杂、泥沙俱下的秦岭大故事。重新想象这个过程,便有了《山本》。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涡镇”涤荡去秦岭所赋予的地理属性和限制,而成为隐喻意义上的历史漩涡。而“涡镇”之“涡”本就是水流交汇、形成漩涡的意思:
涡镇之所以叫涡镇,是黑河从西北下来,白河从东北下来,两河在镇子南头外交汇了,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涡潭就动起来,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接着如磨盘在推动,旋转得越来越急,呼呼地响,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地。据说潭底下有个洞,洞穿山过川,在这里倒一背篓麦糠了,麦糠从一百二十里外的银花溪里便漂出来。[8]
三
于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形塑了涡镇的故事形态,便成为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历史”与“虚构”并置,多少会产生诡异的意味。因为,我们既不能跟“历史”许下关于“真相”的承诺,亦不能与“虚构”达成关于“谎言”的和解。所以,“虚构”中的“历史”,或“历史”如何进入“虚构”之类的话题被提起时,讨论将变得极其困难,因为,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像是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诞生了:我们会假定,用文字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真实地记录和还原,或者说存在一种以此作为目标的叙述,我们称之为“历史”;而那些把未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当做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叙述的文字,则被称之为“虚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离开属于权宜之计的知识分类,我们将无法谈论任何问题。然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刻,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他们挑战着我们对于知识分类及其惯性思维的确信,提醒我们相对模糊边界有助于更清晰地审视问题。《山本》中的涡镇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
《山本》的开头写到:“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9]这是一个典型的“讲故事”的开头。操着世事沧桑的腔调,准备从“很久以前”说起。在我们的常识范畴内,这是“虚构”开始了。贾平凹在《后记》里也在印证这一点:“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10]“传说”也好,“传奇”也罢,其实都是我们在“虚构”范畴可以把握的对象。事实上,贾平凹并没有让《山本》变成奇崛的故事和怪力乱神的想象力的跑马场,时不时会有真实的历史片段插入故事。比如说:“形势已经大变,冯玉祥的部队十万人在中原向共产党的红军发动进攻,红军仅两万人,分三路突围,一路就进了秦岭。”[11]抛开具体的细节问题,判断这句话所涉及的史实并不难。因为,冯玉祥充满争议的一生中,唯一一次与中共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便是对“渭华起义”的镇压。1928年4月至6月间,刘志丹在陕西东部起事,冯玉祥派出三个师围剿[12]。
但凡与历史相关的“虚构”,大约都会以所谓真实发生的历史作为叙事背景。尽管我们与“虚构”可以达成关于“骗局”的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构”就此放弃伪装成真实的企图。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技术问题。但是《山本》并未止步于此。历史片段频繁地出现在涡镇的故事中,他们不仅构成了情节发展和叙事进程的极其关键的动力因素,而且规定了故事发生的基本走向和形态。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
涡镇的故事取得实质性进展,始于井宗丞成为涡镇舆论的焦点时:
保安队剿灭了一股共匪,把共匪的一个头目的头割了就挂在县广场的旗杆上。涡镇的人似乎听到过共产党这话,但风声里传着共产党在秦岭北面的大平原上闹红哩,怎么也进了秦岭?阮天保就说共产党早都渗透来了,县城西关的杜鹏举便是共产党派来平川县秘密发展势力的,第一个发展的就是井宗丞。为了筹措活动经费,井宗丞出主意让人绑票他爹,保安队围捕时,他们正商量用绑票来的钱要去省城买枪呀,当场打死了五人,逃走了七人,后来搜山,又打死了三人,活捉了三人,其中就有杜鹏举,但漏网了井宗丞。[13]
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并不难判断具体的史实背景。中共全面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事情[14]。稍后的6月,冯玉祥便开始在其辖地河南、陕西、甘肃三省进行“分共”和“清党”[15]。还原此处的史实细节旨在说明,贾平凹将传奇的发生或者说虚构的走向夯实在真实历史的底座上。当历史明火执仗地闯入虚构,涡镇的故事便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开始,借用萨义德的一个术语,即“开端”:“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指定一个继之而起的意图……,这样,开端就是意义产生意图的第一步。”[16]很显然,从这个时候开始,涡镇的故事生长出一条重要的线索,或者说“革命叙事”被植入涡镇的日常,因为秦岭的珍禽走兽和奇人异事孕育不出“现代革命”的种子。这是一个历史引导、牵制虚构的叙事过程。随后的若干处关键性情节亦印证了这种策略。
继续举例子说明。井宗丞所主导的“革命叙事”在崇山峻岭中高歌猛进的时候,显豁而重要的史实依然与这个故事如影随形,并构成了决定故事基本形态的重要因素。
当红十五军到达平原后和北方高原上的红十七军会师,开始冬季反攻,占领了平原西部一座城市,又围困起另一座城市,省委指示红十五军团进一步牵制国民六军不得去平原支援,宋斌就想集中力量先攻下防卫相对薄弱的麦溪县城,建立第一个秦岭苏维埃政权。对于宋斌的主意,蔡一风一直有些犹豫,他认为以眼下的力量还不足以能拿下麦溪县城,既便拿下,能否长久守住?。[17]
这段引文的信息集中于“城市”。这个名词同样构成了1930年代前半段中共内部路线分歧的关键词。从中原大战爆发后李立三提出“没有中心城市的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18],到王明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以更为激进的姿态继续推行“城市中心的观点”[19],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暴动和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是红军军事行动不可违抗的原则。受此影响,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在1935年之后才相对平息。尽管在后来的一些党内决议和党史叙述中,将这些观点及其相关行为被定性为“‘左’倾冒险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20],但是在当时,李立三、王明等宗派团体一样可以把“右倾”“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标签送给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同时伴随一些强制措施或暴力手段。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面这段引文之于“革命叙事”的意义。
井宗丞说:这是咋回事?阮天保说:我这里有军团长宋斌的命令,你看看。哦,你现在没办法看,那我给你念念:阮天保团长,鉴于井宗丞犯有严重的右倾主义罪行,命令你在他一到崇村,立即逮捕。井团长,你听清了吗?井宗丞说:这不可能,军团长为什么要逮捕我?阮天保说:命令上不是写着你犯有严重的右倾主义罪行吗?井宗丞说:右倾主义?什么是右倾主义?”[21]
事实上,井宗丞的遭遇可能还涉及到当时在各大根据地开展的“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22],这样的事情虽然在当时就被不断被纠正,但是直到1935年以后才被逐渐平息。需要提醒的是,这些事情与前述的史实大体在同一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发生、延续。同时,这段引文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与井宗丞死于非命有着直接关系。井宗丞的死亡是涡镇命运的转折点,它不仅造成了“革命叙事”的中断,而且导致了涡镇的毁灭。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无意用已经形成共识的重要史实来衡量虚构细节的精确性,之所以不厌其烦进行史实还原和背景介绍,是因为,我无法对在虚构中横冲直撞的大历史视而不见。按照贾平凹的设计,涡镇是“秦岭”的化身,汇聚着奇鸟异兽、奇人怪事,孕育着传奇发生的资源和可能性。但是,传奇的发生和发现需要前提,所以,日常秩序发生紊乱、封闭的时空被打破,奇异、怪诞、不可思议方能发生,并被记录、传唱。《山本》里提供这种条件和前提的是来自外部的大历史,且是异质于涡镇种种象征、隐喻意味的现代性的大历史,所以,涡镇被打开的那一刻,传奇的发生便有了中断甚至被改写的可能。
通过前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猜测出《山本》里主要故事大概发生于1927年前后至1935年前后。所以说,涡镇敞开之时,真实的历史时刻便降临了,它笼罩着秦岭成为叙事的边界和导向。于是,传奇在大历史的挤压中被形塑为革命的地方性经验,换而言之,因为大历史参与了叙事的建构,传奇的传唱被改写为革命的讲述。至少对于井宗丞的故事来说,历史横亘在传奇通往野史的大道上。然而,随着井宗丞猝不及防的死亡,革命叙事亦戛然而止。在情节层面,我们固然可以把人的死亡和城池的毁灭理解为故事走到了尽头。但是未竟的革命和被迫中断的叙事意味着什么?突然的中断会不会造成意义建构的瓦解和崩塌?这一切能否被理解为,在坚硬、沉重、血污的大历史面前,虚构力不从心、溃不成军?倘若言之成理,我想大概是因为面对革命的复杂性,贾平凹也只能欲说还休……
四
与井宗丞的故事并行的,还有弟弟井宗秀的故事。两兄弟的故事构成了涡镇故事的两种面相和趋向。他们的故事拥有共同的神秘起源:父亲被安葬在别人赠予的土地上后,他们的命运便发生了转折。这三分地是当初别人陪嫁的嫁妆,故称胭脂地,然而却是个风水宝地:
她听见赶龙脉的一个说:啊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的。[23]
所以,两兄弟的故事从一开始都是传奇即将诞生的态势,在随后的故事铺展中亦时不时闪现暗示胭脂地确实灵验的片段。前面的文字中,我们以哥哥的故事为例,讨论了传奇的中断与改写、历史对虚构的压迫和限制等问题。接下来,我们可以以弟弟的故事为例,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如果说贾平凹在井宗丞所主导的革命叙事上表现出了某种暧昧,那么他在井宗秀的故事上则表现较为明显的青睐和希冀。因为,相比之下,井宗秀的形象建构和故事铺展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建构性。所谓“复杂”,指的是井宗秀故事的多义性和形象的多层次。
从我们对1920年代末以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理解来看,井宗秀的故事像是军阀或新军阀的成长史。军阀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所谓“军阀”指的是:“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24]所谓“新军阀”,是相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旧军阀而言,指的是1928年“二次北伐”后,北洋军阀体系瓦解之后,依然盘踞各个地区分而治之的国民党各派系的军事政治集团。《山本》里的井宗秀的成长之路便是如此,他成为富商之后先是谋求当地土匪的庇护,后以官方的名义成立预备团、预备旅——实则是以乡党、血缘、亲属等个人关系作为联系纽带的私人武装[25],进而实现了对涡镇的全面掌控。事实上,熟悉陕西民国史的人,很容易判断出井宗秀的历史原型是统治陕北长达20年、时称“榆林王”的军阀井岳秀[26]。
尽管这样的故事及其涉及的历史现象在正统史观里通常是道德和制度缺陷的批判标靶。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意识中对乱世豪杰的英雄崇拜情结对此类政治形象的传奇化改写。所以,在《山本》中我们看到了井宗秀的另一面:修筑工事抵御外辱,改造旧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维持涡镇民事、治安秩序。这样的描绘难免引发我们关于乡土社会传统士绅形象的想象:“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性权威”[27]的结合。于是,军事强人、精明商人和士绅,这些侧面叠加出一个英明神武、励精图治、安民保境的地方自治者的形象。很难说,这样的形象和故事不是贾平凹微弱的理想主义光芒闪耀的结果。因为,绅权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权力和精神品格在民国已经急剧衰落,因为其所依附的王朝政治体制和文化道统早已分崩离析。所以,在革命、战争、现代性横扫一切的时代里,绅权很难有所作为。正如历史学家对1920年代以后中国绅权现象的实证分析那样:
与清末以前的传统文人绅士相比,民国时期的“新绅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是强制性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性权威。上述鄂西12位权势人物中,有的虽然也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抵御过外来匪患,或抵制过军阀官僚的苛索,或为地方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兴校办学之类的公益事业,但与其劣迹恶行相比,前者多为后者所淹没。少数公正士绅反被这些有劣迹的“土豪劣绅”从地方自治领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绅”遂成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28]
面对这样的情况,便是“虚构”行使特权的时刻。它唤醒了已经消逝的精神品格来抵消历史的斑斑劣迹,以挽歌的情怀来讲述一个或然的故事。有些时候,的确如此,对某些消逝的美好的执迷,其实带有指向未来的诉求。只是因为历史的断崖过于陡峭,所以微光常常无法抵达。
这项特权无疑属于“虚构”的政治文化功能。然而需要提醒是,面向历史的虚构,并不必然就是带有消解、抵抗的意味。如同诗性正义并不是虚构的天然属性,以诚相待也并非是所有历史书写的初衷。所以,历史和虚构同样作为有意图的叙事和有技巧的修辞,也有界限模糊、相互启发的时刻——历史从虚构那里学会如何用庄严的面相编织谎言,而虚构也会以谎言作为招牌重建一段历史。《山本》的《后记》里有一句话: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浆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还是虫子和苔藓。[29]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虫子的残肢和苔藓的石化看成石碑上变形的文字,也可能把模糊的文字当做虫子、苔藓的化石。这便是历史和虚构边界模糊的时刻。当依凭文字不足以抵抗真相的时候,我们书写的未必是我们的看到,也有可能是我们想看到的。
【注释】
[1]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3]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4]参见方岩:《<古炉>:“珍品”还是“赝品”》,《文学报.新批评》创刊号,2011年6月2日
[5]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6]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8]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9]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0]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1]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2]参见王云:《渭华起义》,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4]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章《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15]参见杨奎松:《革命(叁)·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五章第五节《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
[16] [美] 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页。
[17]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20]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章《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21]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2]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
[23]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25][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6]参见张紫垣:《井岳秀在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79年版(内部发行);县政协文史办:《井岳秀生平有关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蒲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蒲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发行)。
[27]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
[28]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
[29]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