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因风雪老 生命有爱终深情 ——长篇小说《风雪那年》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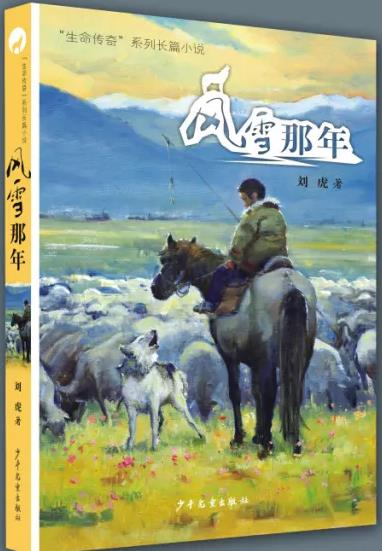
这本书最早的标题叫《遗孤》。为了给她取个更有意味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的温暖的名字,我和编辑还有很多朋友折腾了大半年。这在我和我的编辑来说,一定都是不多见的。
在我并不十分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曾经遇到过很多“遗孤”。这些遗孤中有人,也有动物。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个。
遗弃
一是我们单位一个职工犯罪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抛下孩子走了。几个原本聪明,学习很好的孩子在无依无靠中很快养成了不少坏习惯,包括为了吃饱肚子去偷窃。另两个是关于动物的。
我在祁连山中碰到过一个猎人。他给我讲,有一次他家的羊圈被狼袭击,愤怒的他把狼杀了,并和猎犬继续追踪到狼窝,却看到两只小狼崽像见到亲人一样跑向他们,他那正在哺乳期的,刚才还在狂吠的猎犬,居然就被毛茸茸的小狼崽征服了,现场给狼崽哺乳了。看着那两只天真活泼的失去母亲的小狼崽,猎人无奈,只得把他们接回家,当狗养了起来。因为政府不允许普通人家豢养狼这类野生动物,几年后,两只虽已长大但没有旷野生存能力的狼被送进了动物园。又过了几年,我在野外碰到了一桩奇特的事:林业部门的人正把几只外地的野狼送到祁连山中。原来,祁连山因狼的数量锐减,其他野生动物在缺少天敌后,非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因体质下降危及到种群安全。政府为防止发生连环性生态问题,只好花钱从外地买了些狼。
再有一个是关于狐狸的。那年,我在祁连山的小哈尔腾工作,租住在一个煤矿上。我们到达前,煤矿工人采煤时无意中炸毁了一个狐狸的洞穴。狐狸妈妈当场被炸死,留下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狐狸。那只小狐狸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妈妈已经不在了,被人用牛奶喂了没几天,就把煤矿工人当成了亲人,见人就会主动跑过来,爬到人身上,亲昵地用鼻子碰你;玩累了,就随便找个没有叠好的床,钻进被窝呼呼大睡。故事的结局貌似很简单,一段时间后,小狐狸就被当地的林业部门接走了。可以想象,如今,我要再想见到那只小狐狸,一定只能去动物园或马戏团了,而且一定是隔着铁笼或栏杆,肯定见不到那副天真活泼的面容了。
就在当年的工作中,我的脚,甚至我们的越野车,都无数次陷入老鼠洞里。那片原本丰饶的草原,多年来饱受鼠患威胁,遍地老鼠洞,植被退化、沙漠挺进、疾病横行。我们单位另一个项目组,就有人感染了鼠疫。这些恶果的原因之一就是老鼠的天敌狐狸等数量的下降。
冬天,我回到城市后,一直想就这些题材写部小说,但苦苦找不到起点。如果按我以前的写作习惯,可以轻松地把这处理成一个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我已经写了一些,驾轻就熟,但我觉得这几个故事以旧有思路写不出新意,我暂时将它们搁置了。
两年前,我回家过年,在院子里经常和一个多年不见的发小碰面,他却从不理睬我的招呼。我们初中时关系很好,不过后来我考学成功,他却在高中阶段就因一次义气犯罪进了少管所。出来后他先是被社会拒绝,找不到工作,只得和曾经的“狱友”混迹一处。后来家人也嫌弃他,他便从家里搬了出去。四十来岁的他依然单身,监狱倒是几进几出。我也是多少有点傲气的人,主动问候几次得不到回应,渐渐也就不搭理他了。
春节那天,我外出拜年返回时和他相遇,他脸上散发着红亮红亮的光,大老远就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两人擦肩而过时,我像平时那样把头微微一低,谁知,他却很突兀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几下,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口齿颠簸半晌,没有发出声来,随后,就松开我,踉踉跄跄地走了。我还没从刚刚的那场惊愕中回过神来,已经走远的他忽然回过身,远远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见我扭回头,又说了声“新年好”,就快速走开了。我把这事讲给另一个同学,他说,那有啥奇怪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平时要是和你打招呼,害怕你被别人说,怎么和这么个坏蛋打交道。我的心骤然一紧,不觉想起我们少年时代一起上下学,一起打闹,刚刚吵完架又一起游戏,约好到黑河抓鱼,共同扛着气枪到林子里打麻雀的美好时光……
无论是那几个父亲入狱母亲改嫁的孩子,还是成为孤儿的狼崽或小狐狸,他们的孤儿身份是那么具体,具体到有人给他们一口饭吃,或者哪怕把他们送进孤儿院、关进动物园和马戏团,身份带来的问题好像就得到了解决。
我的那个发小呢?他怕是比那些孤儿更孤独,因为几乎整个社会都对他关闭了,更准确地说,他是被社会遗弃了。
忽然,“遗弃”和“孤儿”这两个词跳进了我的脑海。
无论我的同学还是失去母亲的小狐狸和狼崽,假如这些生灵都遭到遗弃,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怕是永远都得不到解决了。
拯救
我意识到,这些故事完全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架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最终都可能沦为“孤儿”。亲人会因衰老、疾病或意外离开我们,谁都可能因某种自身或外因陷入孤单。既然如此,成为孤儿就不应是生活的终点,而应成为生活的新起点。现实生活中,我们与周围的世界彼此难离,无论人与人,人与动物,还是动物和动物。被遗弃者终会反身影响到遗弃者,拯救这些孤儿,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与其单纯突出遗孤这个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的概念,不如把主题隐藏在更宽泛的想象之中,让生活和岁月本身来回答这个问题。
小说即将交付印刷时,编辑有了新的思路,和我确定了标题——《风雪那年》。那年那场罕见的暴风雪是故事最核心的转折,风雪那年发生了什么?也在标题上给故事设置了悬念。
那个让康卓夫妇心痛欲碎的夜晚,他们的独子在新婚之夜遭发小枪击而亡;那个风雪之夜,康卓夫妇果断放下仇恨,将凶手无辜的年仅五岁的儿子贡保诺布送到医院,并最终收养了他;康卓夫妇的这一意外行为,也让曾经因唾弃凶手而迁怒凶手亲人的牧民们为当时的义气愤怒而羞愧;多年以后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洗心革面、在亲人盼望中出狱的那个人,临时决定连夜赶回家中,却恰好碰到儿子遭遇狼的袭击,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儿子。
人和狼在长期的对抗中,俄勒冈草原的狼数量骤降,兔子和老鼠猖獗,草原遭到破坏。结尾处,我特别设计了在那场血腥厮杀中彼此都遭到重创的人和狼,在硝烟散去后的偶遇中,长大后的贡保诺布故意破坏其岳父试图对狼实施复仇的子弹的轨迹,已不仅仅是放下了仇恨,而是张开了爱的怀抱。贡保诺布放下与狼几十年的“恩怨”,人和狼在遥望中达成了彼此的容纳和理解。
一场寒风,将仇恨扑灭;一场暴雪,见证了感天撼地的人间大爱;一段风雪中的艰辛历程,彰显人类在面对自身危机时的博大胸怀、超强智慧和敢于去爱的勇气。
文学艺术的目的是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铭记仇恨是为了避免新的伤害;增强爱的能力,无疑是使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有效方法。
岁月总是平凡驳杂而艰辛,经历并挺住了风雪侵袭的岁月才会因荡涤而愈发璀璨晶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标题的转换,不仅摆脱了用题目强化主题的老套路,也赋予作品更深的意味,突出了立意的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