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写作者都是“越轨者” ——散文写作三人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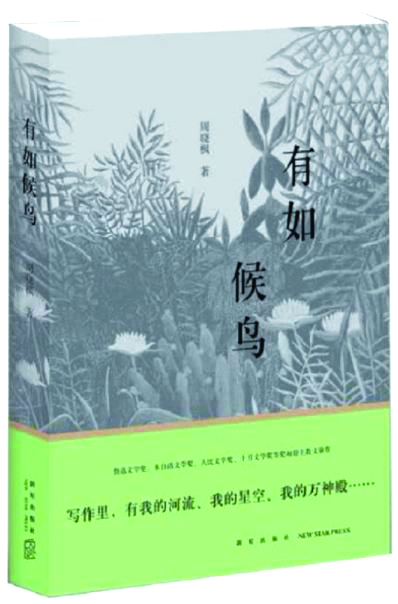

情感力量,让我们通过写作变得越来越宽广,而不是越来越狭隘和自私。写作者应该在有限的胸腔里容纳万千的生命,忘却自己,进入到万物里去感知,才能够有所谓的共情能力。
好的批评文章,不是看它写得如何波涛汹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看到“水落石出”。真正好的批评修辞是质朴锐利,卓有识见。
所谓真实也好、虚构也好、主观也好、客观也好,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异,因为我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全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还死死抱在那个学科细分以后的所谓对于散文的这种定律上面,这实际上就是散文的懒惰。
用散文去触碰更复杂的人生
张 莉:《山河袈裟》是2017年初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也是李修文沉寂10年之后的作品。《有如候鸟》是周晓枫的新作,获得了许多好评,其中《离歌》被视为转型之作。《众声独语》是我2017年出版的一部批评著作,副题是“70后一代的文学图谱”。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各自对修辞、对散文写作有了更多新认识。
周晓枫:我偏爱那种大金牙一样耀眼的句子,看书时习惯把很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句子用尺子划道,但《山河袈裟》,我摘出句子非常困难。如果划得出来,通常是一个情境或场面。李修文的文章是整体而混沌,具体而结实,静水深流又荡气回肠。他的文字有钝感和重量,饱满,讲究而不矫情,有教养而不卖弄,写的是东方的、中国的,有古风。在李修文的文字里,人民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或近或远的血缘,是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的亲人。我不知道他是否经历过游侠一样的生涯和体验,也许他看过繁华,也承受过困窘,一个人,从未丧失他的羞怯、怀疑、悲伤和敬畏,才能经历毁灭而重生。
李修文:我写《山河袈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报恩,我可能在报一场暴雪的恩、报一场大雨的恩、报一条走过的路的恩,更要报这10年里头我所遭遇到的这些人事的恩。美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存在于一个更宽广的美学谱系里才能呈现它的生命。对纯粹的“美”我一直抱有警惕,但也发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许许多多的时刻,一个人的美学如何贯注到他的生存当中,最终形成他的底气,形成一种独属于中国人而非他国人的底气,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所说的这种美学非常的微茫,而且在今天越来越微茫和不可琢磨,可是我觉得还是心有不甘。在今天,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美学,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姿态面目在时代生活里生长?到底在哪个人身上、在哪条河里静水深流?《山河袈裟》就是在写这个东西。
但是,你总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事物无动于衷,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周晓枫的《离歌》,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年代里,每个人所遭遇到的重大要害到底靠什么样的美学来呈现?《离歌》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好的散文可以泥沙俱下,也可以混沌未开,更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离歌》带给我很大的信心:她写的主人公既有生存,也有生存之难;既有内心,也有内心之难,一如我们身边多少上下翻腾却终日被欲望摧折的人。所以,《离歌》也在促使我,以后要用散文这种文体去触碰一些更为复杂的人物和处境。
张 莉:读《山河袈裟》,我不止一次想到新文学传统中“人的文学”,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初衷就是要和“引车卖浆者”在一起。《山河袈裟》再次实现了这样的理想。在《众声独语》里有一篇李修文的作家论,题目我化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李修文厚重、饱含情感能量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无穷的远方”,也能想到“无数的人们”。《离歌》是有关欲望与名利的作品,是失败者之歌,读来令人感喟不已。《离歌》之好,在于写得无限逼近我们时代真相,在于它提供给我们巨大的镜子,我们得以照见时代,也照见我们自身。这些作品让我想到,我们的修辞应该建立在真实情感之上,要和真实、和真相、和现实发生关系,否则,无论多么华美的修辞,都只是空谈罢了。对于写作者来讲,今天最锋利的修辞就是如何直面我们所在的时代和生活,如何抵达地、准确地表述你所感受到的一切。
读这两部散文集,我想到《世说新语》里的“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我想,真正能做好“修辞”的人,应该是有情人。“情感”是所有写作的发动机。对于批评家来讲,写评论也是交付情感的事情。只有“有情人”,才会和我们所在的生活和所在的人群发生关系,他的写作才可以真正构成一种美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修辞。
修辞要和内心保持一致
周晓枫:修辞锋利是双刃剑,可以更及物,更切中幽微,它同时也会伤及创作者自身。什么样的修辞是好的?我觉得首先是准确。修辞的准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让我们学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校正自己,否则,所有的技术会反过来伤及自身,修辞要和我们的内心保持一致性。
熟能生巧是肯定的,训练使你的表达提升;但写作者的内心不能生出“巧”来,你要永远抱着好奇、尊重甚至敬畏的心理面对陌生的经验和世界。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写未必是才华横溢,可能是更可怕的枯竭,是丧失了触感和判断力,用他熟练的技术活和常规化的俗套,用不提炼智慧的习惯来处理这个题材,他才会觉得无所不能。
李修文:我一开始写作是写小说,受了先锋文学的影响,总是叙事时将自己放置在情感原点上,但当我在生存中遭受了巨大触动之后,突然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还是不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写作者?不妨回头看看我们的名著:《红楼梦》里那种从繁华到孤寂,那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西游记》里,小说结束时虽大功告成,但身为人的生趣也不知所踪了,这种独属于中国式的感受,往往很难在西方文学传统里看得见。《红楼梦》和《西游记》描绘了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眼里和心里都存在的东西:深深的无力感。四大名著全都一开始极尽想象地构建了美,最后又眼睁睁地看着美丧失,这种无处不在的叹息与感伤在我看来特别迷人,但又莫可名状,在现代社会里难以准确地触摸和呈现。在今天,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情感该如何表达?弘一法师摇着一只小船,从此以后江海余生,这样一种情感我们该如何表达?所以我有一个认识:如果我将我个人的美学实践视作一个任务,那么,庄重地、而不是戏谑地对待情感这个课题是其中最艰难的部分。
张 莉:和李修文一样,我也是西方理论的爱好者。但是,学习了那么多理论之后,有一天我问自己,如何成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写作者?2017年我一直在重读本雅明,我一遍遍读他写的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卡夫卡,读他写的“讲故事的人”。为什么本雅明的作家论好看?因为他和他评论的作家发生了真正的情感,他爱他们,真正的欣赏他们。同时,他把评论写成了美文,因此,那些文字不再只是作家论那样简单,即使我们不了解这位作家,我们也会懂得他的表达。他的评论使我们认识到,好的批评家和好的作家之间是相互照亮、同生共长的关系。如何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文学批评的恰切方法,寻找最佳的散文式表达?我在寻找,我深信这样的寻找有意义。
从传统中寻找给养
周晓枫:以前有人问我,写作里什么最重要?我说是想象力。提问者的答案是情感。我当时觉得,情感是最基本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供阐释的,它也没有那么位居轴心的重要性。现在,我很尊重情感的力量。我们批评文学作品里没有情怀,其实首先是没有“情”,自然无法生长出那个“怀”。情是最简单的,像土壤、水源和空气一样,是基础条件,只要这些不受污染,没有给它加上很多防腐剂和化学农药,让它保持最天然、最干净、最本真的东西,从中就可以生长许多东西,可以滋养万物。情感力量,让我们通过写作变得越来越宽广,而不是越来越狭隘和自私。写作者应该在有限的胸腔里容纳万千的生命,应该像出色的口技演员一样,忘却自己,才能模仿他人,进入到万物里去感知,他才能够有所谓的共情能力。情感能力是这么重要的支撑。不管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还是自我怀疑,哪怕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动笔,只要情感足够真挚,就能保证你未来的复苏可能,以及拓展自己的可能。
李修文:《山河袈裟》写完之后,我发现我的语感发生了变化,突然就深深爱上了杜甫,爱上了《古诗十九首》。我把《古诗十九首》下载在自己的手机里,不断读,越读越觉得好:语感端庄、简朴、平易,一点也不大惊小怪,就仿佛所有的作者接受了所有的命运,对了,它还特别及物,字就是字,词就是词。很自然的,我希望自己写出杜甫那样的文字。你的语感、你的修辞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们是和你的生活比翼齐飞的。经常有人问我,你到底在写什么?我说我写得特别简单,就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就想:我能否写得再切实一点,少一点花团锦簇,多一些沉潜之气?说到底,修辞最终还是会影响见识,甚至,我们对修辞的检讨和反省会形成我们新的见识。朱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文人怎么做,讲了两个字,就是充实。“充”,说的是我们一定要去不断触碰个人生活的边界;“实”,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及物,去和身边遭逢发生最真实的联系。
张 莉:《山河袈裟》中,读者能感受到李修文与文化传统的接近,中国戏曲、古诗、古画的气韵内化在他的血液里了。比如说那篇广为流传的《长安陌上无穷树》,题目就代表着他的美学。“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这篇文字不仅使唐诗重新长在了我们的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情谊的源远流长。李修文一直在往回走,从中国文化传统里寻找给养,因此,他的散文美学远离了当下流行的散文套路。周晓枫的散文是另一种追求,她借用现代电影的表现手法,有意味地控制叙事节奏和故事切换,给人以阅读挑战。她在着意打破那种久已形成的散文写作秩序。
整体而言,他们都是有想法的写作者,在有意识地对中国散文文体进行拓展。我认为这种拓展非常重要。今天,散文已经是全民文体了,作为专业散文写作者,必然不能亦步亦趋跟随前辈书写,应该想到独辟新路。很多年前读到过鲁迅翻译有岛武郎的一句话,“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作为写作者,首先要“不怕”,若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体,就要有勇气先打破陈规。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好的写作者都是越轨者”的原因,好的写作,就是要从打破一些惯常的理解与认识开始。
时代的精神往往从散文中生长出来
周晓枫:张莉跟我探讨她的批评文章时,经常说:“你看这个词是不是用重了,这个词是不是用得夸张了,这个词是不是用得过分了?”很多时候,批评家给的秤杆容易高高的,好像不唱出那些色泽饱满度很高的褒义词就是不懂事。这导致我们的评论标准发生了可疑的动摇,好像切实的、及物的、更贴近作品的表扬都不解气了。在修辞火候上,坚持“宁欠一分、不过一分”,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助于反思。我们需要反思,我是否在用词上偏离了我要描述的对象?我是否在批评时更靠近了人际关系而偏离了学术道德?慎重,才是让我信任的批评。
张 莉:用哪个词来恰切地给这个作家定位一直是挑战。《众声独语》的副题是“70后一代的文学图谱”。10年前开始阅读这些作家作品,写下我的判断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作者,可参照的评价也并不多。用哪个词形容作家,我总是很困扰。用轻了,我觉得对不住这位作家的劳动;用重了呢,又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工作,不公平。作为写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到用词准确,但我深知这是极难的。我不断提醒自己,修辞是有限度和边界的,批评家一定要掌握修辞的分寸。
什么是好的批评修辞?我想,它不应该是“糖衣炮弹”,也不应该让人“雾里看花”。批评家把话说到什么份儿上,如何不浮夸、不贬低,都是批评修辞的组成部分,尤其要有识见,要有穿透力。作品是好是坏,批评家不能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好的批评文章,不是看它写得如何波涛汹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看到“水落石出”。老实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好的批评修辞是质朴锐利,卓有识见。
李修文:我脑子里没有这个“轨”的概念,这也是张莉的文章非常有魅力的一点,我读她写我的文章,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我自己,但我又会边看边点头称是,好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他用他的理解和阐释,和作家本人共同确立了自己。用张莉自己的话来说,这也就是“审美信任”。
对我来讲,写散文就是希望在第一时刻对我的遭遇给出反应,它应该先于虚构文体,快速地和这个时代水乳交融。我甚至觉得,如果散文这种文体一直还在路上,还在行走,那它就还存在着一切成长的可能性。不夸张地说,时代的要害、气场、风貌往往都是从散文里面率先生长出来的,那么多铁定的事物、那么多金科玉律,在今天都被颠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散文在今天还有没有别的生长可能?
周晓枫:散文跟小说的区别被经常讨论。灰姑娘的大姐,为了把脚塞进水晶鞋里,不惜锯断脚趾——我们是否要为了散文的常规尺度,而破坏作品的完整性?
读李修文的散文,里面有这么多的爱恨情愁,跌宕起伏的戏曲情境。有人因此判断,这不像散文。但这是否是读者自身的问题?当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在复印机下的,过得比较规范、拘谨、沉闷,我们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我们已经安全得不再冒险,享用多年奋斗带来的利息,我们可能就会被慢慢腐蚀下去,以为这就是标准的人生,不再相信人生的际遇和奇迹,怀疑别人那种剧烈起伏的人生纯属虚构。现实中,有人为了躲避从天而降的灾难,或不惜以血肉相搏来赢得希望,他们的世界可能就比我们更丰富、复杂、精彩,就不是我们这种中年化的平庸乏味。
“主客相契,时机相当”
李修文:我们过去那种从生活材料开始再到文本创作为止的这个创作过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散文因为它自由,因为它像匕首一样简便轻捷,所以可能会率先进行实验和变化,它也可能会在极大程度上混淆甚至改变过去的传统,所谓真实也好、虚构也好、主观也好、客观也好,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异,因为我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全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还死死抱在那个学科细分以后的所谓对于散文的这种定律上面,这实际上就是对散文的懒惰。
周晓枫:很长时间里我们阅读散文,更习惯是退休老干部的总结式文体。我想跟散文一起成长,不是把中心思想和结论交给大家,而是把我在过程中的犹疑、否定乃至相互矛盾的东西呈现出来,不习惯的读者,就会觉得小说化。的确,我们在小说里注重悬念设置,情节陡峭,有特写镜头和广角镜头的拉伸,包括节奏改变。而散文,好像就应该老实本分,不耍花招,克制又慈祥地交代底牌。假设散文有一个国家那么大的话,你不要把它缩小成一个城邦、街道、后院,然后就是种花、养鱼、看孩子……这种自我萎缩的过程,没有那么值得歌颂和捍卫。在散文长度增加以后,不可能是一个小品文式的豆腐块,而是要牵扯时态、节奏等很多问题。我们不要把过去的散文标本,看作散文的惟一存在形式。
张 莉:语言是修辞的一部分。用哪个词不用哪个词,代表了作家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讲,我很喜欢这三个书名,“山河袈裟”代表了一种广阔、一种际遇,一种孤独;“有如候鸟”有辽阔感、飞翔感,同时也意味着越轨。而之所以有“众声独语”这一书名,原因在于我以为“独语”在今天如此重要,它代表了一种文学态度。
此时此刻,对真正的散文家而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写作是否能对散文写作有推动,或者,我们将在哪个方面对今天的散文写作进行推动,这很难,也许我们做不到,但应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天读者对散文的期待很高。孙犁说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主客相契,时机相当”。散文遇到了新媒体时代,同时,它作为一种客体也遇到了许多好的写作者。非常期待更多的写作者赋予散文这一古老文体以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