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着火光而来》:感受烟雾形状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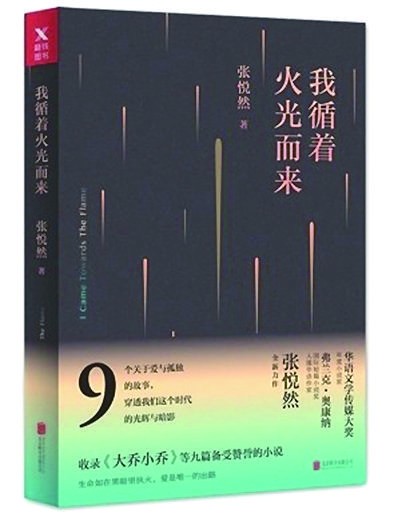
(《我循着火光而来》张悦然/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版)
张悦然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大多有留学经历,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热爱艺术或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比如《动物形状的烟火》中的林沛是一个青年画家,《湖》《嫁衣》中的主人公都有过留学经历,《沼泽》中的美惠是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的周沫是虽离婚但懂艺术的家庭主妇……但无一例外地,她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她们正陷入某种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之中,或孤独,或虚无,或背叛。
这群失败者,乍一看并不陌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当代文学期刊里遭遇各种各样的失败者。与张悦然同时代的诸多“80后”作家,郑小驴、孙频、甫跃辉、文珍、吕魁等的小说中,主人公也常常是陷入某种精神困境的失败者。他们的失败,首先来自切实的失败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内化为一种精神困境,评论家李敬泽如是说:“有这样一种气息,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来自生命内部,这是‘存在’的某种提醒,某种无法言喻的不安。”
相似的失败者叙事,首先与“80后”普遍的“日常体验”有关,不过,相似也带来同质化的风险,青年评论家项静曾批评道,“‘失败者之歌’式的写作最大的缺陷就是,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于一个简单基本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所有重要结局的原因几乎都不敢放得稍微远一点”。
但张悦然并没有陷入这样的窠臼之中。她以前写作的缺点,在这里成为优点。自出道以来,张悦然就是一个感受型写作者,《誓鸟》之前的作品,她热爱的是对某种极端的、偏执的情绪的沉溺性书写,读者很容易进入张悦然设置的情绪圈套中,但这种情绪往往缺乏现实和逻辑的根基,因此它常常华丽而空洞,精致但破碎。张悦然曾颇为准确地将其概括为“形容词文学”:“我们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大量形容词的出现,源于‘80 后’所处时代物欲的爆发。形容词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很主观,第二是风格可能会变得非常繁复、华丽。其实这是我们这代大多数人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抛弃和改变它。”
《誓鸟》之后,张悦然的一系列写作,可以明显看出张悦然在“改变它”。张悦然的感受型写作依旧没有变,对某种情绪的精准把握和书写,是她的一贯优点。你很难将它们归纳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她笔下故事的推动力与其说是来自某个具体而强烈的情节冲突和人物冲突,毋宁说它来自人物某个瞬间的感受和情绪。就像《嫁衣》中,绢之所以剪碎乔其纱的衣服是因为她在脑海中闪现了乔其纱与欧枫相恋的幻象;《沼泽》中,美惠的回忆触发点是初初那种重获爱情后幸福神采的脸……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其他失败者叙事,读者读到的是情节,但张悦然的小说,我们读到的是情绪。情绪是烟雾状的、迷离的、不可捉摸的,也因此是超越套路的。
诚如前文所言,主人公的情绪共同指向的是某种精神困境。这本小说集里主人公的精神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具体的“失败实感”,比如小说《家》,张悦然讲述的是主人公在现实中寻求支点,以拯救自己“失败”;而《大乔小乔》,则触及到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造成的两个姐妹的不同命运,“关于律法所决定的被诅咒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来自人类某种普遍的城市生存体验——嫉妒、孤独、虚无、沮丧,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母体,它更关注的是存在,是人类更本质的精神困境。因此我们可以在世界文学中找到它们的同类,就像《嫁衣》以姐妹之间的相爱相杀讲述人性的“嫉妒”,也许张悦然是在与菲茨杰拉德的《伯妮斯剪发》、克莱尔·吉根的《姐妹》对话,《嫁衣》是剪碎了姐妹的嫁衣,而后者则是剪掉了姐妹的头发。
评论家显然更希望张悦然往第一个面向书写,这方便评论者进行社会性的解析和提炼。但就短篇小说而言,我其实更偏爱张悦然那种感受型写作,这在当代短篇小说书写里太少见了。主人公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犹如困兽之斗,这种情绪迷离、湿漉漉的,你不知道主人公是否最终能够逃离,但就在某个片刻,你也被这种情绪感染,仿佛疲惫了一天瘫软在沙发上,你在他人的困境中洞穿自己,会感到一种释然的放松和审美上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