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我上到一年级就文革了。我的启蒙教育很早,我爸爸教我识字大概是四岁,都是自学,第一个最正规的学堂就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一个自由思考者的教育方式,他先发现你喜欢什么。他也让我拉过小提琴,但是后来觉得我不喜欢就不拉了。他发现我喜欢跳舞就带我去求老师,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也带我去求师。
他不太禁止我读书,比如什么书是儿童不宜,他不管,他觉得你自己会有鉴别能力的,而且他觉得越小接触大人认为不宜的东西越好,反而不觉得特别神秘和禁忌。
我的母亲比较严格,会禁止我看一些书,我就偷偷地看。我们家的《西厢记》是我爷爷买的,很大,线装的,这边是图这边是字,图很荤的,有时候搬出来看我爸爸也不管我,妈妈在家我就绝对不敢看。
上到文革就停学了,我爸爸被打倒以后我也不敢上学。学分数,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爸爸拍桌子打板凳地教,你怎么这么笨。后来我想到这些孩子被吓成那样,脑子“啪”一下就空白,断电了的感觉。我到了小数点就没学下去了。
我从12岁到军队的文工团,跳了8年舞蹈。
最早是1979开始写作。我们部队参加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我说我想去,就批准我去了。我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开始采访,采访伤员、从前线撤下来的小战士,有一天夜里就来了一千多个。采访他们以后就觉得,舞蹈这个东西太不能表达我自己了。就像我爸爸当年从画家转行成作家一样,我也大概是从那次转行成了一个写作的人。
当时我写了几首小诗,都发表了,因为很缺这样的文章,就给了我一个三等功。我又去了一次前线,就使我彻底转行了,转到创作组。
文工团派我去写报告文学之类。去的是云南,最远也就走到蒙自的野战医院包扎所。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一直在前线做战地记者,当时写了很多文章。在那段日子,我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我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严歌苓新作《芳华》是对军旅青春的深情回望。同名电影由冯小刚导演,黄轩主演
8年军队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我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8年我收到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函,让我去了解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去七个城市访问。这个访问让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年轻作家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相互之间的艺术的批评和读书气氛挺好的,我就特别希望到美国去留学。回到中国我就学英文。
我后来考上两个学校,一个是水牛城布法罗大学的英文系,还有一个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的介绍都是错的),因为给我全奖学金,所以我就去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在芝加哥,是一个私立的艺术学院,学校没有任何学科跟艺术有关,最好的是电影系,写作是其中的一个系,名字叫小说写作。
我1990年秋天开始读,一直读到1995年。我阅读英国文学原文的基础是很差的,学校要求我从基础开始学,我就去学莎士比亚了。
任何一个行当都有被训练的余地和空间。即使你是天生的小说家,被训练以后,可以写得更加省力,而且在学校你可以有纪律、系列地读大量文学作品,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去读,也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去读。
写作无非也就是让你多写,如果你是一个自由的状态,不去上学就很懒,写得少。在这个写作班里你必须写,写一个章节,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一个特写,每天不断地实践和体会写作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一边写一边阅读,会进步很快。

严歌苓近照 摄影:周鹏
我很满意,我到哪里都是边缘人
在美国留学时,一位女友打长途电话给我做媒,要为我介绍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女友公寓做饭时,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美国帅哥敲门而入,脖子上的吊牌写着“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他竟然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方言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我很幸运和劳伦斯成为夫妻,多年来,我们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我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这种存在感给予我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我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所以说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我这个人生活的经历就是一个吉卜赛,到处跑,我没办法写一个地方,我不是乡土文学作家。

我觉得我到哪里都是边缘人,在中国是个边缘人,在国外也是个边缘人,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什么他都不信以为真,不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什么东西他都会保留一个质疑的、侧目而视的姿态。这一点就让我在西方、东方、美国、亚洲、非洲、中国之间,永远都在比较的过程中,越比较越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敏感。对语言也是,中国人是这么说的,英语是这么说的,这个使我产生一次又一次对母语的新认识,也有对英语的认识。现在我逐渐地学德文,德文和英文也产生了对比。
哪里也不融入,都是边缘。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么好处?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的这种自由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位置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出版社出过我的小说《扶桑》之后,第二本我写了英文小说,就很顺理成章地出了。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有被退稿的经验。小说当时出了以后,被BBC每晚连播,叫“睡前一本书”。所以我又被他们约稿去写短篇,一直来约,我说我现在实在腾不出空来给你们写英文小说了,我说我还是要写中文小说。
最贴心最舒畅的就是和陈冲的合作
1995年2月,陈冲当选柏林影展评委,一天忽然她从柏林打来电话。她说:“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听上去有点像心血来潮,我问什么使她做了这么大的决定。她说经她评选的许多影片大同小异,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写照,没有任何使人感到心灵升华,甚至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她说:“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起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的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隔了两天,我收到传真,是陈冲改编电影《天浴》的初稿。她真的动手了。她的电话不断,一方面问我对这些改编的意见,一方面似乎在说服我,甚至她自己。她说:“都在追求“Avant Garde”(法语:前卫、先锋之意),什么病态啦,不近情理啦,全成了“Avant Garde”,我看病态太泛滥了,反而正常感情,健全的人性该是当前最“Avant Garde”的!
等陈冲从柏林回到旧金山,她已写完了《天浴》电影剧本的初稿。问她怎么可能在当评委的繁忙中抽出空来写剧本?!她说:“有激情啊!有时也因为时差睡不着觉。”
从那以后,陈冲基本上推辞了一切角色,包括一次和著名犹太裔导演兼演员伍迪?艾伦的合作。
《天浴》筹措资金、采景、选演员等一切事务,都由陈冲自己来做。有时她也苦笑,认为在自讨苦吃——自已制片和导片所受的辛苦是做演员的十倍。尤其在好莱坞当演员,条件非常贵族化,各部门分工很细,做演员就是拿了钱演戏,演了戏走人,不必负太大责任。但她也意识到,电影最终是导演的艺术,只有做导演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人格特色,以及思想、信念。只有做导演,才能改变好莱坞对中国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甚至偏见与误解。她近年来越来越难接受推荐到自己手上的亚洲女性角色,她认为这些白种人概念中的亚洲女性,简单得几乎成了符号。要改变这种模式,创造真正的中国人的故事和形象,她自己必须投身于主创,选择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方式(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来讲故事。
我觉得最贴心最舒畅的就是和陈冲的合作,虽然我们就是像过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个剧本,然后俩人一块做事情,贴心地谈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投资了怎么办等等,这种经历终生难忘。
中国编剧比好莱坞编剧待遇好
进入好莱坞的编剧协会,你必须有一个在美国公映的电影,还要有美国大的制片公司请你做编剧的经历,这样我们就进去了。我问陈冲这是好事吗?她说人家一辈子都想进还进不去呢,我说,那我就去吧。
加入了编剧协会,你就受协会保护,它会提前付费,福利上也有很多好处,包括当时有很高的医疗保险、养老金,再加上每年给寄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影片,可以看好多好的片子。编剧协会的成员有投票权,不过当时我在非洲,收到片子都第二年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投过票。
加入编剧协会是永久性的,成员的稿酬不能低过一个数,在美国来讲那个稿酬是很高的。他们每隔一年就要罢工,然后稿酬就提上去一点,罢工期间你不能给任何人编剧,否则就要被这个协会踢出来。
不过在好莱坞做事有时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后来我单独改了一个俄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没有拍成。我问,为什么你们没再提出修改意见,就不拍了呢?对方说,我们都是存着,什么时候想拍就拿出来,我们存放的本子只有50%投拍的。
这使我觉得很没劲,再来找我,我就不做了,我还不如用中文写,至少能看到成片。后来没多久陈凯歌来找我写《梅兰芳》。
美国的规矩是,最开始是制片介入,导演不介入。编剧协会有一个规定,签在合同里:修改不能超过两稿,不能无限制地让一个编剧改。制片第一稿看完了提出意见改完,找到合适的导演他就去拍,如果找不到那就会一直放在那里。导演介入以后,会再让你改,那就是另外一单合同。
都是先付费,但是后面还有一笔,一旦开拍,它要根据整个电影的预算,付给你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一般大制作是1%到2%,小制作是要高2%到3%,编剧能得到几十万美金。
只要有饭吃,我不会当编剧的。我现在尽量就写小说,我爱写小说,写小说在艺术上、时间上的控制都是特别自由的。我是酷爱自由的一个人。
编剧是我白天的工作,写小说反倒像业余的。实际上我现在写小说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编剧。我不去和评论界牵涉,或者是为得奖运作,谁也别想掐死我。编剧是比较纯粹的,你编得好就挣钱,拍不拍不是别人的事,但你写了就能挣钱,这是一个单纯的供需关系。我可以用这个工作来保持我做另外一个工作的独立性,就是说我不需要运作任何事情,可以清高地独立地做人。
中国的编剧若要成功,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在国内编剧圈,创作题材撞车很严重,中国的编剧和导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条路上。
但是中国编剧比好莱坞编剧强势多了,待遇是蛮好的,一般来说超过好莱坞的编剧。好莱坞当编剧,据我了解一般是八九万元(人民币)每集,现在可能十来万元,但在国内就远远不止了。我曾和张艺谋说,他花这个价钱可以请到很好的好莱坞编剧。在经济方面,我们编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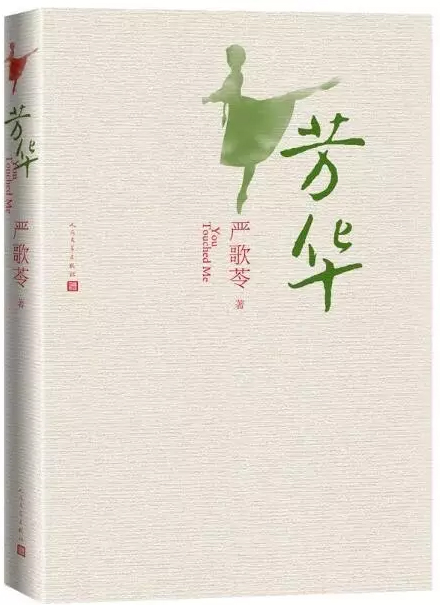
严歌苓新作《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