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军:《望春风》,芥子般大小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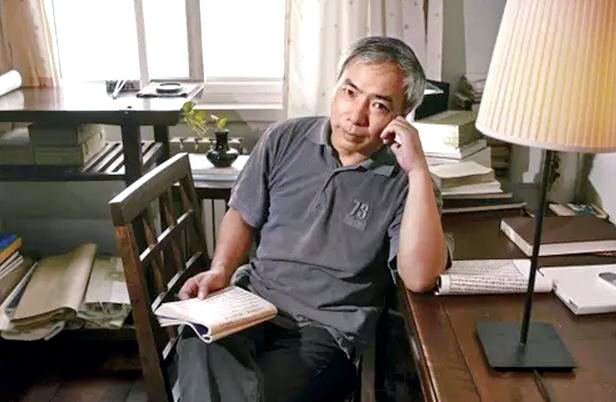

格非在其长篇创作中总是力图要在世事颓败之际为主人公寻找到像芥子那么小的一点点信念,有了这么一点信念,虽然不能“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但是,至少是可以开始做事了,所谓“立住脚跟”,不再像传统那样永远地发着“身似浮萍类蓬转”之感,而是在最低的限度内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时代的虚弱,这种探索异常艰难。但是这种努力,是真正地“直面现实”,是恰当地思考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也因此,我觉得格非的创作仍然保持着先锋的精神,而且超越了语言的层面。他能佳作频出,当属这种“先锋精神”的回报。
《望春风》上部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时候有两个引言:一个是刘禹锡的话:“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一个是蒙塔莱的诗:“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全书出版后,保留了后面这个引言,刘禹锡的话没有了,换成了《诗经》里的一句话:“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交换的这两句话都含有光景颓败的意味,但前者侧重客观描述,后者则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主观感受。
这一改动,透露了作者的写作“野心”,小说虽然几乎全景般地描绘了江南某片乡村的败落,但作者不想停留在生活图景的展示上,也不愿停留在历史流变的揭示上,他更想关注人物的精神,而且是具体的个人的精神,不仅细致入微地观察其变化,还想帮助他们找到“立足”之处,象征的说法就是让人物回到“故乡”,回到我们现在常说的“存在的家园”。对于生活在沉沦中的人们,这是最自然的渴望,但是因为积弊已久,这种渴望也是深隐不明的。作者探赜索隐,试图寻找一条回归的路径,只是“去圣日遥”,路径似乎比渴望更加隐晦。
结构:从“过去”到“现在”
小说分四章,而不是分上下部,但其实是有一个上下部结构的,更确切地说有个“上中下”的结构。前两章“父亲”和“德正”,是写“我”生活在故乡时的村庄里的生活的。后两章“余闻”和“春琴”是写“我”离开故乡后村庄里的生活以及“我”回到故乡时的生活,也兼写“我”在外面的生活。前两章在时间结构上指向“过去”,后两章显示“现在”。虽然“过去”和“现在”经常交叉出现,给人历时性生存有共时性之感,但是这两个时间线索还是比较明晰的。这个明晰性,从某种意义上也强调了人物在精神上回归的艰难。后面两章,隐含了一个“中下”结构,第三章为中,第四章为下。中部“余闻”,通过“我”的听说和看到,讲述了上部中出现的各色人物的命运结局。这一章关系到《望春风》作为长篇结构是否成立。第四章“春琴”则关系到小说主题是否成立,是旨归,是作者最意欲突破的地方。
上部即“父亲”和“德正”两章是作品的华彩乐章,描绘了一个古风犹存又充满生机的乡村世界。此时小说里的“我”正值童年,小说也就得以在童年视角下展开。这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最适宜的工具。因为这样的视角,作者一改清冷的语调,变得温情脉脉,而且使这一温情的回归变得比较自然。
在作者温情的笔下,这个叫“儒里赵”的乡村及其周边,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不仅有“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的乡绅如赵孟舒等,还存有各种“文化设施”,如寺庙、花园和大宅院。这里还是一个风俗醇厚、人情丰盈的地方。比较有意味的是这样一个所在并非存在于“民国”这一被理想化了的时代,而是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而且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像村里干部按照上级的指示批斗乡绅赵孟舒时,派专人照顾他,用专车(虽然只是独轮车)接送。
善恶交融的儒里赵
但是作者写的不是一个陶渊明式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善恶交融的世界。这是一个“恶在善中”的世界,善能承受恶,消融恶,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特点。“我”的父亲虽然懦弱,勾搭妇女,但是对“我”的爱却是作品中最动人心魄的情感。妓女出身的王曼卿与各种男人通奸,但在“我”的想象里,却是离家出走的母亲的化身。虽然有叔叔婶子苛吝待“我”,但同时也有队长一家无微不至对“我”的照顾。连乡绅赵梦舒的自杀都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让人警醒。而“我”的堂哥,这个将来会毁灭乡村的“资本”,此时的创业也显示着向上的气息。这两章刻画了大约50多个人物,其中有一半写得形神兼备,偶尔一笔的人物也留下鲜明的痕迹。当主人公“我”接到从未“谋面”的母亲的信离开村庄远赴南京时,儒里赵和它的风俗人物像一幅画被单独裱了起来,作者一笔一画描下的世界更加清晰生动,而作品众多未解的谜团像景深一样,给儒里赵这幅山水画增加了幽深感。
第三章其实最难写,也就是说主人公“我”在儒里赵之外的生活。他去的是南京这样算是很大的城市,作为上部的悬念,这是很能吸引人的。而且“母亲”此时已经是高干家属,那么“我”此去的生活应该是天翻地覆的另外一个模样,就像村里人想象的那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村里漂亮的姑娘雪兰迅速地嫁给了他,而在此之前,雪兰一家甚至因为有人为“我”提了一下亲而感到奇耻大辱。但是作者并没有描写“我”在南京的生活,更没有描写“我”可能作为高干子弟的生活。“我”出了儒里赵,转身去了与儒里赵并无根本区别的邗桥砖瓦厂。所以第三章还是儒里赵生活的延续,这个设置使作者重新回到熟悉的题材,是一个很机智的处理,可以在有限的篇幅里充分表达出主题的意蕴。
但是这个设置也留下一些遗憾。小说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要表现乡村的流变。而流变的历史感和沧桑感需要时间的暌隔,至少要有足够的“心理时间”。颓败来得太快,就像一块巨石轰然砸下,虽然动静很大,但是在阅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相对简单。
这一章的主题是乡村的溃败。相比上部,同样是善恶交融的一个世界,但已经是“善在恶中”。最典型的一个情节是梅芳帮助牛皋和龙英一家讨回公道后,牛皋他们举办庆祝酒席,竟然不请她,而且认为梅芳帮助他们是“挑头闹事”,人情之溃薄,人性之迷乱,到了令人心颤的地步。此时的儒里赵不仅房屋遭遇拆迁,作为生存之基的人情也遭遇了拆迁。善已经无法消融恶,而是被恶消融,相对于一二章清晰而生动的画面,这一章的画面比较黯然。
作为个体面对世界的超越性思考
如果到第三章结束,这真是作者回归传统的一个作品。从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沦落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不管从结构上还是从题旨上都让人想到《金瓶梅》或者《红楼梦》,而且在作品的质量分布上也颇为相似,《红楼梦》因为怀疑其后四十回不是原作者所写,后半部不如前半部似乎很自然。但是《金瓶梅》是相对完整的一部书,其后面的意蕴也相对单薄。更不用说《水浒传》,后面几乎是彻底的失败。
但是作者又写了第四章,让“我”和春琴的爱情单独成章。
我前面说这一章是作者的旨归,并不是说作品的意蕴都隐含在这一章里,而是说作者超越性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这里。早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就开始探索人作为个体面对世界时的状态,像小说里的曾山,即使还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但是已经意识到自我意识的缺乏,并努力试图在荒诞不经的世界面前建立一个自我,或者寻找到一个建立自我的途径。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主体意识觉醒在中国当代文学上最早的体现。同时期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写得异常生动,但已经走上“民间文学”的道路,放弃了《呼喊与细雨》中更个人化的探索。而格非的这一主题也没能在小说界引起反响,几乎仍然是他一个人在这个主题上不断地摸索。而且,到了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最后一部《春尽江南》,探索也没有得出理想的结果,而是收获了更深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却不同于《红楼梦》呈现的悲凉,不同于《金瓶梅》的凄冷。作者还是能在人物微弱的精神里呈现人性的光芒,在荒唐透顶的世界里于失败之际保持些许尊严。这是对西方文学的回应。
所以,虽然作者自己谈论《望春风》时说他希望达到《金瓶梅》的叙事高度,但是内在的精神更像是跟西方文学的对话,赵孟舒的自愿自杀、队长德正的三个宏愿、梅芳的坚持原则都显示了人物的某种自主性,不是被动地为命运所转。“我”是作品里一个看上去十分被动的人物,大多时候他只是一个观察者,一个事件的呈现者,几乎一直是逆来顺受地承受着生活。但是,当第四章中他和婶子春琴发生了爱情,当儒里赵的世界已经沦为废墟的时候,“我”这个人物的被动性本身却呈现了一种主动性的特点,就像表哥赵礼平说他的那样:“你这个人,一点没变,就是好摆个臭架子,人再穷,架子不散。”这就好像当所有的人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站着不动的人好像是很被动的,但是当人们发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往后溃败的时候,那个同样站着不动的人,却有了一种往前冲的态势。
爱作为一种信仰
“我”与婶子春琴的故事,让人想起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阿尔萨与费尔明娜·达萨晚年时期的爱情,虽然作者像马尔克斯一样都极尽各种手段把它写得很真实、很现实主义,但这仍然是一场罗曼蒂克的事,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爱的自身,而更多地来自于它的背景。在马尔克斯那里,这个背景是“晚年”,在格非这里是“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的男女之爱有了信仰的意味。因为文化的不同,马尔克斯极力张扬这种信仰,他可以自然地表达出生存的惟一有点意义的就是爱这样的主题。而格非却一边表现着这个信仰,一边又极力销蚀着信仰的痕迹,把这场爱写得异常琐碎、脆弱,有些滑稽,甚至不惜抹上一层乱伦的阴影。作者希望主人公穿过废墟到达存在的“家园”,希望这种爱能对抗生活的溃败,能给人提供心灵的慰藉,但是又不相信真有这样的爱,或者说不愿相信广阔的生活只有这点爱是有意义的。所以,小说结尾让主人公说了一段《圣经》式的话:“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或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作者想用这样有气势的句子来弥补仅为男女之情的爱的不足。当然作者也非常清醒,知道这段话有虚妄的成分,所以他描写主人公说这段话的情形是咽下一个对周遭环境的真实而残酷的判断,仅为安慰人而说的。
世事颓败之际的一点信念
我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为这篇读后感,起名“芥子般大小的信念”,并不是指这种能移动大山的信心,而是借用“芥子”的原意,表达一种非常小的信念。我觉得格非尤其是在其长篇创作中总是力图要在世事颓败之际为主人公寻找到像芥子那么小的一点点信念,有了这么一点信念,虽然不能“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但是,至少是可以开始做事了,所谓“立住脚跟”,不再像传统那样永远地发着“身似浮萍类蓬转”之感,而是在最低的限度内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时代的虚弱,这种探索异常艰难。再好的信念必须来自真实,真的需要作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且能否“拨灰见火”还要靠天意,但是这种努力,是真正地“直面现实”,是恰当地思考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也因此,我觉得格非的创作仍然保持着先锋的精神,而且超越了语言的层面。他能佳作频出,当属这种“先锋精神”的回报。
技术上,《望春风》的语言虽然相比作者的其他作品朴实许多,但不时出现的一些“雅语”跟主人公在小说中的身份有些脱节,因为小说的写实性增强,人物不再是寓言或象征中的一个意象,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语言和人物身份的契合变得更重要,当语言呈现的蕴藉意境非主人公能感受时,读者往往会有被阻隔在外面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