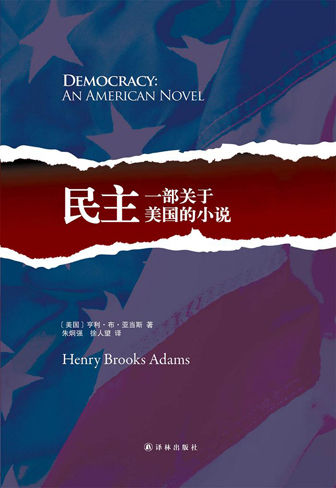中国作家网>> 小说 >> 作品展示 >> 正文
《民主: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23日13:56 来源:中国作家网 【美】亨利•布•亚当斯 译者:朱炯强 徐人望一
莱特富特·李太太决定到华盛顿去过冬,而其原因则被许多人认为荒唐乖悖。她身体壮实,却偏说那里的气候有益于健康;她在纽约宾朋如云,却突然想念寥寥几个波托马克河畔①[1]的熟人。仅仅在最亲密的知交面前,她才直言不讳,坦率地承认自己备受精神空虚、百无聊赖之苦。自从五年前丈夫去世之后,对于纽约的社交界,她已经胃口倒尽,趣味索然了。她对股票的价格漠不关心,对从事股票交易的人们毫无兴趣;她变得严肃了。这群乱七八糟的男男女女,单调乏味得与他们居住的褐色砖房一样,哪里值得一顾呢?她在心灰意懒中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她阅读了一些德文的哲学原著,却越读越沮丧,因为如此精深的文化居然使人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在与一位博览群书、持先验论观点的代理商谈论了一晚的赫伯特·斯宾塞②[2]之后,她也看不出把时间花在哲学上,是否会比早年同一位年轻风流的股票经纪人调情卖俏更加上算。其实,否定的证据是十分明显的。调情卖俏尚可以有所结果——事实上也真的导致了一桩婚姻;而哲学,除了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同样乏味的晚上,实在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先验论的哲学家们大多上了年纪,一般都有家室,白天忙于事务,一到晚上难免有点儿昏昏欲睡。然而,李太太尽量学以致用。她投身慈善事业,探访监狱,巡视医院,阅读贫民文学和犯罪作品,和那些作恶作孽的统计数纠缠在一起,以致心目中几乎看不到道德的影子。最后,她对这事感到十分厌恶,终于不能忍受了。看来,此路似乎也行不通。她断言自己已经失去责任感了,就她而论,纽约所有的贫民和罪犯,尽可以从今以后威风凛凛地起来造反,控制这块陆地上的每条铁路。她何必操这份心呢?这个城市关她什么事?在这个城市中,她找不到什么似乎需要拯救的东西。人多就有什么特别神圣的地方吗?一百万彼此相似的人,为什么就比一个人更有趣呢?对于这个拥有百万之众的巨大怪物,她能把什么思想灌注到它的心中,使之无愧于她的挚爱和敬重呢?宗教吗?成千上万的教会正在不遗余力地见缝插针,根本没有她创立新教、充当受神启示的先知的余地。雄心壮志?崇高的受人景仰的理想?追求任何高尚纯洁的目标的热情?她一听到这些词语就有气。难道她自己不正是被雄心壮志吞没的吗?而现在,她不正是因为找不到为之牺牲的目标而满心惆怅吗?
莱特富特·李太太如此痛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波士顿,痛恨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生活和特殊含义上的一切生活,其原因究竟是雄心壮志——真正的雄心壮志——抑或仅仅是烦躁不安呢?她想要什么呢?不是社会地位,因为论出身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体面的费城人。她父亲是著名的牧师,丈夫也同样无可指摘,是弗吉尼亚李氏宗族的一个支脉的后裔,这个支脉为了寻求财富而移居纽约,后来如愿以偿,或者说,找到了足以使这位年轻人在纽约安身立命的财产。在社会上,他的遗孀拥有她自己的无人争议的一席之地。她虽然不比左邻右舍颖悟多少,但人们一直认为她属于聪明的女人之列;她富有财产,至少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足以提供一个明智的女人享受美国城市生活的全部金钱;她有住宅和马车,衣着体面,饮食精美,使用的家具绝不落后于装璜艺术的最新水平。她游历过欧洲,在历时数年的几次访问之后,回国时一手抱着一帧青灰色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的葛鲁①[3]的典型作品,另一手提着几包波斯和叙利亚的地毯、刺绣,以及日本的瓷器和青铜艺术品。于是,她就宣告已经阅尽欧洲了,并且坦率地公开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她既不明白,也不怎么在乎究竟居住在美国好,还是居住在欧洲好;她对两者都没有强烈的挚爱;对辱骂两者也不抱反对态度。但是,她一定要猎取美国生活势必提供的一切,酸甜苦辣,兼收并蓄,点滴不遗;她决心非竭尽美国生活之所有不可,凡是能够从中获得的,她都要大量索取。“我知道,”她说,“美国出产石油和肉猪,我在轮船上见到过它们;我还听说它出产白银和黄金。任何女人都可以挑挑拣拣,择其所好。”
不过,前面说过,李太太最初的生活遭遇并不顺遂。她不久便公开宣称,纽约尽管可以作为石油和肉猪的象征,但生活的黄金,却是殊非她的眼睛能够从中发现的。虽然生活是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人、职业、目的和思想,但是所有这些在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就都突然停止了。它们找不到支撑它们的东西。她或亲或疏地认识十几个富翁,他们分别拥有从一百万到四千万不等的财产。可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钱财的呢?能够拿这些财产派什么与众不同的用途呢?要知道,花费的金钱多于足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的数量是愚蠢的,在同一条街上居住两幢房屋、赶着六匹马拉车行都是鄙俗的。然而,在留出一定的进款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之后,余下的部分怎么办呢?让它们存积起来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让李太太极其痛苦的是,这些剩余收入确实在日积月累,但既不能变更、也不能改善它们主人的品质。把它们花在慈善事业和公共设施上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但谈得上明智吗?李太太读过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有关贫民的报道,倾向于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是公众的义务,个人的巨额捐赠虽然有益,但也有害。退一步说吧,即使把它们用于慈善目的,除了助长那种令她痛苦不堪的人性,使之永继不衰而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一碰上这个问题,那些纽约的朋友无不求救于根深蒂固的陈腐之见,对此,她毫不顾忌地嗤之以鼻,说她尽管非常钦佩著名旅行家格列佛先生的天赋,但自从寡居以来,却始终不能接受他那大人国①[4]的信条:一个政冶家,如果能让原来只长一片青草叶子的地方长上两片,那就应该比所有的同行都更多地受到人类的敬重。倘若这位哲学家当时提出青草的质量应该经过改良,那她就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不过,”她说,“坦率地说,要是在现在只有一个纽约人的地方见到两个纽约人,我实在不能强装高兴;这一见解太荒唐了;一个半就够要我的命了。”
又如波士顿的朋友们。他们说她所需要的正是从事更高级的教育事业,她应该投入为大学和艺术学校而奋斗的神圣行列。李太太朝他们莞尔一笑。“你们知道吗?”她说,“我们纽约已经办了一所全国最阔气的大学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困难一直是即使花钱也雇不到学生。你们要我到街上去拦截孩子吗?如果那些异教徒不肯改邪归正,你们能够授权我用火刑柱和武力逼迫他们上学吗?纵使你们能够这样做,纵使我把五马路的小伙子统统赶进大学,迫使他们统统认真地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英国文学、伦理学以及德国哲学,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在波士顿是这样做的,现在坦白地告诉我,结果如何?大概你们那里有一个光华夺目的上流社会;大概培根街到处都是诗人、学者、哲学家、政治家;你们的晚会一定妙趣横生,你们的报纸一定才华横溢。可我们纽约人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我们不常进入你们的社交界,但一旦我们进入时,却发现你们的社交界并不见得比我们的优越多少。你们同其他人一样,都长到六英尺高就停止了,为什么没有人长成冠盖如云的大树啊?”
纽约社交界的一个平常之辈,虽然经常领受头领们的这种轻蔑态度,却以平庸之见盲目地反唇相讥。“这女人要干什么?”他说,“被图伊勒伊花园和马博罗宫①[5]搞昏头了吗?以为自己该当女皇还是怎么的?为什么不去宣讲女权运动,不去登台演戏啊?如果她不能像别人一样安守本分,何必仅仅因为自己不比我们高大就血口喷人呢?她想从尖酸刻薄的唇枪舌剑中得到什么啊?说到底,她懂得什么!”
李太太的确懂得很少。她贪婪地、不加选择地阅读各种书籍,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地生吞活剥,以至于拉斯金、泰恩与达尔文和斯图尔特·米尔,格斯泰夫·德劳兹与阿尔杰农·斯温伯恩②[6]联袂携手,从她的脑海中蹁跹而过。她甚至不怕困难,在本国文学上花过工夫,也许还是全纽约唯一了解一点儿本国历史的女性。当然,她未必能够按先后顺序背出历届总统的姓名,但毕竟知道美国宪法把政权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知道总统、议长和大法官都是重要人物,因而下意识地感到纳闷:他们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她想象中见到的浓荫大树?
既然如此,烦躁不安也罢,不守本分也罢,雄心勃勃也罢——随便你怎么叫吧——就可以解释了。这就是远洋轮船上,那种必须先到机舱去同技师谈谈,而后才能放心的乘客的心情。她想亲眼看看那些原始动力的作用,亲手摸摸那架巨大的社会机器,亲自衡量一番那动力的能量;她打定主意,一定要深入庞大的美国民主和政权系统的心脏,去探究它们的奥秘。她并不在乎这种刻意追求会把自己引向何方,因为,以她自己的话说,她至少已经耗尽了两条生命,在此过程中,简直已经坚强得麻木不仁了,因而绝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生命。“一个女人,”她说,“在失去了丈夫和一个婴儿后还能保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那就必然变得非常坚强或者非常软弱。现在,我是纯钢一块,你可以用杵锤冲击我的心脏,它一定会把杵锤弹回去。”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