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艺》2025年第5期|维摩:大象也受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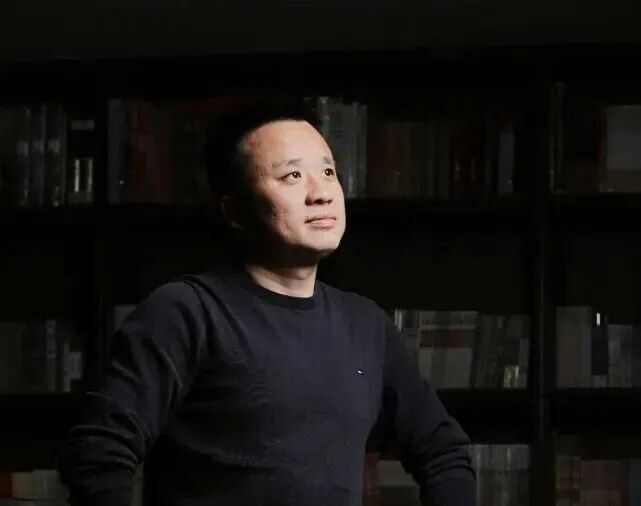
维摩,本名王小朋,作品散见于《天涯》《莽原》《清明》《广州文艺》《鸭绿江》《福建文学》《四川文学》《黄河文学》《红豆》《雪莲》《前卫文学》《小说月刊》等,出版短篇小说集《巨翅白鸟》。现居洛阳。
大象也受凉
文 | 维 摩
为送希达上学,佩瑜走了捷径。
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一路逆行,发出嗡嗡的颤动。过凯旋路时,红灯拦住了她。西风从不远处撞过来,带着浓烈的草料和粪便气味。希达在后座上揽着她的腰说,大象受凉了,正在拉肚子。佩瑜侧过脸,看见王城公园里高大的摩天轮凝立不动,西风便是从那里吹来,送上了大象拉肚子的消息。公园围墙外的法国梧桐正在凋零,城市的天际线正在变得空旷,凉风中的孩子更加细腻敏感。
希达长得随她爸,口味和腔调也像。幼儿园时,每天都闹着要顿河接送,哼哼唧唧的声音听得佩瑜脑子发麻。佩瑜和顿河吵架,她就在一边说风凉话,明里暗里帮着顿河。只是有一样:爱看大象,这一点让佩瑜坚信她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王城公园里动物很多,只看大象不看其他的人寥寥无几,如果不是血脉所系,三口之家里绝不会有如此高的比例。希达还在怀里时,每到生病哭闹哄不住,佩瑜就带着她去王城公园看大象。大象不动,她黑葡萄样的大眼睛也不动,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公园,公园里只有她和大象两个活物。看够了,希达就会长吁一口气。那么小的小人儿,好像是忽然悟透了什么了不起的难题,吁气吁得又长又深。听到吁气声,佩瑜就知道可以回家了。回家时的希达要么手舞足蹈,要么沉沉安睡,之后的几天就像电动小马达一样活力充沛。大象一天天老去,希达渐渐脱开了佩瑜的怀抱,扎起了马尾,穿起了裙子,唯一不变的还是每周去一趟公园,看一次大象,吁一口长气。
佩瑜很欣慰,他们家也总算有九都味儿了。网上说九都城有三大民俗:喝汤、看花、逛公园,她小时候一样都不喜欢。也难怪,她家住在河西大厂,街坊邻居都是东北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踢球、喝酒、吃大米。再远一点的街坊,住的是上海人和广州人,说话慢声细语,脸上总带着笑。除了在工厂做工,他们还会烧菜、理发、做生意。河西区的人依靠普通话交流,河东的几个区都操着粗糙硬邦的豫西腔。有点生活差异,也在所难免。
所谓河东河西,说的是七里河,学名涧河,《山海经》中也称其为谷水。一条河三四个名字,更能看出它资格老、辈分高。七里河从西边的峡城流过来,到九都市区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洛河。拐弯的部分,是南北走向,恰好成了河东河西的分界线。在东周,这条河紧贴着王城的西墙,是天然的护城河。城里人吃喝拉撒,也都指靠这条河。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洛水暴涨,夺入七里河河道。七里河也不是瓤茬,借着西来的洪水跟洛河干仗。两条河如同黄龙翻滚,绞缠在一起,让王城里的人寝食难安。周灵王看不下去,打算派人把这两条河都堵上。太子晋则认为堵不是办法,应该疏浚河道,使洪水流向大河,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周灵王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太子晋据理力争,争来争去就惹怒了灵王。周灵王一怒之下废了太子晋,将他贬为平民,逐出宫去。
你瞅瞅,古代人和现代人是一样的,天子家和老百姓家也没啥区别,解决家庭纠纷的办法都是如此简单粗暴。
希达自小脾气倔、心眼深,学习成绩忽上忽下。老师一个电话过来,总能让家里鸡飞狗跳。顿河下不去手,动手的往往是佩瑜。动手多了,娘俩也就结下了仇。小时候的希达只会躲在房间里哭,大一点就学会摔门而去。等夫妻俩消了气,头件事就是急慌慌出门去找孩子。顿河总是不得要领,佩瑜却往往能在王城公园的大象池边找到女儿。
苍茫暮色中,宽松的白色卫衣和粉色的荧光鞋子无端放大了孤独的气氛。看着孩子瘦削的背影,佩瑜就想起自己第一次来王城公园看大象的那个傍晚。
佩瑜十四岁时第一次走进王城公园,走的不是正门。那时候公园还是自筹自支单位,全年无休,收门票,一张两元,收的钱还不够狼熊虎豹的口粮。前面说了,河西与王城隔着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据说是建于1985年。河西这边的桥头立着一个双檐六角的亭子,名字叫“谷水亭”。六根柱子上镌刻了三副对联,佩瑜只依稀看懂一对:稻麦千重谷粮丰稔;烟岚一抹水木清华。王城那边的桥头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启功题写的“中州桥”三个朱红大字。巨石旁边的围栏与公园相连,把行人和车辆都阻隔在了公园外面。佩瑜出门时,兜里揣了两块钱,但是看同学们都没有买票的意思,只能随着他们往谷水亭桥下的河滩走。他们一路走过堤岸的缓坡,从缺口跳进河滩。那里有五六块菜地,搭架子的是黄瓜和西红柿,闪着水珠的是玻璃生菜。天气正热,佩瑜的嘴唇很干。越是如此,她就越要离那些诱人的蔬菜远一些。她小心地从田埂上绕过,跟着同学们走向远处的河滩。河滩长满茂盛的野草,野草里掩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和粪便,温热咸腥的河水在不远处流淌。草丛里只有一条通向桥头的小路,隐约露出黄土的痕迹。
佩瑜走在队伍的末端,一边走一边抱怨。她后悔不应该穿裙子出门,野草扎得小腿又疼又痒。等走到桥洞边,同学们已经踩着石块碎砖爬进了桥洞。她跟了进去,被高大空旷的桥洞吓了一跳。过堂风吹来,肌肤上游走的凉意让她忘记了难堪。他们从最大的桥洞一路上行,走进最小的桥洞,一架锈迹斑斑的梯子等在那里。
路熟的男同学早已从桥洞壁上的铁梯攀爬上去,向彼岸前行。佩瑜这才发现,原来这座水泥桥的下面还挂着一架小小的钢架桥,锈迹斑斑的梯子便通向那个钢架桥。钢架桥顶部是排列整齐的电缆,站在钢架桥上,任何一处电路维修都变得触手可及。只是钢架桥与大桥之间距离很近,即便是未成年人,也得弯着腰才能从小桥里依次走过去。走过小桥,就穿过了七里河,走进了王城公园的河滩里。这里的草修剪得很整齐,穿过一片并不茂密的竹林,从青石台阶向上走,不远处就是荷花池和公园管理处。人要分散开走,免得惹眼。男同学已经反复交代过,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大胆地从管理处门前过。管理处里都是懒汉,只管动物不管人,没人主动找事。即便有人拦的话,就说是刚才从公园里走过来的,迷了路,还得回公园里去。一般情况下,都能蒙混过关。
偏偏到了佩瑜这里,被拦住了。
事也凑巧。别人路过管理处,都没有任何动静,等佩瑜走到门前时,恰好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来,堪堪与她走了个对脸。佩瑜一紧张,就迈不动步子,头也不由自主地往下垂。两人见状,就拦下了她。
有票没?
我是刚才从公园里走过来的,迷了路,还得回公园里去。
佩瑜看着两人臂上的红箍,感觉自己的双颊也跟红箍一样红了。她的声音像是被抽去了骨头,软塌塌地没了力气。
看一下你的票。
丢……丢在进门的垃圾桶里了。
佩瑜说着,手却在裙兜里紧紧捏住了那两块钱。有那么一瞬间,她想把那两块钱扯出来,补上一张票,也就心安理得了。可她抬头又看见远处青石阙门后的同学们,他们探头探脑地望着她,似乎她说错一句话就会把他们全牵进来。她就这样僵着,时间突然就慢了下来,蝉鸣和蛙声都变得漫长而压抑。佩瑜在蛙声和蝉鸣里渐渐坚定了决心,她不再害怕,即使自己被带走,被关进管理处的小黑屋,她也不会供出同学们,更不会说出钢架桥的秘密。她这样想着,一种悲壮的崇高感笼罩了她,就像是连环画里看到的英雄人物面对生死抉择时一样。
这时候对面戴执勤红箍的中年女人扯了扯男人的袖子。你吓到这孩子了,她说。说完转过头来,对佩瑜说,去吧,上面就是动物园,以后记得买票。
这话并没有让佩瑜放下心头的重负,虽然她用最快的脚步跑上了台阶,但整个下午她都开心不起来。直到走向大象池的那一刻,她才忘掉了这一切。
那是一头年轻的大象。此前佩瑜只是在课本和电影里见过大象,她知道大象很大,却不知道可以大到这种程度。这样的庞然大物,竟然那么温和。孩子们朝他丢石子,它也毫不气恼,照样对着草料细嚼慢咽。蚊虫们绕着它飞行,寻找发动攻击的机会,它也只是摇摇尾巴或者扇扇耳朵,稍作驱赶。看到慢吞吞的大象,佩瑜心里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说不清道不明。直到后来的某一次,她在象池前灵光一闪,终于明白了大象的反面是什么。原来她一直没法释怀的,就是那个反面。她的父亲,那个始终怀着一团烈火的中年男人实在是太差劲了。生活里的任何琐事,都能成为他愤怒的根源。一杯太热的水、一块捉不到的肥皂,或者是一杯劣质白酒,都足以让他摔碎花瓶、砸坏桌子、踹透木门。所以当母亲决定离婚时,佩瑜毫不犹豫地和她站在了一起。这样的决定是惨烈的,母女俩的家庭收入迅速陷入窘迫,母亲不得不延长自己缝纫店的营业时间,直到深夜。
此时此刻,象池边的佩瑜突然想到,如果父亲有大象一半的好脾气,那该多好。
这时一个男孩子走到佩瑜旁边,学她的样子趴在围栏上。他的眼睛盯着大象,口气却像是在跟佩瑜讲话。他说,那是一只亚洲象,亚洲象比非洲象体型小很多,即便如此它也没有天敌。亚洲象从侧面看起来像个驼背的老头儿,非洲象看起来像精神小伙儿,可惜非洲象来回都需要漂洋过海。你知道吗,三千年前,咱们这里曾经有过许多亚洲象。在商朝,人们不仅捕象,还曾组建过一支训练有素的“大象军队”,借助大象的力量肆虐八方。周武王伐商时,便曾经与商王的“象军”展开过激烈交锋。你看,我们这个省简称“豫”,右边不就是一头大象吗?
男孩不是佩瑜的同学,身上有着与河西大厂不一样的气息,他属于河东的王城,或者更东边的老城。佩瑜看着他专注的样子,目光变得如羽毛般柔软。晚风吹起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是呆呆地看着大象,直到夜幕降临,工作人员来驱赶他们。
佩瑜回去有些晚,妈妈也没数落她。缝纫店里活儿很多,她顾不上,只是问佩瑜吃饭没有。缝纫店是家里房子改的,前厅做活儿,后面吃饭睡觉。佩瑜在堆积如山的衣服和布料之间站了一会儿,想跟母亲聊聊大象,但看到她在灯影里飘来飘去的身子,终究没有开口。
从那时起,佩瑜总是周末到王城公园去看大象,也总会在大象池边遇到那个爱说话的男孩。两人照例聊天、沉默、看大象。只是从那以后,佩瑜就再没有走过河滩,没有走过钢架小桥,而是大大方方地花两块钱买门票了。对于没有挣钱的孩子来说,每周两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她戒掉了一切零食,忘记了雪糕的味道,只为保证能拿出来那一张门票钱。
少年手中的时间,如同握不住的流沙。低头去看时,往往已来不及说再见。一连三个星期男孩没有出现,佩瑜忍不住打电话到他的同学那里,才知道他已经考上了九都市一高,全寄宿,学业很忙。佩瑜恍然,这才知道技校和普高的不同。她仍然可以挥霍时光,但他不行。她的目标是混口饭吃,而他的目标则是名牌大学。
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过去的就过去吧。佩瑜在看大象的日子里浑浑噩噩地长成了大姑娘,终于有一天自己也忙得顾不上看大象了。顿河找上她那会儿,她已经三十出头,正是市场价值暴跌的年纪。她在移动营业厅卖一个月诺基亚,还比不上顿河一台手术来的钱多。她不知道顿河有没有报恩的那层动机,但他的真诚还是打动了她。
算起来,顿河要比佩瑜小五岁。小时候的顿河挨了打,血淋淋地跑到北山陵园外的草窠子里怄气,怄着怄着就睡着了。佩瑜和母亲去陵园烧纸,就把顿河捡回了家。顿河在佩瑜家住了两天,佩瑜妈做的好饭好菜都紧着他先吃,把佩瑜气得够呛。直到第三天,顿河妈拎着点心找上门来,才把他带走。临走前,佩瑜妈翻出自家的白铝饭盒,把上午做好的韭菜盒子装了满满一盒,让顿河带上。顿河也是心大,嘴里连一个谢字都没有,跨上自行车后座,转眼就消失了十八年。
顿河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还捏着那只久违的白铝饭盒。佩瑜接过来,手感冰凉,不像空的,打开一看,里面并排躺着两支娃娃头雪糕。这小子,别看不说话,心还蛮细的。小时候娃娃头太贵,佩瑜说过,将来挣钱了,一定要逮住娃娃头吃个够。也就是一句玩笑,他就记了这么多年。
正是牡丹花开的时候,王城公园自然是首选的看花之地。顿河带着佩瑜挤在人群里,说是去看那朵稀世的“青龙卧墨”,拐来拐去还是拐到了象池。佩瑜本来想跟顿河聊聊大象,看他一脸无趣的样子,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其让他来看大象,不如让他去看猴山。这么大的人了,一点儿也不稳重。佩瑜妈说,别管那么多了,你这年纪,等不起了。佩瑜还是犹豫,犹豫了几天就听说她爸跟顿河借钱的事。脑瓜子嗡的一下,火气就撞上了心口。
佩瑜带着火气闯进铜加工厂的男工宿舍,把来来往往的青工们吓了一跳。正是炎夏,男人们都是三寸裤衩子遮身,上光膀子,下露大腿,脚趾头里夹着蓝色的人字拖。她急火火地冲进来,青工们无处躲避,场面一度非常混乱。佩瑜面色铁青,紧走几步,一脚踢开她爸的房门。她爸正躺在床上哼唧,声音少气没力,说是刚刚做完接骨手术,住院钱不够,只好先回来养着,等养好了再回去拆钢钉。佩瑜上前捏了一下,他嗷嗷直叫,两眼憋得通红,不像是说瞎话的样子。佩瑜没再盘问,扔了五百块钱在他身上。那是佩瑜妈交代的,还让她转告父亲少喝点,年纪大了骨头脆,经不起摔。佩瑜没传话,气哼哼出了宿舍,没几天就嫁给了顿河。
嫁顿河以前,佩瑜问她爸到底借了多少钱。顿河担心她着急上火,愣是一个字没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聘礼微薄,婚礼简陋,婚后租了一段儿风动工具厂的一居室老房子,佩瑜自然心里明白,只是嘴上不说。等缓过劲儿来,家里条件越来越好,两人更不愿提起这段往事了。顿河忙于挣钱,佩瑜一向心大,日子过得很是消停。直到为了希达上学,俩人之间才爆发了第一次争吵。顿河想就近入学,佩瑜要送孩子进名校。顿河觉得小孩子的童年,还是轻松一点好。佩瑜瞪了眼,轻松?考不上大学你轻松不轻松?
顿河脑子一热,回了一句,你没考上大学,不是一样挺好嘛。
佩瑜技校毕业,顿河倒是上过名牌医科大学。学历悬殊,本来谁也没当回事,偏偏顿河这么一说,佩瑜就认为是顿河看不起她。你算是把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了,你压根就瞧不起我。佩瑜当下红了脸,敲桌子打凳子,大吵一架,把希达吓得哇哇直哭。从那以后,俩人隔三岔五就吵架,原因无非是孩子。希达在吵闹声中一天天长大,哭得少了,沉默多了,有时候一个人能在窗户前待很久。好在她现在零花钱宽裕,而王城公园又免掉了市民的门票,所以一有时间,她就往大象跟前跑。回家时,情绪就会好很多。
这一次有点糟糕。
已经到了小升初的节骨眼上,希达还是没心没肺的样子。佩瑜问顿河有什么打算,顿河学聪明了,沉默不语,等着佩瑜发话。佩瑜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喝了一口茶水,扳着指头细数九都市几家名牌初中的优劣。末了,圈定二外和地矿两家,都是要择优录取,佩瑜让顿河想想办法,找门路安排女儿进去。这闺女考试不行,也没啥加分特长,你这当爹的得找人,自己孩子的事,上上心。顿河说,都是全寄宿,女儿还小,能不能等到高中再说。佩瑜眉毛一挑,起了高腔,高中?高中就晚了。
没等佩瑜发起火来,就听得客厅里“啪嗒”一声轻响,希达摔门而去。俩人没吵起来,愣怔了一会儿,又说了几句话交换意见。无非是顿河抓紧找门路,佩瑜不再因为女儿吵闹之类的。说完,俩人分头出门去找孩子。不多时,顿河接到佩瑜的电话,说是孩子已经找到了,她们稍晚一会儿回家。顿河有点诧异,既然已经找到了,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想到这儿他就收起手机,掉过方向盘往王城公园去。到北门一看,动物园已经下班,大门紧闭。
去看老头子,是希达提出来的。在佩瑜的记忆里,这个当爷爷的跟希达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也就是每年过年时,应景上个门,领一下老头儿的压岁钱。老头儿养老金不多,但是对孙女足够大方。希达也不知怎的,跟老头特能说话,上到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没几句正经的。每次被佩瑜催得不耐烦了,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佩瑜跟她妈也聊起来这事儿。她妈提醒她,你忘了,有一回你子宫肌瘤手术,住了半个多月的院,恰好顿河出差,我陪着,希达就放在老头子那里。怕是那个时候,隔代亲就续上了。
佩瑜恍然。
佩瑜和希达敲开老头子的门,他干枯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一半是意外,一半是开心。房子很小,还是在顿河的资助下买的。顿河瞒着佩瑜,但佩瑜早就弄清了来龙去脉,只是不说。房子里陈设简单,电视上正在播亚洲杯,中国队刚失一球。桌子上摊着一小堆花生,九都大曲剩了多半瓶,另外一部分在玻璃杯里。老头子忐忑不安地看了一眼佩瑜,看她没有发火的意思,就大着胆子拉希达坐到沙发上,把电视调成纪录片频道,又把遥控器塞在希达手里。这几天云南野象群穿村过镇,一路向北,吸引了太多流量。纪录片频道播放了无人机全程跟拍的镜头,都在猜测象群最终要去向何方。希达的确很关注象群的消息,但她接过遥控器来,却又换回了亚洲杯直播。场面上,中国队再失一球。老头子眉毛抖了抖,瘪了瘪嘴,终究还是忍住了脏话。
一老一少在沙发上看球,佩瑜就脱下外套,去翻弄冰箱。冰箱门关上后,厨房里的灯亮了,油烟机响了起来。中国队防守反击了一会儿,再次被对方压制。佩瑜从厨房走到客厅,手里端着一盘大葱炒鸡蛋,一盘韭菜炒千张。她把两盘菜往老头子面前一推,又把九都大曲给他满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倒完酒,她就坐在了父亲的另一侧。希达躺在爷爷怀里,搓了两枚花生递给他。那一会儿,老头子就忘掉了亚洲杯,忘掉了中国队,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了一张沙发。
得知大象拉肚子那天下午,佩瑜早早就到学校去接希达。去之前她给班主任请了假,希达六年来第一次没有上延时课程。老师有点不高兴,说这么紧要的时刻,希达又不是不用发愁的优等生,原本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学业上才是,怎么还要请假。佩瑜歉疚地说了几句好话,又编造了请假的借口,这才搪塞过去。
感到意外的是希达,老师告诉她可以离校时,她还在对着课本发呆。老师敲了敲课桌,说你妈妈在门口等你。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就火速起身,收拾书包走出学校。脚步有些快,粉色的鞋带开了她也不在意。偌大的家长等待区,只有佩瑜和电动车等在那里。希达系好鞋带,跨上后座,佩瑜就拧动了右手的电门。电动车没有朝家驶去,而是驶向了中州桥另一端的谷水亭。
稻麦千重谷粮丰稔;烟岚一抹水木清华。佩瑜把车停在谷水亭的楹联边,看了看斑驳的木柱。她本来想给希达讲一讲对联的意思,又觉得自己讲不清楚,只好作罢。她穿过马路,顺着另一边老旧房屋外的小路,走下缓坡。希达背着书包,一声不响地在她身后跟着。时间过去太久,很多地方都变了样。这让佩瑜的路线变得非常复杂,但她依旧找到了堤坝的缺口,从那里跳进了河滩。荒草已经变成黄色,被冷风梳理后趴在了地面上,踩上去犹如深毯。城市里不再有菜地,河道里秋水枯瘦。小路已经湮没,佩瑜凭记忆朝着桥洞的方向走。桥面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没有一个注意到她。
佩瑜踏着石块走进桥洞,然后转身向女儿伸出手,把她拉了上来。桥洞里冷风穿堂,她怜惜地帮希达拉上了校服拉链。做完这些她就继续上行,一直走到最小的桥洞里。
希达跟了上来,看见那一架锈迹斑斑的铁梯。这架神秘的梯子让她兴奋异常,双颊发红。
佩瑜笑了起来,她指着梯子说,走,我们一起去看大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