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回声】第六期 |“春羽”:在冒险与野心中唤醒青春的能量
今年3月14日起,中国作家网联合《青年文学》杂志社、《文艺报》“新力量”专刊、《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举办“‘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征文。启事发布以来,受到广大青年写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响应,收到投稿近900篇,其中通过初审并在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开放展示的500余篇,最终遴选出38位获奖者。
就像“春羽”计划的主题海报与命名所揭示的:一片新绿中,新生的羽翼衔来远方的花。我们期待从此次征文中发掘出新的写作力量、新的艺术视野、新的文学表达、新的审美风尚。广袤的土地,从不缺少新生,满怀期待的同时,当我们困窘于新意难寻,应当反省的,或许还有我们自己是否带了老旧的眼镜。
因此,“春羽”落幕后,我们需要一次回望、一段回想和一些回声,站在“发生”的时间点外,去看看这些细嫩的羽翼,有着如何的流光溢彩。本期话题我们邀请了高校师者戴瑶琴,从创意写作的角度观察高校写作的共性问题,更进一步讨论什么是“真”与“新”;征文终评审李晓晨与初评审陈丹玲从审稿人的角度更加细致地对文本进行了剖析,使我们得以由此视角审视除获奖作品以外的、更丰富广阔的文本;作为征文统筹,中国作家网编辑杜佳经历了从策划到落地,从审稿到与作者“面对面”的全过程,以回望为一个切片,剖白我们对原创写作的思考和更多期待;我们还邀请到两位获奖作者代表胡旸旸、思铸航,将创作感悟倾吐一二。
我们力图站在整体的高度,尽可能丰富这组“回声”,期待通过它们的交相辉映,还原这片园地最初的新意。
——栏目主持:邓洁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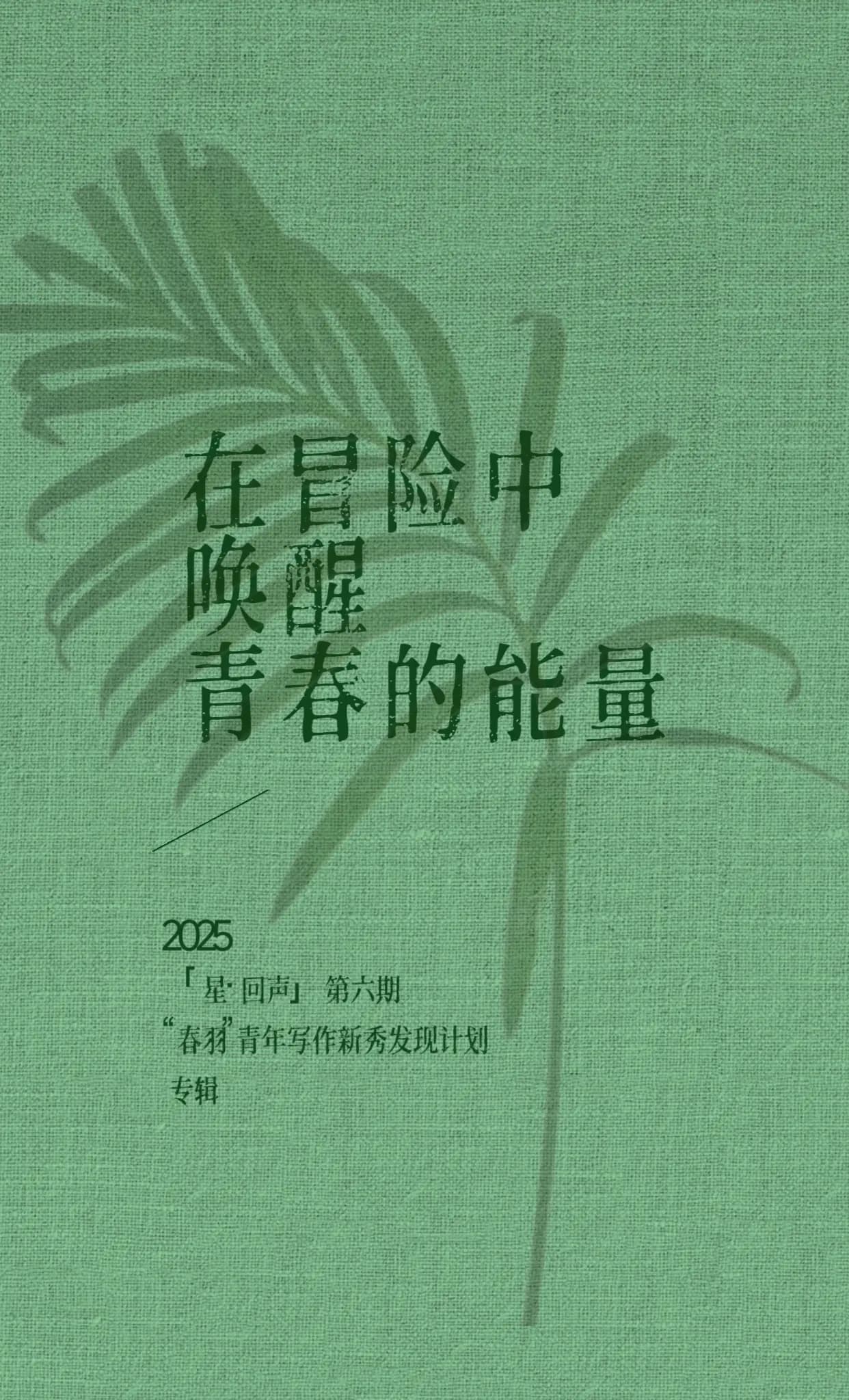
朝气与暮气
——回顾“春羽”计划兼论高校创意写作
戴瑶琴
“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进入高校创意写作文学现场,跟随当下青年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自我发展的探究,期待获悉“围绕真实生活”和“时代重大课题”的“新感受、新经验、新观念、新需求”。因而,征文虽没有设定具体主题,但强调对“真”和“新”的重视,以及对“多元”和“复杂”的接纳。
500余篇作品在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发布,文本展示了青年创作者良好的文学语感,也呈现出一定艺术设计,同时提示了目前高校创写存在的某些共性问题,如切入视角的新鲜感不强且辨识度不高,个人/群体的独特性感受十分稀见;如情节四平八稳,过于规整的人物代际序列与事物演进线索。因此,尽管颇用力地讲着“故事”,但作品还缺乏一些时代感和现实性的有趣、有效、有机结合。
从构思上看,参赛作品里立足回望维度的小说占比较大,作品主要关涉乡土/城市两大题材,意象描写、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的还原度和细腻度最高,视角或方法,甚至选材,却浮显模式化倾向,特别是开头和结尾有典型套路。家族绵延、代际矛盾、文化传承是小说的高频主题,并由亲情流转、女性成长、民族特色、乡村振兴等关键论题架设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路。热爱、朝气、信念,正以梦想的名义,被压实于略为滞重的“上一代人”城乡赛道。当前高校创写习作揭示青年学生依然保持稳妥的乡土叙事,将其作为能够最大量储存个人思想的容器,同时核心细节均匀分布于虚构故事的中轴线,一旦作者未找到巧妙的转场方式,某个年代时间或某处地方空间,就搬运至各段生活的衔接点。应该说,线性叙事最普遍,作者用心经营叙事技巧,可组构的社会网络大多较为稀薄,人物关系依旧为点对点式塑造。
从人设上看,创作者以人物为中心,矗立起一个个成长故事,借此传达其对事件的认知和对人生的反思。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作品主要是创写者的单向自我输出,客体的行动与语言实则由主体来驱动,他们并非从现实生活中自然走出,而是经过被创造、被规划。作者不由自主地对标成熟且成功的文艺作品人设,再推出包裹多条戏剧冲突线的人物,赋予其鲜明对比以激发叙事的持续动能。祖辈和父辈是最受高校青年创作者倚重的描写对象,文本透露着对他人历史场域的某种“熟悉”,当所有人物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怎么结局皆出自作者想象时,作品很难有接地气的“新感受”与“新观点”。
从生活细节上看,当前青年写作者认同生活对创写的重要性,也愈发注重观察日常,习惯性记录个人周边的变化,并始终对社会特定人群充满探索兴趣。他们经常捕捉某一个时段或时刻,立即以此为原点面向过去,当下性和未来性被选择性忽略。创写者调动共识经验融入创作时,就需同步该经验所处的历史环境,而故事之所以可以自我感动,却难令他人共情,原因在于真正深入生活并不充分,经验与环境产生错落,作者未钻研细节从何而来、又如何逝去。
高校创写拥有一批热爱文艺的青年学生,他们具备良好的文学感觉和文学表达,我们若解析输入/输出教学环节的各自比重,并理清其匹配度,会发现课堂教学实则在两个向度都还是点到为止。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园/社会,之所以能形成教学设计的一组组对比,是因两者之间存在真实助推创写的相辅相成关系。教学明确组合的重要性,但未确立合适方法以落实效度及深度,匆促地输入(阅读)和输出(写作),制造出堆砌式创作,自然连带视域的窄化与思域的扁平化,最关键的是,作品始终缺少些活泼、新鲜、有意思的生命力量。
文学创作是一种表达,高校青年学生愿意诚恳地将心灵交付文艺创作。在实际创写中,写自己和写周边是较易操作的路径,强熟悉度协助作者迅速建立素材库。然而,写作是需要磨时间的兴趣,“读-写-改”更是一个闭环系统,创意写作无法速食,也无法速成,任何一次创意产出都源于素材的充沛和思考的充分。阅读学生作品能感受到,文本信息已展现作者努力地完成某类生活的复现,可借用熟悉的经验对替代体验生活这一长期进程一直跃跃欲试。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性不完全等同独特性,尤其对文化传承这类重点选题,创写者会不约而同地强化中华优秀文化的部分标志性符号,如地方戏曲、非遗,又因弱化文化内部的深层探进,令这些元素流于形式,反倒成为一种突兀的文化点缀,若对艺术效果进行检验或可发现,保持原故事的结构,甚至人设、细节皆不变,置换另一个文化符号仍然逻辑自洽。
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羽”计划既是高校创写教学的一次检验,又是对其提出了具体要求,“新”建立在“真”基础之上,首先扎根当下现实,追寻日常真相,是创写后续突破的必要准备,求真比求异、求美、求新更需师生共同渡过漫长的坚持与执着的探问。
(戴瑶琴,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书评人。)
一个观察“为什么写”的契机
——“春羽”计划综述
李晓晨
这次参加“‘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评审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集中地读过这么多年轻写作者的文学作品。在这样一个不限定主题的小说征文中,众多来自高校的写作者们展现出了自发、蓬勃而令人欣喜的创作热情。他们敏锐多思,视野广博,叙事甚至颇为娴熟,向想象中的理想读者阐释自己对人、生活、自然、世界以及各种关系的认知与理解。
总体来看,这些基本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写作者大都对文字充满了自信,作为“网生一代”,他们自幼便生活在一个敞开的、阔大的、多面向的世界,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通过各种方式接触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有些人对某一位或某一类作家艺术家的风格十分熟悉。不管所进行的是什么类型、题材的创作,大都有丰富的阅读经验为基础,这在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年轻的作者们对伟大的前辈和经典作品的致敬。我留意了他们的专业背景,其中只有一小半来自中文及相关专业,其余大部分具有医学、计算机、法学、外语、金融、建筑等学科背景,这实在是令人振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文学在一个人成长的历史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在求学、就业、考取各种证书的间隙,还有人愿意花时间不带功利性地阅读、写作。文学毫无疑问影响着他们的人生、价值标尺和认知观念,在生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这种滋养将成为给未来提供精神支撑的源泉。
回到作品本身,此次参评作品所涉丰富,校园生活、家庭伦理、情感体验、生态环境、宇宙结构、民间非遗等皆在其中。如小说《经纬线》聚焦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织锦,通过家族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几代人苦心织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从家乡带到国际舞台的故事,作者的写作气魄和笔力值得称道,在小说结构上也颇具匠心,尽力在短章之间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还有对碎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十五秒之外》虽然是科幻题材,却深刻思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们每天都面对的命题:当人类的认知被局限在15秒视频之内,那些延续数千年的思想和经典究竟何去何从,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发生永续性改变?《鲸有死日皖无出涌》则巧妙结构,将现实与过往线索并置,重新拼贴、建构出一位作家的创作与过往,新意迭出,巧思独特。小说《平原往事》《象牙舟》《江格尔》《羽化》等,思接千载,由古至今,有的重新改写神话史诗,有的以小切口切入生态保护主题,有的从个体经历出发试图完成对城镇化进程的观察与思考……这样的写作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不仅关注日常,也敏感于时代生活的巨变——既是时代的,同时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过,在集中阅读的过程中,我也时常会觉得恍惚,有时觉得面对的是所知颇多、熟稔文章写法的写作者,他们非常知道什么是对的、好的、技巧成熟的;有时又会觉得作者似乎还没有触摸到写作的根本,他们笔下的是一种相对陌生、区隔的生活,以至于通读完所有这些作品后,我最想弄明白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怎样写下了这些故事?我特别希望能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以一个写作者的同理心来理解这一问题,但毕竟离开校园太久,同这些年轻的作者建立彻底的理解和联系似乎存在一些困难。其实,我所希望的是看到能让他们真正“动心”的写作——真切的来自于生活深处的体验与思考,而不是完全建筑在阅读与理性之上的文字的城堡,毕竟,那些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首先应该能触动作者本人,此后才有可能打动更多读者。
对创作者来说,文学应该是不吐不快、不写不行,面对时代的巨变,写作者需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并与之相匹配,怎样获得新的题材、新的视角、新的经验、新的情感,怎样同更广大的人群建立直接、真诚的联系,这可能是需要思考和值得重视的。这让我想起东莞素人写作群的写作,他们一边忙于生计一边写作,很多人都说,“生活里的故事太多,有很多创作想法,不写下来觉都睡不踏实。虽然知识和技巧不够熟练,但特别愿意一边阅读,一边摸索写作,这是富有激情的事。”我想,这样的创作实践也许会为年轻的写作者提供启示和经验。
创新和创造从来都是极其艰辛的,它始终来自大地,来自人民,并让更多人因此变得更好。在这个充斥着算法和流量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回归文学的本质,并一再重申:写作不是为了成为作家,更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它关乎人心,关乎世道。我想,这是每一个热爱文学,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需要时刻警醒的。
(李晓晨,“‘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终评审)
乱花渐欲迷人眼
——“春羽”计划观察
陈丹玲
中国作家网“‘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主题征文作品呈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生机和景致。
文学,是与人为善的事情,是通过创作对生活的重建与心灵的倾诉。为何而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绝大多数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深受经典滋养和与理论指引,渴望在实践中传承和创新文学传统。譬如读到由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作的小说《杀死那个陈丽娟》,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姐妹间复杂的情感纠葛,通过对陈丽娟这一叛逆形象的塑造,探讨了个体在社会与家庭中的挣扎与自我认知。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深度关注,充分体现了具有专业性的价值追求和对深度思考。
在小说创作动机上,非文学专业学生则表现更为多元。他们可能因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独特见解、生活经历的分享欲望或对某个主题的浓厚兴趣而进行创作。在题材选择、语言结构,以及细节设定上显得余裕和自在。比如一个会计专业的学生在小说《风的年轮》中,将视线聚焦于草原与风电的共生关系,由此展现了生态与科技的融合之美。这种跨领域的创作动机不仅丰富了题材涉猎,也为专业领域的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文学专业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通常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与方法。他们精心构思叙事主线、隐线,注重情节的合理性、人物的逻辑性以及主题的深刻性,他们训练有素,对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内心非常明确。比如,小说《寻找金字塔》对“金字塔”搭建与毁灭的描写,充满了童趣与想象力,体现了作者捕捉与运用灵感的能力。
事实上,不论专业背景,参赛作者们结合所学专业知识,以及深入社会问题调查的体验,都在作品中留有一定印记。在表达上,除了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之外,更多元的词汇、概念、场景等被容纳进来。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叙事凌乱和创作体裁的模糊。而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
(陈丹玲,“‘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初评审)
一次“青春力”的唤醒
——由“春羽”征文所想到的
杜佳
2025年初,在回顾梳理日常来稿、“本周之星”选拔、《灯盏》文集编撰等原创频道工作的过程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感受是“好小说的稀缺”。这引发了编辑们的共鸣。于是,一项初衷为“发现选拔具有写作新质的小说作者”的动议萌发了。经过更细致的考量,我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青年写作者集中的高校,正式开启了这趟发现之旅。
从启动到揭晓,一次又一次与这些文字面对面时,我们深深意识到,数以百计投稿背后的意义和分量——是青年写作者在新视野、新表达、新审美倡导下的集体探索。经由文字的书写,我们得以第一次如此集中而清晰地看到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虚构、个体与时代之间寻找文学的、也是精神支点的努力。
青年写作如火如荼的当下,一次以“为平台发现有生力量”为契机的征文,或许仅仅是沧海一粟,却也构成了一枚观察当下青年写作的切片,用实践印证着从题材、技法到审美趣味的嬗变。
一个首先浮现出的问题是“怎样的小说是我们期待中的好小说”?
阅读过程中,令人感到触动和欣慰的是,尽管面向各有侧重,表现也趋于多样,无法一一尽数,但毋庸置疑,“对传统与现代差异所形成的张力多有探索”正成为许多作品共同的主题——城乡差异、数字鸿沟、老龄化、性别议题、代际关系、成长阵痛……时代洪流冲刷之下,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命运的关注,正在青年作者笔下变得鲜活可感。对真实生活的细微体察成为这类书写的重要特征。在写作者的视野中,“看见”正成为一种抵达时代深处的力量。
张济显的《断桥谁见》用一个小小的裂口去触碰权力、性别等大议题,凸显举重若轻的美感;王丽妍的《经纬线》同样诉诸巧劲,将黎族传统技艺黎锦的传承与几代黎族女性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经纬交错间照见的不仅仅是个人际遇与命运,更映射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步履印痕;思铸航的《挽回荒原》是一个关于“短暂交汇”的故事。原本并无交集的男女偶然地相遇了,各自困顿的人生因此拥有了一丝安慰,不过,正像草原上的两条河流注定再次奔向不同的远方,“他们”也终将不得不迎向各自的命运。亦真亦幻的笔触之下,作者无意塑造一种陌生的奇观,而是怀着深切的悲悯试图通过书写触摸那些困境里的人和“他们”抑或说“我们”无从祭奠的孤旅;范愫的《金珠》以沉浸式的生活细节描摹一种“现代病症”,人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相处,有时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了解。日复一日的见面重复着一系列程式化的情境,就像小说里的瑜伽动作和结束语,不断提醒着人们也许“相逢对面不相识”,而真正“走近彼此”的契机永远需要有人率先破除心防,让光从裂缝流淌进来,照亮彼此赤诚的瞬间,也是与自我、与女性身份和解的瞬间;女性故事在这次征文中不算少,但刘倩的《来烫头发的谭姐》在其结构和女性形象塑造中仍然让人过目不忘。在作者笔下,女性的命运有了更多的面貌。讲述视角的转变与其承载相契合,不乏巧思,以“我”的纪录片拍摄工作为引子,理发师黄洪霞眼中的顾客谭桂花的故事,映射了一个“女性互助与情感回馈”的故事,当“我”的身份揭露,谭姐原来就是“我”的母亲,如此,“我”也通过他者重新认识了母亲的另一面,补全了自己的记忆,完成了“代际和解与人的相互理解”……
聚焦现实的同时,不少作品插上科学幻想的翅膀,呈现另一种面貌。当人人认同科技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之手,便捷、先进、智能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还有人好奇“月之暗面”,那么小说的书写便发生了。时潇含的《晒背》就是这样一篇关于未来想象的科幻小说。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们这些被智能时代落下的人,落到要为那些让我丢掉工作的机器人服务的境地了”,这几乎可以看作理解全篇的题眼——当科技高度发达,吃穿等生存需求不再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人的精神将寄托在哪里?小说通过一种类似“心流”的辩论展开叙事,非常有代入感。事实上,《晒背》中的“辩论”绝非孤例,而是频频出现在“春羽”科幻题材作品中的重音。尽管语调各异,其间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但年轻的写作者们都没有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借科学幻想一途,迂回地折射了对现实世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从中提炼出文学的金子。
一定意义上可以认定,以青春笔触、独到发现回应时代议题、展现现实关怀,同时飞扬想象的小说是我们期待中的好小说。
另一个萦绕始终的问题是“好小说是否意味着完美无缺”?
为发现具备新质的书写感到欣喜同时,我们也不无担忧。阅读来稿时,某些试图探讨社会议题、捕捉时代情绪的小说,无论在写法上、还是内容上都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在“舒适区”“安全区”打转。举个或许有些不恰当的例子,假如从两篇反映初入社会的彷徨心态的作品中各摘取一部分,加以互换,粗看之下甚至“毫无违和”,而这样的情形对于追求异质的书写无疑是尴尬而危险的。聂鲁达说,“所有青春都像一盏灯,在雨中被冲倒,湿漉漉却在燃烧”,这意味着,青春敢于在未知的冒险中砥砺自身,方能焕发一往无前的力量。
前不久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揭晓时,奖项评委、马华作家黎紫书在颁奖现场的一段话颇为“出圈”,在大多时候习惯了“柔风细雨”的批评场合中显得振聋发聩。当年出身文学奖优胜者的背景,让黎紫书坦言自己“是被文学奖抬举出来的作家”,深知一位作家在文学奖评选中“被看见”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她作为前辈担任文学奖评委时,也会“很有心机”地利用算法托举自己认为“需要一个机会”的年轻写作者。比起技艺圆熟、完美无缺,在广阔的华语文学世界,她宁愿看到“即便技巧尚不成熟,抱有缺憾,但足够有野心,更奔放,更有突破性,不那么小心翼翼、大局为重的作品”。黎紫书所述尽管无法与“春羽”面临的境况一一对应,但其呼吁却与我们对从“春羽”中走出的写作者的寄望不谋而合。
从最终获奖名单来看,来自高校创意写作与中文专业的学生占据了相当比例。学院化的写作培养模式,一方面为青年写作者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训练,另一方面也由“写作可否被教授”的争议引发更多反思。“春羽”在一定程度上用切实的方法回应了对当下文学教育的反思,发现文学新人,更试图引导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于是,打破“门户之见”成为一个重要考量。评审以作品质量作为“最优先”评判标准,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不同学科背景的作者们同台竞技的景象。或许,这恰恰意味着一次“青春力”的唤醒。获得一等奖的胡旸旸目前并非文学专业学生,离开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这次参赛成为是她重拾写作的一个开端。得知获奖消息后,她曾激动地告诉我,当年轻的灵魂在纷繁复杂功利中悬置了文学,她总会记得此刻,记得“春羽”这个“复活点”。
春天的羽毛,乘风而起,终将抵达我们无法预知的远方。
(杜佳,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编辑、“‘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统筹策划)
改谅轻易的伏从,通洗艰涩风干的金尖
胡旸旸
《干娘菩萨》脱胎于中学时代的语文阅读题及我一名祖先的口述史。阅读题是一段谈论“赤脚郎中”的非文学文本,其使我知道这项听起来相当前现代的符号的尾羽竟然延触到了如此晚近的年代,发展的参差竟然拥有这样的张力;“十三”则是我曾祖母的序齿,她在湘中方言里被叫作“十三娭毑”。那段时间我正在打听这位没见过面的祖先,在我当前的专业方向中可能也文绉绉地被称作“口述史”。她在上世纪上叶有一度煊赫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后半生又投入当地基层基础教育工作。口述史赋予我诚然如史的凝重、触碰与怀想神追,我感到生动、感到好玩,同时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怖:逝者的曾经存在究竟能保持多久?许多事情包括很细微的细节,一片草的颤动、一颗露的冷坠都诚然发生过,但一切曾经发生的都将随亲历者的消失而淡褪。我因而感到有通过更不朽、更明白的载体来保留这种“发生”或保留一种“发生的意境”的必要性。这就是我构造如此时空背景的原因;又为了更轻盈的写作责任,我虚化了具体地区及其方言、改换了人物的职业,在“科教文卫”里选了更具发展关切的一个。同时,纯然发展关切也不是完整的动机,不但因为旧的发展问题在今天已然快车上道、旧的关切隐隐似乎是过时的,还因为写作的我毕竟是一个年轻的人。我所眼见许多家庭的形态、纠结的血缘、求学的远走、背井离乡的故事仍然在不断上演,交通迭年发达的时代仍然存在有其难处的不相见、不和解,有新的乡愁和乡恨。我什么都想寄托一点,《干娘菩萨》就是这样发生的。
必须要说的是,它能获奖,我其实也感到意外。这是朵没被期待的莲花。投递是个偶然,投完后一度遗忘。它的草稿写成于某个高中的晚自习。我的童年少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属意要当作家,写绚烂的庸俗恩仇、流水式快意际遇。有枣没枣投一杆子,不知死活收获《收获》的拒信,在十月被《十月》退稿。不敢想这个奖发生在更早,我会如何仰天大笑、喜形于色、大掀蓬蒿,但它发生在今天,只容我骑车去上选修课的路上趁风哭了千把米。
我很久没有专心写小说,早已像无数无法以此为生的人们一样走进了新的评价体系,得到了比赛、实习、论文、报告。现在接触的文字工作,也以专业材料文献为主。在高校写作挑战人的敏感、宁静和毅力,我们不幸而万幸身处遽变的年纪,分分秒秒都浸透着“沉没成本”的潮湿气息,宝贵的灵光和嗅觉要提供给诸多事宜。把自己掷给写作是奢侈的事。太敏感就会显得脆弱,太宁静就会错过煊赫,太有毅力就会失去分给其他事务的毅力。我曾经承认自己于此道不通。承认“做不成诗人”,为不再写而狡辩,不知道有一天能在文无第一的世界里取到第一。意味着我把文学吊了起来,羞于谈论(就在这时我还感到文学:多幻想的一个大词),承认遗憾、承认错失。就在这种时候,错失的又回来了。不能不令我流泪。
故我回头再看征稿要求:“……为及时发现文学写作的新生力量……”发现,发现。仅代表自己,我对这个词报上含泪的感念。我固然是被发现的那一个,但远不止被某个平台、某次活动发现;还更有我作为一个把写作、把文学悬置了的人重新把自己再看见的心情。
本次获奖后,许多高校的同学、老师、朋友发来祝贺。他们无一以文谋生,无一从事文学行业,我却看到了许多文学的蛛丝隐约颤动着。公共课认识的大学同学经营着盛放随笔的公众号;学传播的中学同学有过每每高分的作文卷面;评论一长串尖叫声的英专生以前会把试卷剪成拼贴诗;走了艺考惯会摄影的小男生有过一个小笔记本专门记录偶得;早出晚归最刻苦的法学er当年在最紧张的高考前一个月逐句看完我写的小说;因公交集的外校马院“青椒”爱读《红楼梦》。他说:祝贺,苦难的人间不能没有文学。高校也就是这样,年轻的灵魂在纷繁复杂绚丽功利中最不乏一怀隐秘的性灵。
我由是得以凝视我自己,维护今日生活、透过去日泪眼,改谅轻易的伏从,通洗艰涩风干的金尖。
如果真于此道卒有所获,我总会记得今天,记得“春羽”是我的“复活点”。——我们共勉!只要有了念头,总会继续写下去。
(胡旸旸,就读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征文一等奖获奖者,获奖作品《干娘菩萨》)
是虚构拯救我们
思铸航
我理想的创作状态是一种独立而自洽、敏感却可调节,能捕捉到转瞬即逝的一个词,能体验到悲哀的可贵的状态,可能我曾短暂拥有过它,但在我上大学以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从头开始。我一直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按时间段机械地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一期”即2019至2022,我避世的高中三年,只是埋头阅读,一篇一篇写,迷茫地完成某座建筑。阅读方向的缘故,我的小说虽稚嫩矫情,脱离当下,但相比今天,胜在大胆率性,情真意挚,一字一句都经历足够的思索。
我的大学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珲春”源自满语,意为“边地、边陲”,东北的边城寒冷且荒芜,日本海的海风力大如钟,彻夜吹拂,天黑太早,什么都没做,一天就结束了,课程不多,能逃则逃,大学前三年有不少时间供我读书和创作。我还是反复阅读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海明威、博尔赫斯、莫迪亚诺、高行健、马原……他们笔下的骤雨、山林,依旧在晴朗的晚上震颤我。
我打定主意要写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而我终于发现有如此野心的作者不止我一个,他们坐在写字楼里、站在中学讲台上,或者像我一样尚未进入社会,在大学宿舍里戴着耳机码字。偶尔和天南地北的高校作者们线下聚会,聊八卦,心里一层隔膜还在等待溶解,没有人轻易捅破,终于到深夜,口干舌燥,呷一口冷茶,叹一口气作为上面环节的总结:“想出头不容易”。于是纷纷点头附和,话题终于引到创作本身来。这样的夜晚是可贵的,你可能终于获知同龄的高校作者天马行空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无比热爱想象力,却越来越不认为能靠这些文字能完成什么。
写到上世纪的事情,我总是和我爸打电话确认一些漫漶不可辨认的细节。这次比赛中,我的参选作品《挽回荒原》,一万字,共花费四天时间(对我来说已算迅速),也要多亏我爸,他知道怎么开运输车,怎么杀羊制皮,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我第二篇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受到万玛才旦的一些启发,算是一种尝试,抛开我熟悉的西安和延边,去讲述一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藏族男人寻找虚构生物的经历。
从十五岁写下第一篇万字的小说时,我开始意识到虚构的魅力,它让同桌啧啧称奇,让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冥想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后来我才意识到,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创作者,虚构是我们唯一能做,且有希望做好的事情,在面对不同时段的压力时,我知道虚构拯救了我们,它告诉我生活习惯提出问题,可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要去回答,虚构默许了我的逃逸,并减轻我的内疚——打不过就跑吧,跑远了再扔石头砸,一点也不丢人。
我也重复确认,我的身上携带着紧迫感,证明我对生命叙述的警惕,以此鞭策自我。同时我又对自己尽可能宽容,去信任“灵性”,感知世界微弱的变化和响动,我用拙嫩的、浅白的“一期工程”使自己到达了某个有几率被真相指控的位置,接着进入更宽阔的创作领域,交谈更多,却失去自由。高校作者们的创意写作趋于同质化,我想到这或许也是丧失“紧迫”所导致,但幸运的是,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小说作者不再满足于转折突变或辩论证伪,而是去“推翻”,甚至跳出文本圈套,来指认和审判自己作为作者的身份,也许这是创作者承担责任的一种体现?
我永远追求悲哀和抒情,也期待更多和你们畅所欲言的夜晚,向诸多青年作者致敬。
(思铸航,就读于延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春羽’青年写作新秀发现计划”征文二等奖获奖者,获奖作品《挽回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