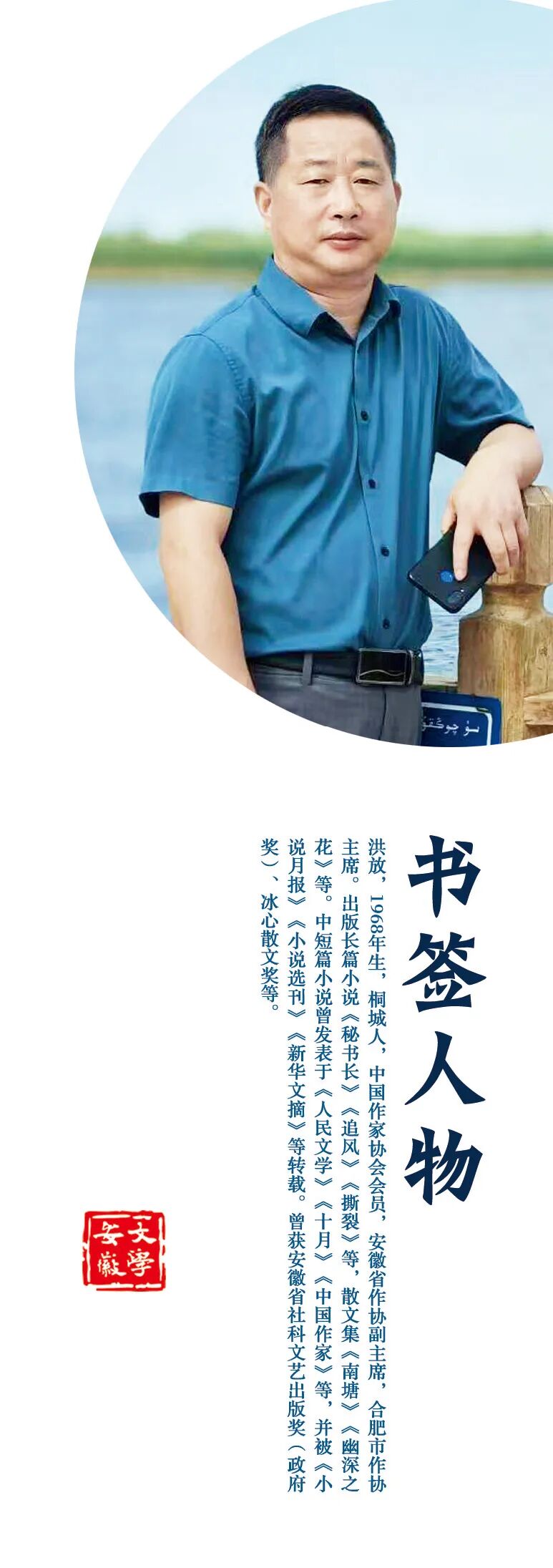《安徽文学》2025年第6期|洪放:松香一样迷离
1
省里组织宣讲团,到各县去宣讲。团长问我想到哪里,说这样的活动,既是宣讲,也是调研,还是一个会会亲朋好友的机会。我说我回青桐。青桐是我以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的老家。三年前,我以人才引进的名义,从青桐调到讲师团来。我也没想到,快五十的人了,从中专毕业就一直在青桐机关熬鹰般地熬着,居然有一天熬到了省城,成了讲师团的讲师。省里愿意要我,特别是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点名要我,我觉得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我一直没问过团长,但我心里清楚,理由不外乎三点:一是我一直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大小也是青桐县委政研室的主任;二是这些年我发表了几篇还有些分量的政策研究文章,其中有两篇还被高层批示;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有些私人化了。团长也是青桐人,以前就熟悉我,我在青桐的那些年,也或多或少地为团长办过些私事。不过,这一点是我的猜想。团长是个有原则的人,他大概不会为了这些私人交往,就硬生生把一个县城科级干部,直接给挖到省城。记得我拿着调令离开青桐时,县里领导很是有些不舍,说,青桐这块地方毕竟是小了,小了,就藏不住小刘你这条龙。我说领导批评我了,我哪是什么龙?我顶多算是文庙泮池里面的一条小鱼。后来,有两次我陪着团长去青桐,县领导说团长将青桐的人才给抢走了,搞得青桐现在政策研究这一块很被动。我听着这话,只能一笑。团长很是快乐,他望望县领导,又望望我,说:“反正都是青桐的人才,到省里了,还不是为青桐做事?不仅小刘,就是我,不也得听家乡父母官的?”
时间过得太快,省城三年,我一下子就从五十挂边,成了五十多岁。我一直记着团长在我到省城上班时的那次谈话。团长很是亲切,说为什么要调我来,又希望我怎样发挥作用,还有就是应该注意些什么,说我以前在青桐,跟省直机关打交道多,很多事情都熟悉,但那可能都是表面现象。真来了,要认真观察,深入调研,多思考。说到底,就是摆正位置,多出成果。团长特地叮嘱说,以后别再写那些小说什么的了。小说,留着将来退休了,再好好写吧。我点头,团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他的话,我必须听。小说,我确实写了二十多年。在那之前,我还写过十来年的诗歌。骨子里,我把自己当作文人,可我又实实在在是个小公务员。小公务员该有的好习惯、坏习惯,我都有。大酱缸里泡久了,再怎么洗,也洗不掉酱味。何况,我压根儿也没那么高尚,那么纯粹,我也没想过要洗。反正都是工作,都是过日子呗。在县里到了顶,就到省里来。至于往后,谁能说得清呢?
讲师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宣讲团,到各地宣讲政策。这活看起来高深,其实也是程式化工作。每次宣讲前,团里都组织集体备课,统一教案,制作课件。宣讲的人,是按照团里任务分配,对照课件去讲的。讲的时候,可以有所发挥,但有限度。这个限度,只有宣讲的人自己能把握。我到底在政研室干过几年主任,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上手很快。我白天在团里兢兢业业,晚上回到宿舍,还是忘不了小说。好在现在的文学报刊,团长和其他人根本就看不着,也不会看。我发表的小说,活像自己的私生子,藏着掖着,从不会抱出来给他们看。不过,到底是发表小说了,外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是指文学界。甚至,省作协的一位领导还专门打电话找我,要我多跟他们联络。我说我真的没工夫,何况写作对我来说纯属业余,等以后退休了,我一定跟着他们混。我这话没毛病,也是真心话。同时,还响应了团长的要求。
团长见我不语,便问:“怎么,有事?”
“没有。我正在想去哪里。”我说。
团长说:“又不是相亲,还需要这么想?快定一个!“
“那就淮县吧。”我说。
“好,那就淮县。”团长拿着手机,接电话去了。
我回到四个人背靠背办公的办公室。老唐问我决定去哪,我说淮县。老唐有些奇怪地盯着我,问:“咋要去淮县?那可是北边。跟你老家青桐,隔着三百公里。你到淮县去,那里有熟人,还是情人?”
“都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淮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淮县。”我说。
老唐不信,老齐也站着,喝着茶,吐着茶叶,望着我。这确实不合常理,一般情况下,大家选择到哪里去宣讲,都遵循宣讲、调研、会朋友的三原则。而我真的没有。淮县我一直没去过,我只知道,淮县地处皖北,是淮河岸边的第一大县,人口近两百万。经济发展不好也不坏,属于全省中等。至于那里的民风民情,自然资源,我都不清楚。那就奇怪了,我为什么在那一瞬间,就想到了淮县呢?
大家都不信我的解释,我也解释不了。于是,不了了之。我就被确定到淮县宣讲。
一周后,我坐上了到淮县的高铁。淮县那边说来个车子接我,我没同意。一来,我不是什么领导。二来,坐高铁是我喜欢的事。我喜欢静静地坐在高铁窗口前,看高铁风一样驶过广大的原野。我并不是喜欢那沿途的风物,高铁太快,根本看不清楚。我喜欢的是高铁的速度,犁铧一样,一下子就犁开了那大片大片的苍茫与混沌。就像一篇小说,一旦进入人物内心,就像流水一样,一泻千里,恣肆汪洋……
2
下午的宣讲算得上顺利,两个小时宣讲,半个小时互动,关键是听众素质高,纪律好,会风正,互动环节问的问题恰当。主持会议的淮县县委副书记总结说:这是一堂高质量的政治课。我听了,只是在心里笑笑,脸上依然挂着宣讲应有的严肃而活泼的笑容。
中午县领导陪着吃了饭。现在县里很为难,公费接待,不准喝酒。因此,中餐有些草草。我倒是喜欢。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后,县委宣传部的黄部长陪同我调研。黄部长问我想去哪些地方,我说,来了淮县,听部长安排。他比我大两岁,头顶全秃了。他还不断地摸着头顶,好像能从那里摸出一蓬青草来。他说:“那我们就随便走走,淮县是个人口大县,但县城不大,可看的地方也不多。我知道刘教授不仅是教授,还是作家,那就去看些老古董吧。”
“作家?哈哈。黄部长过奖了。”我其实有点小激动,能被人称作作家,比称作教授,或者领导,感觉要好得多。
黄部长说:“当然是作家。而且,首先就是作家。”
“怎么个首先法了?”我问。
“刘教授早年写诗,后来写小说。您的很多小说我都学习过。”黄部长又摸了下头,还将手拿到眼前看了看。我也不知他到底看出了什么,反正,他看着自己的手,有种恋爱的感觉。他说:“年前,我还在刊物上读到那篇写忏悔的小说,深刻。”
没想到,他还真的读了我的小说。我更激动了。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激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偶尔写点东西。当然,跟刘教授比,我那都是小儿科。不过,那些东西,可也都是用心写的。”
我很想说我也看过他的作品,但还是没说。我怕他较真,真的问我看过哪一篇,那就露馅了。我只好点着头,说:“写作是一种爱好。我们都是爱好。这是一辈子的事,与其他无关。”
“对,太对了。”黄部长兴奋地又摸了下头,说:“我经常跟县里的那些文人们说,这些都是爱好,不要指着爱好当饭吃。该干吗干吗,有闲工夫了,有闲心了,再写。可不能因为爱好,把自己的好生活硬生生给废了。”
“这个我同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笑着说。
黄部长接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文学创作上来。说淮县两百万人口,拿得出手的作家却没一个。都是半油篓子,上不得台面。究其原因,还是学习不够,悟性不够。想起来就满腔激情地写,写完了,也不知道好坏,找个刊物邮箱就投,结果当然发不了。省级刊物一年也上不了一两篇。作家协会总结时,就很难堪。他问我:“现在都在破局,咱淮县文学创作这局,怎么破?”
我想了下,说:“还是读得少了,见得少了,想得少了,写得少了。”
“好,精辟。四个少,就是这四个少。如果再加,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条:爱得少了。”他脸上放着光,指着车子前面说,“马上要到宋朝建的大福寺。你要问县里街上怎么没有什么人?到那里就知道了,都去那了。那个心,诚得跟石头一样,砸都砸不开。要是写作的人也这样,我就不信,咱淮县出不了像您这样的大作家!”
“我哪是什么大作家?我也只是业余玩票。”我说,“不过,说真的,现在搞文学的人,确实少了些虔诚,少了些热爱。”
黄部长叹着气,说:“哪像我们年轻时候啊!”
他这一叹,跟一根烧红的铁丝一样,猛地烫到了我的神经。好像我的身体内,或者思想中,本来就有着一处隐秘的地方,被他这一叹气,挠了个正着。随即,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有“嗞嗞”的声音,继而有轻微的疼痛。这种疼痛很快就传遍了全身,像在大冬天突然光着身子跳进了冰窟里,那种刺疼,来自神经末梢,次声波一般,隐蔽,有力。
老唐问我怎么想起要到淮县,我觉得我开始接近答案了。我到淮县,一定是有理由的。现在,这种理由,正用刺疼的方式,一点点地接近我,覆盖我。
我说:“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
黄部长问:“怎么了?老刘。”他认准了我作家的身份后,改称老刘了。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有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淮县总有什么关联。”
“那一定有。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到一个地方去,停下来,忽然感觉那地方曾在哪里见过,包括环境,还有人,都见过。你说怪不?后来我看了外国的书,说这可能涉及量子学说。”黄部长继续道,“太复杂了。但真的有。”
“可是,我到底跟淮县……”
“那可就说不清了。也许,也许……你这次来宣讲,其实就是。你信不?冥冥中,一切似乎都注定好了的。”黄部长又问师傅:“今天有鼓书不?”
“不知道。”师傅说。
“要是有,那真该听听。”黄部长接着道:“老刘,刚才说到我们这县城里的作家,说真的,也不能算作家,顶多算个写文章的人。这时代不同了,要是再早三十年,那时……说真话,老刘,你怀念不?反正我是很怀念的。”
“好像很远,又很近。可一晃也三十多年了。”我说。
“记得有一年,我们一班写文章的人,冒着风雪到淮河边的正阳关古镇。走在那里,一个个悲壮得不得了。一边走,一边念诗。回头想想,疯子一般,不过倒真可爱。”黄部长又说,“我那时刚刚师范毕业,在一所乡村小学里教书。每个月几十块钱工资,除了给家里一点,其余都跟一帮哥们儿喝掉了。喝酒也都有名义,谁的作品发了,谁又写了一篇好散文,谁又被留用了一组诗。甚至谁看上了哪个女孩,谁第一次亲人嘴了,都得喝。有句诗叫‘诗酒趁年华’,是吧?真的好年华啊。”
我的眼前一下子就晃荡起一大群人,排着队在大街上飘忽的样子。夜里,冷清的街道上,都喷着酒气,高声唱歌,背诗。间或还高举起手臂,大声说:“为所有举起和不举起的手臂。”那场景是在青桐,那时我也刚从学校毕业,拿着一份稳定的工资。因此也跟黄部长一样,成了众多集会的组织者。我记得我们沿着青桐的南大街,从南城门口一直飘到县广场。在广场西边的篮球架下,有人扶着水泥球门狂吐,有人唱着《何日君再来》,更多的人是沉默。那个年代,要么沉默如金,要么高歌猛进。我们都有了,我们仿佛成了那个时代的影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青桐,路过已被改造的县广场时,还能看见那些影子在月光下飘忽着,水草一般,冒出无数稍纵即逝的泡泡。
我想着,有那么一会儿,沉浸其中了。一恍惚,似乎有一个影子向我走来。那是一个瘦高个男孩,跟我差不多大。他说着外地话,朝着我走来。觉得他说的话,跟黄部长的话,押着同一个韵,拖着同一个腔。我心里一颤,望着黄部长,正要开口,他说:“大福寺到了。走,下去看看。”
3
大福寺是宋初建的一座大寺,传说当年赵匡胤领兵在此打仗,时间一长,军中粮草耗尽,情况十分危急。后幸得当地老百姓送来一种面饼,解了燃眉之急。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不忘旧恩,便赐这面饼名为“大救驾”,同时赐建大福寺。大福寺的规模,据说是淮河两岸第一。它最兴盛的时候,僧众一千多人,吃粥时得用水车运送。当然,现在大福寺依然人流不断,香烟袅绕。我们挨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从侧门进了寺院的后院。黄部长说得先去找开明大师。
“这大师有些名堂。”他神情间也有些名堂了。
我说:“那倒真要看看。名山名寺,往往出奇人。”
后院里,古色古香。整体建筑风格既有北方的粗犷,又透着些南方的清幽。一般香客,或者游人,不能进入后院。因此,后院难得清静。黄部长带着我,一直走到院子东头,站在天井里,喊道:“大师,大师!”
先出来一个清皮小和尚。我特地注意了一下,他虽然剃了光头,但头发还有小半寸深,就像春天刚刚长出来的草芽,有点黄,又有点英勇。头发间,也没看见戒疤。他神情有些喜悦,说:“黄部长来了,大师一大早就说有贵客要来。果真就来了。”
黄部长朝小和尚作了个揖,又对我说:“是吧,大师早就知道了。”
我早些年,不信佛,其他的也很少信。但近些年来,大概是年岁大了,竟然慢慢地有了改变。谈不上信,但也不排斥。我更愿意听听这些,包括佛背后的故事。我们进了屋,是一大开间,朝东的墙上,窗子巨大。整个室内,一片亮堂。黄部长又喊了声:“大师!”
“来了。”声音很轻,但有穿透力。随着声音,一个穿着黄色僧袍的老人从书架后面转过来,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一手捻着佛珠,一手作揖,说:“施主从大老远跑来,与我佛有缘。快,快,且喝茶。”
我点点头,说:“大师!”
大师说:“我存了些去年淮河的雪水,刚才让诚意烧开了,正好泡茶。”
黄部长说:“真是巧。”
“不是巧,是缘。”大师说着,便接了刚才那叫诚意的小和尚递过来的茶壶,倒了两杯茶,递给我和黄部长。他自己也拿了一杯,说:“开春以后,寺里人多。我有些焦虑。”
“这……怎么还焦虑?”黄部长问。
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寺里人多,才兴旺,这不是好事吗?
大师叹了声,说:“该来的,终该来;不该来的,还是不来的好。各人都有正事,自忙自的才对。”
我心一怔。这些年也走过一些寺庙,还真第一次听大师这样说话。我看开明大师,面容清瘦,眼光明亮柔和。他也看着我,说:“施主是从南方来的吧?看这眉额,应该是写文章的人。”
黄部长爽朗一笑,说:“大师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是教授,又是大作家。”
“早些年我也写过些文章的。”大师这话,既像是回应黄部长的话,又像是自语。说完,他给大家杯子里又续了茶,接着说:“我这边正好有一本诗集,送给施主。不过,诗不一定好。”
我说:“那我正好学习。我就怕悟不透呢。”
大师从书架上抽出本黄封皮的书,递给我。我一看,书名叫《青灯集》。翻开,有一缕香火气。里面有古体诗,也有新诗。我随便读了几首,居然都是烟火人间的事情,有写春天柳树抽芽的,有写河里小鱼嬉戏的,有写香客虔诚烧香的,有写送别友人的。写的都是小事,都是俗事,却写得清亮,通透,一点也不造作。我说:“都是好诗。大师诗歌的功底也是了得!”
“施主一眼看穿了。二十来岁时,我在北京上学,跟北岛他们有来往,因此,也跟着学了几年诗。”大师说,“那时候,年轻人谁都能写几句。不过,这一晃也三十多年了,再没见过他们了。”
“真没想到,大师曾经也是个诗人。”我说。
“哪有什么没想到,都是缘分。该有那一段诗歌的缘分,就有了。如今,没了,就没了。”大师忽然岔开话题,“我们斋房那边养了一只猫,昨天生了十只小猫,我们去看看吧!”
没等我们同意,大师就径直往门外走,我们跟着大师,穿过院子,再踅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进到前院,再往西,穿过一座小门,又是一个院子,大师说:“十只小猫,花色还都不一样。看着让人欢喜。”
大师这话音,跟一个长年待在寺庙中人的话音,颇有些不同。明净,且有几分可爱,跟刚出水的小鱼一样,新鲜活泼。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想着。很快就想起来了,就是在青桐街夜色中飘忽的人群中那个朝我跑过来的人——他翘起了嘴角,一边说着,一边朝我打起了响指。
那是谁?我一定记得的。可是,我真的忘记了。我喃喃道:“那是谁?”
“谁?”黄部长问。
我摇摇头,说:“刚才想起一个人来。”
大师说:“我认了其中的一只猫做徒弟。喏,跟诚意就是师兄弟了。”
诚意有些腼腆,说:“我是师兄!”
大师说:“你当然是师兄。那是师弟。都当然是。”
十只小猫,圈成一个圈儿,将大猫围在中间。大师一进门,猫都开始叫。其中一只就半跑半爬着,蹭到大师脚边。大师弯下腰,抱起它,说:“就这只。我觉得从前就认识它了。”
小猫望着大师的脸,安静得像页经书。
看完小猫,大师说他还有点事情,必须出去一趟。又吩咐诚意,安排黄部长和我在寺里用斋饭。黄部长说:“这倒不必了,晚上有安排的。下次我再请刘教授专门过来吃素斋。”大师说:“那我就先走了。寺里正在搞佛教故事展览,可以看一看。”
大师走后,诚意陪着我们去看了佛教故事展览。看到中间,我问黄部长:“不是说有鼓书吗?去听听。”
“今天可能没有。”诚意说。
“咋了?”黄部长又摸了下头,然后攥了攥手。
“好几天没来了。按理,这时候正是唱大鼓书最好的时候,人多,场子旺。可是,那人真的没来。”诚意有些为难,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福寺唱大鼓书,一直都不间断的。”
“是啊,没间断过。唱得好,念得好,演绎得好。那鼓声一响,鼓书一唱,四下里都没了声音,只有鼓书声,上达天空,下抵土地。那鼓书声,唉,可惜今天不在,老刘,那可真的是激动人心,让人抓魂的。”黄部长说着,还拍了拍手掌,又说,“淮河第一鼓书,就是这。可惜,唉,可惜。不过,也没事。我让人问问到底咋了。我真想刘教授能听听,真好,真是好!”
我的心也一下子提了起来,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说:“我还真的很想听呢,我都像看见那说书人了。”
4
晚宴设在宾馆外面的淮水人家。黄部长说这事是他做主的,中餐领导已经陪同过了,晚上就不让领导再掺和。领导们也忙,更重要的是,喝不喝酒成了个问题。这里面的意思我自然懂。领导到了,不喝酒,冷冷清清。喝酒,违反纪律。领导为难,其他人更为难。黄部长说找了些对脾气的人,保证晚上让我喝得痛快。
客随主便,我在宾馆稍稍洗了下,就步行到淮水人家。其实也就七八百米路。出了宾馆,都是些高楼,这是全国各地竹笋一样的新城。新城的特点就是楼高,路宽,人少。转过一条街道,向南再左转,城市一下子矮了下来。一街之隔,就是淮县的旧城,也就是老县城,跟我老家青桐的南北大街差不多。不过北方地大,路修得敞亮,就像夏天男人光的膀子,锃亮。南方地窄,路像条蚯蚓,七里八拐的,倒也有一种逼仄的美。沿着这些矮楼又往前走了二百米,就看见淮水人家的门匾。匾架在门楼上,朱红的四个字,很有些功力。进了门,就有人招呼:“刘教授,在楼上三个8。”
包厢里烟气氤氲。黄部长拉着我,让我坐在主宾位上,菜已经上了一半了,大都是凉菜,也有火锅。众人依照黄部长的安排,一一落座。黄部长让人开了酒,特别声明说:“这酒可是我从家带过来的,今晚这饭,也是私人招待,不是公务啊,今晚是淮城文学界欢迎大作家刘老师。”
我脸热了下,摆着手说:“哪里,哪里。都是写作者,见到大家很高兴。”
黄部长一边命人斟酒,一边一一介绍。都是知名作家,诗人,散文家。介绍完,便直接进入主题。我多少也听说过北方人的酒量,想申明少喝,但一开口,便被黄部长给挡回来了。他也没挡死,只是说:“刘老师是南方人,青桐的。我们每喝一杯,他喝一半。但刘老师必须给我们讲一条关于创作的秘方,或者一段文坛轶事。”
“这个好,好!”马上有人附和道。
话到这份上,我也不能不同意。于是喝酒。第一杯我干了,第二杯坚持又干了。到第三杯,我已经吃力,便喝了半杯。黄部长眼睛就像长在我杯子上,马上道:“欢迎刘老师开讲!”
说真话,这让我有些为难。这还真不像宣讲那样,一桌子的文人,比一礼堂的干部难糊弄。我低头看了下酒杯,心里权衡着,然后站起来,说:“那我就先讲一段80年代我在青桐的事。”
大家都望着我,眼睛里的光跟酒杯里的光,重叠着,又散开;散开,又重叠,交错着。我说:“下午同黄部长聊到80年代那阵子搞文学的事儿。我倒是真想起一件事,有点意思。那些年,文人们热闹,个个精神头十足,而且喜欢到处跑。一个个像串联的蚂蚁,纵横四方。我当时在青桐县一家单位工作,因为发表了一些诗歌,所以,来来往往的外地诗人就特别多。这么说吧,最高峰的时候,几乎每一两周就有一个,或者一群外地诗人到青桐。大家似乎都约好了,到了青桐,主要是喝酒,谈诗,谈诗坛秘闻。小道消息,远远多于正式发布的。那时,还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所谓秘闻,都是靠口口相传,或者写信传播。从外地跑到青桐的诗人们,也给我和青桐的作者打开了一扇窗。”
“那倒真是。我们那些年也跑出去过,也有不少人来过淮城。”坐在我对面戴眼镜的女诗人阿伊说。
我望了阿伊一眼,算不上漂亮,但很有风韵。我点着头说:“正是。都在往外跑,或者在酒桌上高谈诗歌、理想与人生。啊,那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呢。最好!”
黄部长递过酒杯,与我的杯子碰了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既不想打断我的话,又得继续推进喝酒的进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半,其他人都喝了满满一杯,包括阿伊。她喝酒的姿势,跟接吻似的,酒杯紧贴着嘴唇,眼睛是闭着的。酒杯见空后,眼睛才睁开。酒气仿佛缠绕在眼睛里,露珠一般,折射着人影。我坐下来,继续说我的青桐故事。
有一年,应该是1987或者1988年吧?下大雪,我正上班,一个高而瘦的年轻人找到我单位,说他是个北方诗人,路过青桐,要来看看我。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跟他出了单位。那时,我们单位在青桐文庙的边上,我们先去了文庙,看了大雪中的梅花。然后,我带他走了一圈南大街。大雪天的青石板路格外滑溜,我记得他还摔了一跤。现在想来,应该是北方人习惯了走宽敞的大路,很少走那种青石板的小街。他爬起来后,说这应该叫雪巷,戴望舒不是有《雨巷》吗?我说那挺好,有诗意。那时候,诗意是第一,什么事一旦有诗意了,就美好。大雪中,走在南大街上,边谈诗,边趔趄,也挺美好。出了南大街后,我又带他去了西山。如果你们去过青桐的西山,就知道那山其实不大也不小。从山脚爬到山顶,大概半个小时。山顶上有座亭子,我们站在亭子里,看山脚下的青桐城。他说这城像片桑叶,所有人都是桑叶上的蚕。我还真的被他这想象力给惊着了,一个北方人,能用南方的蚕和桑叶来写诗,了不得,真的了不得。我有些佩服他了。我跟他说青桐还有一些诗人,有的写得很好。比如墨土、川亚,还有江原子,诗都写得好,有才情,有个性。晚上,我喊他们过来。他显然很高兴,说昨天晚上在三河喝得太多了,今天晚上可不能再喝多了,喝多了,明天就走不动了。那天晚上,除了墨土、川亚、江原子外,我还请来了两位女诗人,一个叫艾念,一个叫松香。两个人当中,松香能喝酒,且能大杯喝酒。艾念就斯文多了,滴酒不沾。晚上的酒,自然是放开了喝。别看我现在喝不了酒,那时可是酒量不大酒胆不小,我们喝着酒,说起省城一个老诗人跟自己的学生约会,被老婆给抓了现行。结果,老婆用刀将这老诗人的家伙什给切了。他说起这事,不时用眼瞟着两位女诗人。艾念低着头,松香却问了句:“真切了?那不就没了?”
“当然没了。切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他笑着,笑声拐了个弯,直奔松香而去。
大家哄笑。我趁机问他还想看青桐哪里,离开青桐后,怎么走?他端起杯子咕噜了一大口,说啥都不想看了,看着青桐的这些诗人们,就够了。特别是——他指着松香和艾念,说:“青桐的诗人们是有福的。我羡慕你们,我祝福你们!”说完,他喝完了杯中的酒。要知道,那可是当时青桐产的六十度的老酒,他也应该有些醉意了,站起来朗诵道:“姐姐,今夜我在青桐,我想在你的眉睫上,放下我流浪已久的心!”
“好诗。”大家叫着,又给他加了杯酒。
那天晚上,他最后终于醉倒在雪地里。我们抬着他,去了小旅社。第二天上午,他却突然想起来要去看青桐说书。说是昨天晚上松香说的,青桐北大街的巷子里,有个说书人特别神奇,说得好,他想去听听。我不好阻拦,但当时领导正交代事情。我只好打电话给松香,让她陪着他过去。结果那天上午,松香就陪着他去听了说书。那说书是南派说书,用一只小鼓伴奏,主要说些历史故事。但最好听的,不是这些故事,而是说书人的过门词。那是即兴编出来的,很多都是针对现实中的人和事。用词有点黄,又诙谐,听的人,会其意,观其色,大笑不止,确实可乐。很多外地人都跑来青桐听这人说书。我没去看过,松香据说也是第一次去。他们去听了一上午说书,我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太对头了。中午,松香请我也过去吃饭,是在北大街杪子上的那家小餐馆。没喝酒。正因为没喝酒,所以看人就清楚了。我发现他看松香的眼神有些不对了,而松香看他的眼神也有些不对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只灯泡,尴尬得很。松香说那个说书人说得确实好,只是那眼睛,太亮了。说书人的眼睛最好要像松香一样迷离,要梦幻,要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眼睛里,却又润着一层水,波纹样不断往外荡漾。他跟只蜜蜂似的看着松香,问:“那我呢?”松香说:“也不够。”他说:“会够的。”我一时弄不清楚他们这一唱一和,只是笑。午饭后,松香送他坐大客车去江南。照例,是我们给他买了车票,我还另外给了他二十元。那些年,这是诗人们来往的一个基本礼数。后来,不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到青桐,他也就慢慢地被湮没了。再后来,我们苟同于人世间的各种俗事,离诗歌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松香要跟随那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富商移民澳大利亚,临离开青桐前,约我们当年几个诗友小聚。最后告别时,她说起多年前,那个来自北方的男诗人,跟她纠缠了很久,她甚至都有些动心了。但不知怎么,他就突然消失了。她感叹说:“这人世啊,这沧海。”她还说:“要是将来有一天你真碰见了他,就代我问候一声。别的,没了。”
我停止了故事,一个人喝了一口酒,说:“这次到淮县来,一点理由都没有,但就是来了。我总觉得一定有些理由在推动着我。但那是什么呢?”我问大家。
黄部长说:“没有理由,就是理由!就像开明大师说的,缘吧!”
阿伊却站起来,端着杯子,说:“我敬刘老师一杯,为刚才那故事,也为那个要看说书的诗人!”说罢,没等我同意,她一饮而尽。我也端起杯子喝了,坐下后,我说:“明天,我还是想去听听大福寺的鼓书!”
5
一夜无梦,酒喝多了,黄部长打来电话时,我刚醒。他说上午陪我去找那个说书人。已经跟镇里联系了,我们上午直接到他家去。
我这才觉得有些过头了,真不该给县里添这个麻烦。我说不去了吧,太麻烦了。黄部长说:“不麻烦,也算是调研嘛,到镇里去,不仅仅是听鼓书,还可以了解下最基层的情况;何况鼓书本身也是非遗,是弘扬传统文化。一定得去,我还特地请了阿伊过来陪你。”
我也不好再推辞,何况我心里其实还是想去的,总觉得去了才踏实。下楼坐上车子后,阿伊说:“昨天晚上失礼了。我有些激动,所以多喝了点。刘老师说到那个跑到青桐的诗人,使我想起了一些人和事。”
“很好啊。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所以有共鸣。我是真不能喝了,不然,我还得再敬你一杯。”我说。
黄部长说:“我拉着阿伊过来陪你,一是她愿意,二是她跟这说鼓书的人有段渊源。”他回头望了下阿伊。阿伊说:“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但说无妨。何况过去了的,总是美好的。”
“就是。过去了的,总是美好的。”黄部长说,“大福寺那个说鼓书的,其实以前也是个诗人。80年代时,他是淮城写得最好的诗人,先锋,有思想,有激情。他本来有个正式工作,在县供销社上班。但后来因为写诗,到处跑,就像刘老师说到的那个诗人,天南海北地去念诗,交流。班也不好好上,一次,两次,最后被除名了。他没班上以后,更是跑得没影子了。也就是那几年,他还在上班写诗的时候,有很多文学女青年喜欢他。阿伊是最后的胜利者。阿伊,是吧?”
阿伊说:“不是胜利者,是失败者。”
黄部长说:“无所谓胜利和失败,经历过了,就是美好。”
我问:“后来呢?”
“后来,就说到大鼓书了。大概在90年代初,消失了一两年的他突然回到了淮城。不过,他眼睛出问题了。原来那双明亮得像孩童一样的诗意的大眼睛,变得云遮雾绕,基本看不见了。”黄部长摸着秃顶,说:“也不是一点看不见,还透着点光。但基本是看不见了。”
“病了?还是?”我又问。
“不太清楚。看起来像是病了。阿伊,这事,你应该清楚。”黄部长说。
阿伊说:“这事,我先还真不清楚。有一年,也就是他消失前的大半年,他从外地转了一圈回来,人整个就变了样。整天闷在屋子里疯狂地写诗,写爱情诗。但都不是献给我的。我看过一些,都是献给一个女人的。可以肯定的是,那女人不在淮城。他一首接一首地写,每写一首,我跟他的距离就拉大了一寸。后来我们就分了。分了后,他就消失了。再回来,眼睛坏了。我先也不知道,是他到我们医院就诊,医生问他眼睛怎么就坏了,他先是不说。问到最后,医生说你不说出原因,我们怎么治?你再不说,干脆回去算了。他这才说是松香熏的。”
“熏的?松香?”我一颤。
阿伊继续说:“医生很惊讶。我当时在边上听了更是惊讶。一个人,怎么好端端地要用松香熏眼睛,而且还把眼睛给熏坏了?医生再问,他就不说了。最后竟然生气说大不了不治了,这人世间不看也好。医生也无奈,后来还是没治好。用了很多药,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行。再后来,他就跟人学说鼓书了。”
我问:“那他还写诗不?”
“不知道。反正再没见他发表过。后来也没参加过任何淮城的文学活动。他就待在大福寺里,天天说鼓书。每天那么多人听他说鼓书,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他还曾经是个出名的先锋诗人。”阿伊有些感伤,“我偶尔也过去看看,听听,但从不惊动他。我觉得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鼓书世界?或许还有诗?”
“都有。都没有。”黄部长说。
我刚才一颤的心,又颤了一下。
车子很快就到了镇里,其实离大福寺不远,估计也就十来里路。镇上人早在等着了,说说书人的家就在镇子边上,原来是老房子,前几年成了危房。说书人也不维修,还是镇里从危房改造资金中拿了些钱,给他重新起了三间屋。屋里就说书人一个人,他一直没有成家。这些年,他每天在大福寺说书,听的人成千上万,他从不收费。但凡有一点经济头脑,每个人收个一块两块,也早不是现在这样了。看得出来,镇里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我就问镇里人现在这说书人的眼睛到底怎样了?
镇里人说大概还有一粒米的光亮。平时都拄个棍子,吃低保。在寺里说书时,寺里给他吃斋饭。
镇子上现在也没什么人,到处都没什么人。我们车子只开了五分钟不到,就看见一排三间的平房。镇上人说:“到了。门掩着,也许在家。”
黄部长说:“那是在等刘老师。”
我心里却突然空了一下,跟刚才的颤了一下不同,这回,是空了一下,有些下坠,茫茫的,虚空得很。
镇上人带头,在门口叫着:“说书人,说书人。”里面没有应答。他们推开门,屋内很整洁,空荡荡的,只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旁边一张矮桌子上,放着电饭煲、水壶,还有几个瓷碗。不过,上面也落了些灰尘,应该是有几天没用了。左边的房间是厨房,更简单,除了一只一个火头的燃气灶,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黄部长说:“这才是极简主义。啥都没了。”
镇上人说:“这都是镇里给添置的,不过,他好像基本不用。他都是在寺里吃饭,偶尔带点回家。一个人,过日子就是凑合。”
阿伊特地跑到燃气灶前,拧了下,没出火。她过去摇摇燃气罐,空的。她愣在那儿,直到黄部长喊她,她才转过头。我看见她悄悄擦了下眼睛。我也不说。大家又到另外一间屋子,一看就是卧室。还是简单,一张木床,有些古旧,还挂着蚊帐,所以看不清床上设施。镇上人上去撩了下,没人。靠窗有张桌子,边上还有一张条桌。条桌上放着一些书,我随手一翻,大都是些诗集,随着翻动,灰尘从书页间掉落,在透过窗子照射进的阳光中,变幻不定。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书页里没有灰尘,应该是经常翻阅。还有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这蓝色封皮,让我感觉亲切。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颜色,那是大海的颜色,是诗歌的颜色,也是我们记忆和怀念中的颜色。我用手摩挲着笔记本,打开,扉页上,写着一行字:
松香一样迷离。
我的手那一刻像被钉在了那一行字上。其他人都在说说笑笑,阿伊站在门边上,神情复杂地沉默着。也许,这就是我要到淮城来的理由吧?我将笔记本合上,放到原来的位置。那位置其实是一方浅浅的灰印。笔记本放进去,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正好。
有人进来说:“刚问了邻居,说书人出远门了,走了十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