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5年第9期|郭爽:留籽(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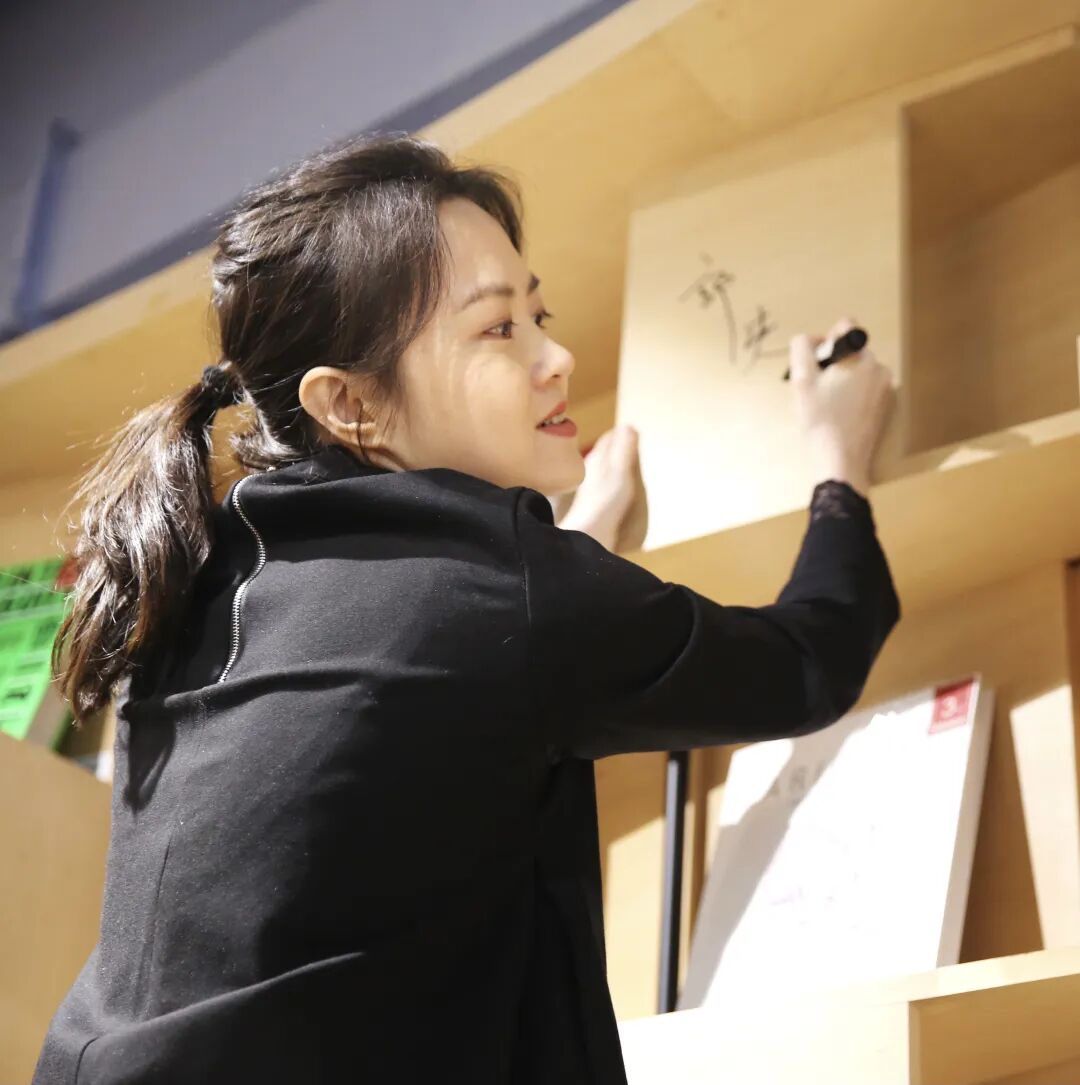
郭爽,一九八四年生于贵州。作品发表于《收获》《作家》《山花》《钟山》《西湖》等杂志,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刊选载。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新人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金短篇”小说奖、山花双年奖·新人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留籽(节选)
郭 爽
窗帘还是灰蓝色,天也就还未亮。这时节太阳出得早,偶尔老彭睁开眼,窗帘被天光映成淡蓝色,他就知道算睡了个好觉。年岁大了,瞌睡慢慢变少,醒来时是半夜也不慌,躺着不动,多半又能盹过去了。他闭上眼,想着还早呢,再睡会儿吧,可不知怎的,就想起平平说她胃不舒服。这个月她说两次了。老彭睁开眼,伸手摸床头的电子钟,液晶屏上显示五点三十六,星期日。龙蛇马羊猴鸡狗,星期一到星期天各乡镇都有场可赶,但星期天在花鸟市场的场最大。他想起刺梨来。准确地说,是晒干的野生刺梨根。寄去让平平煮水喝,喝上十天半个月,肠胃再是什么毛病也好了。他边想边掀开被子,身子往右侧倒了一半停住了。平平的话像是在耳边:“爸爸,听医生的话,晓不晓得?”于是,他忍耐着,一刻钟,两刻钟……直到美丽的晨光从窗帘缝透进来,在两扇窗帘的淡蓝色中间拉出一条粉白色的光带。老彭不知不觉微笑着。十几年不碰刺梨了,但他觉得自己定是能认出刺梨根来,切成片、晒干了、变色了,也能认出来。他有信心。他翻身下床。
“老彭,老彭!”有人从远处喊他。他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又看,不知是不是眼睛又出什么毛病了。他站定,等那个声音再喊。一把红色大阳伞下,一个胖男子左手端碗,右手筷子悬空。他往红伞下面走去,等走近了,胖男子说:“吃过没有?”是老郜。
“几点了,你吃二顿啊?”老彭看老郜碗里的牛杂粉。汤底红、芫荽绿,油滋滋的喷香。
“老板,牛杂粉一碗,小碗。”老郜自作主张给老彭要了一碗。
“今天怕是要超标了。”老彭说。
“天天整你那个粗粮健康餐,偶尔也改善改善嘛。”老郜从老板手里接过新的一碗,递给老彭。
两人面对面坐在大红阳伞下的小木桌子边,窸窸窣窣吃起来。米粉白、滑溜,吸饱了汤汁,热乎乎地滑进老彭嘴里,三两口之后,他额头、后背微微出汗了。若是从前,老彭捞完米粉,汤也要喝掉大半,今天却不同,剩一碗汤摆在桌上。他歇口气,看老郜继续战斗,直到空碗哐地落在桌面上。老郜抬头抹把汗说,可以,这味道可以。
太阳升高了些。阳伞下,两人的白头、略微佝偻的背影被映得红彤彤的。五十岁前后,两人都戒了烟,也就没有赖在这里消磨时间的借口。老板慢悠悠送客道,慢走啊,两位老人家。
两位老人家挤进赶场的人流之中,在油饼摊、炒货摊及蔬菜瓜果、锅碗瓢盆、猪牛羊肉档的各种颜色气味和吆喝声中悠然向前。集市摊档沿路摆出的长龙蜿蜒不见尽头,苍黑的山浮于人潮之上,云朵在山腰处游弋,阳光把云镀上一层珍珠贝母的光泽。山也好,天空也好,云朵也好,既远又近,既古老又如这崭新一天般静静地庇佑着小城和它的全部居民。
“拆针没有?”老郜问道。
“这次不用拆针。”老彭说。
“我记得你上次取出来那十几二十颗石头,放在一个瓶子里头。”
“取结石,挨一刀不说,缝针、拆针……还要留院观察。这次这个支架,小东西,放进去,指标正常就出院了。”
“科学进步快。等我再老些,装个机械手臂,那炒起菜来才过瘾哟。”
“你都装机械手了,还操心炒菜的事!郜新民,出息啊你。”老彭一边说笑,一边打量草药摊和摆卖的药材。
“不行啊?装了机械手就不吃饭了啊?科技再进步,人还不是要吃饭!”
不等老郜说完,老彭三步并两步往一个摊贩身前挤,指着摊贩手中的麻袋问道:“是不是刺梨根?”
跟其他草药摊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药材成堆摆放不同,这个摊贩面前只三个麻袋。其中一袋粉而白的切片,是葛根。另外两袋切片切面小、质地硬。老彭伸手分别探进两只口袋,抓取、闻味、辨色。确实是刺梨根。老彭的舌根处隐隐涌出甘甜的津液。刺梨根的淡淡芬芳激活了他的身体记忆。刺梨根加水煮至汤底澄黄,趁热服用,口腔、胃都会被它独特的气味激活继而舒缓,余留绵长的清爽与甘香。三十多年前,不对,已经是四十年前了,下乡落下病根后,他经常胃疼,吹了冷风就拉肚子。刺梨根的方子是陶勇妈妈给他的。陶勇妈妈说,毛,你每天熬一道,一次喝完可以,分几次喝也可以,坚持半个月一个月。他妈妈怎么认得这些山野药材呢?当时他没仔细想,只按她说的照做,竟是好了,肠胃像换了一副。一眨眼,陶勇妈妈走了十几年了,连陶勇都走了七八年了。老彭不忍再想,抓起麻袋掂了掂重量。
老郜先他一步,问道:“咋卖?”
摊贩像是不知道怎么要价,嘟囔着现在不好找这野生的,原先田埂、路边常见,如今修路硬化路面铲掉杂草,这东西就见不着了。又说,这不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新品种膨大,他这个不好挖,硬得很哪。
“咋卖嘛?”老彭问。
摊贩下决心似的,“十块钱一斤!”
老郜拽他袖子,“走走走!十块钱一斤,没听说过。”
老彭本想讨价还价一番,老郜拉得猛、力气大,他身子偏了一下,也就跟着往前走了。
两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从南到北走通了集市。老郜从一个挑挑子卖鱼的老人手里买下一条大鲢鱼,说是今晚有人预订了一桌宴席,菜老早就点好了,主打的是他的拿手菜炝锅鱼。老顾客,老熟人,肯定要选条漂亮鱼啊。这种鱼跟养殖的不一样,养殖的都是些吃饲料的笨蛋鱼。这种鱼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生命力强!
老彭看老郜小心翼翼提着鱼嘴上的绳子,生怕他这条大鲢鱼被人碰着了,就说:“你先回,我去把那袋刺梨根买了。这都走通了,也没看见第二个卖的。”
老郜想了想,说:“那我先把鱼提回铺子去。你拿不拿得动?”
老彭嘴张开迟疑几秒后咬定:“一袋就五斤,两袋最多十斤,只是看起来多,轻得很哪。”
“买这么多啊?”
“寄给平平。”
“给平平买?那我去买。我去我去。”老郜一只手举高了鱼,生怕鱼被人和人身上的背篼撞上,一只手拉扯老彭。
“哎哎,不用你去。”老彭拧住他胳膊往回扯。
“还要去寄的嘛。你那附近又没有快递站。”
“不用,我打电话喊快递员上门。多几块钱的事。”老彭坚持道。
“那你随时喊我,明天我都没事。”老郜说完,转头都准备走了,又神神秘秘地往老彭身边凑,“清了!我说,我债都清了!上月底最后两千块钱一还,哎哟,周身舒坦!”
凑这么近,老彭才看清楚老郜额头上那条疤。十几年前一天夜里,他们两个吃烧烤、喝啤酒,醉了醉了,一个还坚持送另一个回家。兜来转去,老彭准备横穿马路时从人行道边缘一脚踩空,摔了下去,老郜想要拉他,却不知怎的被他绊住,也摔了下去,正正砸在老彭背上。这一摔,老彭断了锁骨,老郜破了额头,一个打三颗钢钉,一个缝十二针。说起来是笑话了,没想到老郜额头上的疤还这么清晰。
“抻抻展展过几年。”老彭说。
“啊?”老郜没听清。这个老家伙,耳朵越来越背了。
“我说,你快点回去把鱼收拾了。”
“要得要得。我给你留得有点好茶叶……”老郜今天心情好,话也多得很。
两人又往来几句。老郜说,流行的口味来得快去得快,年轻人嘴馋、贪新鲜,只要新开个馆子就去凑热闹,但吃来吃去,总归还不是要早起一碗粉?还不是要吃回这家常菜的老味道?老郜说,积累积累,盘点盘点,他要把这老字号“打造”起来,别的不说,炝锅鱼家家会做,只有他做出了融合口味,吃过的都说好,说有特色。做餐饮,你有一两道菜做出创意,做得不一样,才有江湖地位。
老彭听老郜说着、笑着,有一秒钟,他觉得老郜走霉运的日子尽了,该是好日子来了。
最终,两人分头走开。两个白头在明晃晃的日光下,闪闪亮地走远。
老郜咋就缩水了呢,脸小了一圈,皱巴巴地缩在被子后面。
老彭喊,老郜,老郜,起来吃牛肉了。新鲜宰杀的黄牛,清炖,安逸得很,快起来,汤要趁热喝。
老郜的嘴在氧气罩下紧闭,像有什么东西哽在舌根处。
老彭又喊,你给我留的茶叶呢?我还等你一起去接山泉水回来泡茶呢。
老郜双手僵直,食肉恐龙一般蜷缩在胸前。
老郜床边的监测仪显示屏上,两条绿色的波动线代表他的心脏跳动节律,红色曲线是血压,最下面黄色那条代表他的呼吸。老彭凝神看三色曲线和曲线旁边的数据,又喊了几声,老郜仍没有回应。他抑制住情绪,抬头望向站在床对面的牛牛。牛牛双眼肿着,脸颊不知怎的凹了一大块儿,看着竟比平日更像老郜了。
该说的都跟彭伯伯说过了。
昨天晚上,老郜给那桌老顾客好好露了一手。炝锅鱼相当成功,辣子鸡和干锅牛肉也品质稳定,两道新菜野生菌豆腐肉丸煲、傣味烤肉串拼盘也都“光盘”了。老郜在后厨忙完,还去跟老熟人们闷了两杯。结账时他给抹了零,坚持只收三百八十元。客人们吃得满面红光,站在路边你送我我送你谦让了一阵,才各自坐车走了。老郜靠在门口的旧竹椅上,看街对面的一排商铺渐次关灯、拉闸,自家铺子里两位小工拖完地、擦完桌子、把潲水桶推到指定位置。夜静下来了。他关灯、锁门,哼着歌往家走。到家,妻子儿子都在,吹着电扇听他讲这晚上如何成功。老郜说得兴起,又倒了一杯白酒,就着花生米在客厅里自己喝起来。牛牛明天七点要去督工,先回自己住处去了。妻子孙晓娟跟他看了一会儿电视剧,说累了,就去床上躺着玩手机。后半夜,孙晓娟起夜,发现身边没人,走出卧室,卫生间的灯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她喊两声,老郜、老郜,里面没反应。她拧开门,老郜歪倒半坐在卫生间地板上,鼻孔、耳朵流出的血顺着脖子、胸口往下走。他那件满是孔洞的白汗衫,下半截整个染红了。
眼前,老彭见到的老郜,身上已不见血迹。不只不见血迹,老郜的头发给剃光了,衣服全剪掉,被单下打着光胴胴。他给清理得很干净了。
“咋剃了头呢?”老彭转向孙晓娟问道。
“护士说先准备好,要开颅的话,就方便些。”她边说边伸手摸了摸老郜光秃秃的脑袋,又顺着他脑袋往下,轻轻抚摸这做了四十多年夫妻的男人的耳朵,“咋理得这么难看?他脑壳本身就小,这成个什么样子?”孙晓娟忽地笑了,眼泪淌过皱纹丛生的眼角,大颗大颗打在老郜的被单上。她抓起老郜的手,硬是把自己的手指挤进老郜僵直、蜷缩的手里,左手轻轻抚摸老郜的胸口,凑到他耳边说:“醒啊!醒了啊!郜新民,我是孙晓娟啊。来,你儿子在这里。你儿子牛牛啊。我们要接你回家。醒啊!醒了啊!”
医生没跟孙晓娟和牛牛说的话,跟老彭说了。开颅已经没有意义。出血量太大,发现得太晚。让他清清静静走吧。
老彭没想好怎么跟孙晓娟和牛牛交代。从医生办公室到老郜的病房,步子再慢,三五分钟也走到了。走到门口,他站着不动。门拉开了,孙晓娟夺门而出。两人各退半步。孙晓娟看清是他,说:“不做手术,我们不做。我正要去找你,去跟医生讲,不做了。”
老彭怔怔道:“不做啊?”
孙晓娟声音颤抖着说:“郜家人还不来。他们来了我也是这句话,不开颅,放弃治疗。人没给我保住,就给我好好地、完完整整地走。”
老彭听孙晓娟又说了几句,假装接电话,走出病房,走进长长的走廊,不坐电梯,一口气走下六楼,在医院的喷水池边绕圈圈。直到他发现六号楼边上有条小路通向医院后山半山腰的亭子,才顺着台阶爬上去。他换步太快、太急,还没爬到亭子,胸口那压着的铅块就崩解了。他双腿打抖,身子弯折向前,两只手撑在大腿上,竟发不出声音来,只有些他自己也没听过的、低低的哀号。
当晚八点十七分,彭宥年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他女儿平平的干爹、他的好朋友郜新民走了。享寿六十有六。
一九九三年,彭宥年三十七岁,离婚五年,带着女儿平平过活。七月份,不知怎么搞的,才过一半,他就没钱了。他妈陪着他爸在外地疗养,他不能去烦他们。况且,如果他跟他们开了口,就应了那些老辈子的话——他一个人带姑娘怎么行?里里外外……还是快点找个媳妇!男人可不能一个人过活!他生平第一次决定借钱。陶勇挣得多,但龚玉莹凶得很,找他估计也是白找。郜新民呢?可能没多少钱,但孙晓娟好说话些。他反反复复想,走到郜新民家附近又走回来。走到第二趟还是第三趟的时候,在自家楼下,他迎头差点撞上人。一看,这风风火火的,不是郜新民是哪个?
两个人像是心有灵犀,一前一后开始爬楼,爬上三楼,左边户就是彭宥年家。放暑假,平平去少年宫学美术了。郜新民往沙发上一坐,掏烟出来。彭宥年提起暖壶摇了摇,将就着半壶上午烧的开水,给两人各泡了一杯毛峰。
“你是不是懂相面?你看看我,我是不是多子多孙的相?嘿,跟你说,我又要当爹了。”老郜喜笑颜开。
“是不是哦?”
“孙晓娟怀起了。”
“是不是哦?”
“瓜婆娘还不好意思得很,喊我不要到处乱说。”
“三个月以内是不好到处说。”
“好事不怕出门!”
“也是。”
“就是。再说,我怕哪样?警告我处分我开除我?我几年不领工资不端铁饭碗……大不了罚我款。”
“你打定主意了?留这个娃娃?”
老郜沉默了一会儿,“是姑娘还好点,就怕是个儿。”
“你讲反了吧?我以为你就等个儿来供起哦!”
“我是那种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儿子的超生游击队?”
“我看是。”
老郜笑了,“姑娘好啊。万一是个儿,多个讨债的,屋头再多钱都挡不住被他糟蹋。”
“你咋晓得是来讨债的,就不能是来报恩的啊?”
“哼,你龟儿子没当过儿啊?装,你装。”
“添双筷子的事。”
“你倒反过来劝我了。”
“都是顺着你说。娃娃啊,来了就来了,来了就接住,接住就养活,养大了撵出门去……”
“要真是这样就好咯……”
这天,两人喝了好些散装白酒。说到后面,老郜说,要是哪天我不在了、先走了,彭宥年,我这两个娃娃,就只能拜托你了。孙晓娟是妈,她跑不脱。但你要管,你管,行不行?
老郜一开始耍横、乱说话,多半就是醉了。彭宥年答应他说,你放心,郜新民,平平有的,晶晶就有。我没钱我卖血去。
第二天一早,彭宥年在厨房给平平做早餐,听见有人咚咚咚地敲门。孙晓娟站在门外。她递给彭宥年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这么早银行还没开门,怕他着急,就把铺子里面的钱清点了给他送来。彭宥年三只指头撑开信封口一看,里面十元五元的纸币叠成整齐的一沓。彭宥年要留孙晓娟吃早餐,正说着,平平走来门口。孙晓娟伸手摸摸平平的头说,走,干妈带你去看展销会。那天平平回家后很兴奋,她给爸爸看干妈给她买的发箍,说粉红色的全场就这一个呢。彭宥年给平平戴上说,我姑娘就是漂亮。
一九九三年那会儿,小城没有汉堡店,没有健身房,电影院还在,但小家庭们热衷于拥有自己的音响系统、卡拉OK和家庭影院。人们在朴素的惯性中感到自己对新生活的需求,但没人轻易妄想拥有自己的手机、电脑和小汽车。当然更没有人妄想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郜新民算相当出格。不过,在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上,出格并没有什么用处。他的手艺是家传的。郜家世代做餐饮,新中国成立后郜氏父子就去国营饭店和宾馆掌勺。没有私营餐馆的几十年,老郜家没分家,一旦放开,要重新做起生意来,反而分了。同是家常菜馆,分出来的三支像是彼此避忌,各占城东、城南、城北地带,不仅互不往来,久而久之连菜式都认不出是源自同一家老号了。郜新民继承的这一支,属于记性好的市民口中“正宗的”“不乱来的”。郜新民前半生的三十六年里,都在他父亲定下的规矩中老实过活,先在国营宾馆的餐厅学厨,然后评职称、当厨师。直到他父亲百年作古,他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按自己意思来,开馆子、换新菜、走江湖。不为什么,他只是想证明,他凭本事吃饭,能养活老婆娃娃。在这个偏远的小城,生存从来是不容易的。而人,还得活一口气,还得活给旁人看看,就更艰辛。老郜坚持要第二个娃娃,是不是赌一口气,没有人知道。一旦超生,他停薪留职的那份国营宾馆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出来开馆子、卖牛仔裤、开酒吧、拉白酒去外省卖的人都有,但没听说谁就把工作打脱了的。郜新民是第一个。从此以后,这个矮小、敦实、其貌不扬的餐馆老板,被人提到时就多了些说法,不再局限于老郜的手艺,而是在人人都只有一个后代的环境里,他竟然拥有一儿一女!没有这件事,老郜原本是不会进入那些人的话题里的。这辈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兄弟姊妹一堆,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承认,他们其实是盼望多子多孙的。
自己有没有想过多子多孙这回事,彭宥年不记得了。那时候,他负责的“刺梨601”开始在全省海拔七百米到一千七百米之间的地区试验生产。“601”是本省培育的刺梨品种,三十年前,彭宥年的老师盛怀廉跟四位同事在铜仁地区调研时,发现一株丰产、果大的野生刺梨单株,挖其根带回农学院,经扦插繁殖后,在省内不同土质、海拔、气候的生态区域经过长期人工驯化,成功培育出生物学及经济性状稳定的新品种。在正式命名为“601”前,盛老师退休,彭宥年接过盛老师衣钵,成为第三代“刺梨人”。
彭宥年侍弄刺梨,懂得了刺梨的性情。刺梨树喜丛生,不喜强光,耐旱不耐寒。不仅果实上长满软刺,枝条上也遍布密密麻麻的褐色小刺,扎手,不讨喜。他把刺梨的优点牢记于心:维生素C之王,维C含量是柠檬的一百倍、苹果的五百倍。他懂得刺梨是好东西,但也知道它其貌不扬、口感不佳。人人忙着赚大钱、争上游、跳舞唱歌,吃得油、吃得精、吃得甜,他们能不能接受刺梨?他拿不准。
出路还没眉目,农户那边就先甩手不干了。农户不愿意种这东西。村支书、村主任带头引种,自家土地都拿来种刺梨,也打消不了农户的怀疑。跟同批推广种植的花椒、薏仁、魔芋甚至药材相比,刺梨接受度最低。将心比心,彭宥年能理解农户的顾虑——种了卖不出去,花椒、薏仁、魔芋、药材都能自家吃、送亲朋,又丑又酸又涩的刺梨,烂在手里吗?!家家户户的土地、人力都有限,蚀本就没饭吃,没饭吃就是等死。谁也担不起这后果。只是,如果真走到这一步,不只是他和老师们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601”要失败,也是“601”所意味的另一条道路被判失败——本土作物的保育与改良、土地种植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复合化。
彭宥年找到在深圳混出名堂的好朋友陶勇,请他帮忙联系广东的企业。他想登门拜访,亲自了解农产品工业化的路子。那时候的思路多半如此,要打破旧,就要走新路子,而工业化生产就是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促进消费的新路子。彭宥年坐火车南下广东。车厢里,他这样三十来岁、拎着一袋文件的人不少。他邻座就是一位杂志社的主编,说是去广东拉赞助,想办法把杂志盘活,“光是印刷费、稿费,每季度硬支出就十几万。等财政拨款?等到什么时候?”他跟这位姓郑的主编互留了电话号码。虽然并不确定这样去寻出路到底能不能有出路,但遇见同路人,总有几分安慰。等真到了广东,去食品企业、批发市场转一圈下来,彭宥年在笔记本上写下:刺梨蜜饯、刺梨可乐、刺梨软糖、刺梨口香糖、刺梨雪糕……几乎每一样产品都需要一条生产线。
彭宥年常年打交道的是农作物、泥土、书本,他不懂得钱生钱的道理。调研回来的报告写了又写,钱却是一直不到位。多亏遇到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方小鸣。方小鸣从省里面下来黔南挂职,知道黔南几片用来试种“5号”的土地,是全省为数不多符合“601”种植条件的地块,就抓得紧。他承诺给农户补贴到户,还承诺收果子时从运输公司专门调车队,保证把果子运出去。
“601”的树苗这才种下,都在方小鸣所管辖的农业试验区。
树苗种下的那个冬天,彭宥年与前妻办完了离婚手续。他带女儿平平一趟趟地坐长途车去黔南看那漫山遍野的“601”。每次去,“601”都蹿高许多。这片水土太相宜。一年,两年……等平平学会给自己和彭宥年收拾洗漱包、坐乡村中巴不再呕吐时,“601”开始挂果。
首批果子从下枝、装袋到运送至农学院的加工厂,没有超过两天。以当时的路况和人力,算是快得不得了。方小鸣还在任,还在督管此事。这个言出必行的县委副书记,多年后以正厅级待遇平安退休,时间证明了他的能力和操守。
“601”是吉祥的果子。生产试验阶段小小的波折过后,第一年就大丰收。接下来就是进加工厂、上生产线、包装、上市。说是加工厂,其实是陶勇牵头,彭宥年、郜新民入股的一条生产线。厂房是彭宥年跟学校借的,借的时候写了承诺书:保证生产,完成嘱托。机器是陶勇从广东租回来的。食品安全等各种执照和证件,是郜新民跑去办下来的。
彭宥年这辈子第一次做生意,也是唯一一次做生意,就是这回,用丰产的“601”生产刺梨可乐。说是刺梨可乐,其实是刺梨原汁打底的碳酸饮料。农学院里也有其他食品生产线,老牌子的酸奶、牛奶不说,果汁、果酒都是有的。以往彭宥年只管育种育苗的事,现在自己的“娃娃”落地要上市,也就四处请教各位老师、同事。老师们给他打气,说不着急,小彭,你就想,等于是实验室放大十倍,安全生产,是不是就这个道理?酸奶厂的副厂长跟他说,只要能抓住娃娃和当妈的,就稳了!学校门口、游乐场门口、公园门口的所有小摊档,各个街道的小卖部,人家卖五角,你卖三角!外包装颜色要鲜艳!取经取了一圈,他也就不担心了。人人都在往热腾腾的海里跳!
原料、生产线、校工、包装都已到位,就差个名字。该叫个什么名字呢?郜新民说,叫“三兄弟”。陶勇说,已经有个土豆片叫“兄弟”了。那叫什么,郜新民说,三姐妹?三人笑。另外两人骂郜新民说,咋不叫三只小猪、三套车、三国演义、三个臭皮匠呢?说说笑笑。后面,彭宥年说,就叫“三个刺梨”吧!他起调,按《两只老虎》的旋律唱道:“三个刺梨,三个刺梨,跑得快!跑得快!”郜新民说好,举手表决。三人举手,全票通过。
那时候,一件商品要流行开,有两种手段:上电视打广告和小城居民口口相传。郜新民请电视台扛摄像机的王小彦拍了一条小广告,又请电视台的老同学、老朋友来自家馆子里吃了三五顿。这条广告以最低价贴在了本地新闻后面播放。广告里面,三个少先队员和一个咿呀学话的胖娃娃都在喝“三个刺梨”。三个少先队员分别是彭宥年的女儿彭平平、郜新民的女儿郜晶晶、陶勇的儿子陶为嘉。胖娃娃也不是外人,就是郜新民的儿子郜牛牛。拍广告那天,三个大孩子一见面就屋里屋外地跑、尖叫。牛牛还不会跑,老实待在自己爸爸身边。老郜只用看管这么一个娃娃,心情很轻松。他听王小彦和王小彦的同事们在商量:先拍三个娃娃喝饮料,然后拍饮料瓶,最后拍牛牛。牛牛伸出三根手指,这不就是三个刺梨?老郜频频点头。
广告确实有效果。王小彦的创意得到了市民的认可,伸出三根手指比画出OK的手势风行一时。“三个刺梨”销得好,牛牛成了明星。
郜新民之前就打了包票:全城大大小小饭馆、食堂,他郜新民说得上话的地方,都上架、展示、促销。先从他自家的饭馆做起,每桌免费赠送一瓶。随着广告效应扩散,牛牛的海报成了招牌。郜新民很满意,跟陶勇说外省销不动就算了,能拢住本地顾客,这生意也能做下去!陶勇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人的口味说变就变,还是要出去跑、想办法。陶勇回广东前,给三个娃娃一人一条牛仔裤,给牛牛两袋含DHA的进口奶粉,还专门交代孙晓娟说,早晚各一杯。孙晓娟接过奶粉,看了看坐在地上玩积木的牛牛,说,跑是会跑了,就怕是个哑巴。彭宥年说,这娃娃肯定不笨,你看,从我们来到现在,他玩积木可以玩一个小时。他专注。可能是个慢性子,说话晚。
在不会说话和后面漫长的磕磕巴巴学说话的日子里,牛牛记住了眼前的世界:街道铺的是水泥,所以是灰白色,阳光猛烈时是明晃晃的白色。街道两旁种植的是悬铃木,所以树干是剥落、斑驳的灰色,树叶夏天绿秋天黄,飘絮时是淡黄色。街道上并不拥堵的小汽车是黑色、白色和灰色,出租车是绿色。刚流行起来的铝合金玻璃窗是茶褐色,后面又流行钴蓝色。孩子们的校服是蓝白绿三色,红领巾是红色。大人们的衬衫是白色,的确良裤子是灰色,梦特娇裤子是黑色和咖啡色。除了这些立体的色块,牛牛能看见空气里的灰尘躁动、闪亮。灰尘们头角峥嵘、数目可数,大概因为整个世界的布景都水洗般初生、明净。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