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扎根泥土,眺望时代“尖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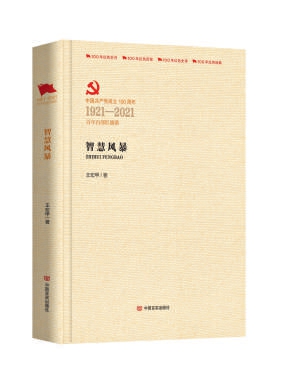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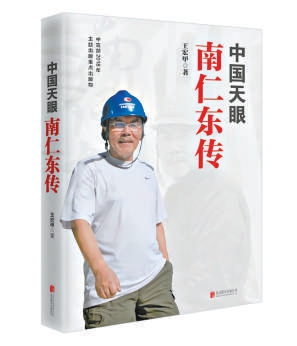

今年9月开学时,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里,悄然多了一颗“星”——《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篇课文为师生推开两重动人天地:一是500米口径的“中国天眼”正以人类“最亮的眼睛”凝望星空;一是人民科学家南仁东深植于他热爱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字里行间流淌的,是科学家把一生熔进国之重器的赤诚,亦是一位作家脚踏大地、打捞星光的热忱——他便是王宏甲。
若说文字是王宏甲的罗盘,这罗盘始终朝着“人”与“时代”的方向。多年来,他像个“用脚写作的行者”,带着泥土的温度,在教育、科技、乡村的原野上穿行。
回望他最初的“文学课堂”,是下乡插队时的茅屋和田埂。他曾说“科学主理,文学主情”,对他影响最大的群体就是农民。他把心贴在人民的悲欢里,把目光落在时代前沿,一深一浅间,写就属于他的、更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长卷。
1.
乡村八年种下文学的“根”
王宏甲在他的散文集《让自己诞生》里有一篇《你统治了我的一生》。他说这个“你”,是农民。“他们教会我的,不只是生存本领,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真诚。这些东西,影响了我的一辈子,也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根。”
1969年1月,15岁半的王宏甲到闽北山区插队,那个叫火爬山的村子共14户人家,他是第14户。生产队把原来放肥料的茅草屋清理出来,就算是他的住处。“下雨的时候,茅草屋漏雨,锅上要撑起伞。”
刚到村里时,他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他砍的柴火总是湿的,烧不着,农民拿来松明放在他的湿柴火下面,才把他那湿湿的柴火烧着了。他说农民对他的帮助几乎无处不在。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作为土地,是谁把我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
他说当年如果自己插队五六年就被调走了,会认为自己是知青。“但是,插队到第七年,我认为我是农民了。到第八年,更认为我是农民。”在插队第八年的冬天,他被招工走了。离开村子的时候,队长、邻居都来送他。
有人说:“你出头了。”有人问:“你还会来看我们吗?”
多年后,他真的回村去看望乡亲们。“重返故地,看到农民们牵衣执手,把我视如探家的儿子,我的泪水就像种子那样,掉进我曾经种过的土地。”
插队生活对他的哺育和影响,都是巨大的。他在离开村庄后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是在离开乡村之后才知道,泥泞的日子,并不只是乡村才有。这时刻,房东大嫂的一句话就像开启深埋地下的陈年老酒,送来无限滋味:别怕,把裤腿挽高一点。”
他说自己总想,大嫂和那些少女们能把腿踩进污泥,也能把腿洗得那么白净。谁能说那里没有美和生活智慧呢!
他还在一篇散文《1969年的白菜》里写下:“我在那八年岁月里至少培养了吃苦能力,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如果没有吃苦能力,生活就会是一堆悲伤,会沉溺在抱怨中唉声叹气一事无成,这就体会不到克服困难的喜悦。人生的困难是始终与生命同在的,克服困难收获喜悦才是人生的常态,是人生的大意义。我会郑重地告诉我的子孙后代,我的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说自己日后作品里最深的情感,是农民哺育的。笔者相信那是真的。
2.
从初一文化到报告文学探路者
1976年底,王宏甲结束八年的插队生活招工回城。此时的他,论学历,仍然只有去插队之前读过初一的文化。他去新华书店买来两元钱一本的《逻辑》《修辞》等,自己给自己补课。
刚回城时,王宏甲被分到冷冻厂当搬运工,后来被借调到商业局“以工代干”。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可他的文学底子太弱了:不知道何谓句子的主谓宾,不知道标点符号怎么用,更不知晓新闻稿要先写导语。可这些丝毫不妨碍他在文学之路蹒跚起步。县广播站的编辑手把手教他写导语,几乎帮他重新写了遍稿子,第二天还在广播里播出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写的故事’,后来还收到了三毛钱稿费,我把稿费单夹在书里,像宝贝一样。”
1979年,王宏甲迎来了自己第一个“真正的作品”——纪实作品《理发姑娘》。这是他从当时商业局搞岗位练兵现场发现的素材。后来,他又把《理发姑娘》改写成小说《大胡子恋爱记》,发表在《福建文学》上。“那时候,我觉得小说才是‘正经’文学,虽说现在看它很稚嫩,但对我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我知道,我能靠写作吃饭了。”
多年以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建阳,我的家乡》,开篇说:“写到家乡,我的笔就会温暖起来。我不知怎样来描述这种温暖给予我的恩惠,但我知道,我常因家乡而感到丰厚的拥有。”有人说,他对家乡的热爱,是“读者打开他作品的又一把钥匙”。
插队归来,王宏甲就为家乡建阳做过一件“打捞历史”的事——写自己的同乡宋慈。这位南宋法医学家撰写的《洗冤集录》被后世确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可是,《宋史》不见他的踪迹。清代《四库全书》对《洗冤集录》只在《总目提要》中存有“提要”,而对作者宋慈,则称“始末未详”。他在时空里被遗忘了。
“我遇到了宋慈。”王宏甲说,“虽然他已去世了七百多年,但生命中有一种奇境,你忽然感到心灵与之相撞,发出一种光亮,便不能失之交臂。”那年他25岁,“听到有个声音在叩我的心扉:你能用文学形式把宋慈写出来让天下皆知吗?”他说自己渺小的心被这个念头吓一跳,但接着就激动了。为什么不试一试?
他开启用脚步丈量文字的模式——到宋慈曾经任职的地方寻访,到《洗冤集录》的刻书地,查找元代的版本(宋代版本已失传),未果,后在图书馆终于找到一份手抄本(源自清代版本)。随后他又在图书馆查《宋史》《福建通志》,一点点拼接宋慈的生平。那时候没有电脑,查资料全靠手抄,王宏甲一头钻进文献大海里记了十几本笔记。他回忆:“写小说的时候,故事是虚构的,但里面的检验方法,全是从《洗冤集录》里来的——比如怎么判断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怎么通过伤口判断凶器,这些都是宋慈的智慧。”
1986年,小说《神验》(后修订为《宋慈大传》)出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泰、阿拉伯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1987年秋,王宏甲应邀出席在中国召开的首届国际法医学研讨会。会上,他讲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为什么出现在中国。
不为人知的是,王宏甲在写作过程中,却渐渐产生了困惑:“小说是虚构的,我虽然尽量贴近历史,但还是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我想写更真实的东西,写那些正在发生、能影响社会的事。”1987年,王宏甲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他在毕业论文《中国文学形式发展探究》里,写下一个重要判断:“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主流文学是纪实文学(也说报告文学)。”他的理由也充分——小说是虚构的,诗歌难以承载大的叙事,散文难承厚重的社会内容,而自《尚书》《左传》《史记》以来,文史相融的纪实文学在中国拥有极其悠久的文学传统。能真实反映时代的当代报告文学,不仅是文艺“轻骑兵”,还能担当“黄钟大吕”。
这个判断,成了他后来创作的“指南针”。“很多人讨论文学,只讲‘写作技巧’‘语言风格’,这些都是‘术’;真正重要的是‘道’——你的作品对社会有什么用?能给读者带来什么?能为时代留下什么?”带着这份思考,他的文学之路转向了报告文学。
3.
文学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
如果说“扎根泥土”让王宏甲的文字有了温度,那么“眺望时代”则让他的作品有了高度。他总能立于时代潮头,捕捉到那才露出的“尖尖角”——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齿轮时代”到“信息时代”,他用文字记录下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1998年,王宏甲先后接到两个任务:一是应北京大学邀请为北大百年校庆写一版文章《百年北大》,二是应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工委邀请,为北京市开展向王选学习的活动撰写一篇通讯。
“这是我极其重要的一个学习机遇。”王宏甲说,为什么说是“机遇”,而不是“机会”,因为“机遇”暗含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第二个任务,王宏甲感觉到了,自己正面对着巨大的陌生。
那时他还不知道,计算机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高效地将汉字输入电脑,是当时摆在国人面前的大难题。王宏甲说自己也不知道,西方已率先结束了活字印刷,采用电子照排技术。当代印刷技术已发生革命性变化,我国仍停留在铅印阶段,如何跟上世界步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王宏甲采访的不只是王选,还有许多位教授。许多个夜晚,他在北大某个办公室采访到十点钟,他和教授都没吃饭,各自回家。王宏甲说自己走在北大校门外的路灯下,就像一个到老师那里补完课后回家的学生。
“的确,我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了。”王宏甲说。
1998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宏甲撰写的长篇通讯《王选的选择》,全文一万多字,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学习王选的创新精神》,由此拉开全市开展向王选学习活动的序幕。此后《王选的选择》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全日制高中《语文》实验课本。
199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王宏甲写的三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初见端倪》。编辑部在《新年致辞》中写道:“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初见端倪》写科学家王选,会使读者想起二十年前在本刊第一期所发表的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是的,同为数学家,二十年前,《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与数论的神奇之光走进大众视野,激励过无数人;二十年后,王选的数学技术变成激光照排,在西方高技术的严酷包围中突出重围,使整个中国的排版印刷告别了铅印,从“铅与火”的工业时代,跨越到“光与电”的信息时代。
于是,王宏甲以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报告出什么是“跨越式发展”,写出典型的时代变迁。再后来,那三万字的种子,生长成三十万言的《智慧风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捧回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更乘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飘进了无数个深夜里的大学校园——没有电视的宿舍里,有人把音量调大,同学们都静静地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播,了解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正在风暴般地改变世界。
再后来,王宏甲创作《新教育风暴》,书中记录下中国一千多万教师带领三亿学生,从工业时代教育向信息时代新教育迈进的浩荡历程。这部作品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与鲁迅文学奖,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成长篇连播节目。
正是在这几次采写中,王宏甲深切地体会到,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也不在文学本身。
“文学只是一个载体,好比一条船,重要的不是这条船有多好,而是需要运用它去通往彼岸。文学的意义,在于能不能与人民同舟共济,呼吸相闻,唇齿相依。”他说,“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报告文学,可以将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多学科熔为一炉,去真实地反映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使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深邃的历史感,还具有前瞻性。”
4.
人们渴望能照亮前路的真实文字
深空里的“中国天眼”还在续写着观星的故事,它的设计者南仁东却在2017年与这片星空作别。
也是这一年,王宏甲接到中宣部的任务:写一部反映南仁东生平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当时,“中国天眼”已经建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天眼”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晓“天眼”之父南仁东。
曾经写出《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的王宏甲,如今再承担这一任务,已非偶然。只是,与当年面对面采访王选不同,这一次他已不可能当面向南仁东请教自己的知识盲区,他再次面对巨大的陌生。
这是又一部“用脚去跋涉出来”的纪实作品。王宏甲去了贵州平塘的大窝凼——“天眼”的建设现场。如今交通便利了,可当年南仁东和一众建设者到达这里之初,深山里没有公路,要靠柴刀劈出一条路才能进去;没有水,没有电,工人们只能住临时工棚。王宏甲到南仁东的同事、学生、亲友以及曾经居住在贵州大窝凼里的农民记忆中去“寻访南仁东”,看到南仁东就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心中,听他们讲“从省长到村干部都认得这个穿短裤的天文学家”。王宏甲深受感动,决心要为这位中国英雄立传。
王宏甲历时一年多写出了《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他说这部传记实际上包含着两大块:中国天眼和南仁东传,一如书名。而要真正认识到中国天眼的划时代意义,还应该了解两大背景:一是南仁东所处的现实环境,二是这项科研的历史文化背景。
于是,王宏甲没有停留在讲述南仁东的英雄壮举,而是把他置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20世纪结束时,美国305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被评为人类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25米,差距悬殊。南仁东说:“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
“天眼为何重要?”在书里,王宏甲从历史文化视角给出答案:天文学是人类最先触碰的自然科学——唯有仰观星辰,才能读懂农时的韵律;唯有追问天体,牛顿才从行星轨迹里算出经典力学。古代中国曾经因为发达的天文学而创造了璀璨的农业文明,2016年,中国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横空出世,这意味着中国再次站到人类观察宇宙的最前沿。这是南仁东用22年深山岁月,一点点焐热的梦想。
王宏甲说,南仁东不仅是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还是总工程师。他看到研发大射电望远镜所需的先进技术散落在我国诸多科学家中,他便聚拢来一百多位科学家,联合了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和大中型企业集体攻关。整个工程还有五千余名建设者参与,众人团结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巨大的创造力迸发出来。是以书中写道: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更重要的国之重器。
王宏甲与南仁东从未谋面,却在踏足天眼基地的那一刻,读懂了这份孤独里的伟大。“满地金钱的年代,他们还在看星星。”这份坚守,源于南仁东的清醒:天眼不是他一个人的执念,是国家的重器,是人民的期盼,每一寸钢索、每一颗螺丝,都连着万家灯火的期盼。
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让王宏甲再度调用自己最熟悉的报告文学体来撰稿,也惟有它能承担得起这份时代责任。
王宏甲认为,报告文学在21世纪理应有更大的话语空间,不是因为其他文体不够优美,而是这个时代太需要看清真实的文字。尤其当世界一次次变成需要重新认识的陌生对象,人们渴望能照亮前路的真实。在他看来,就像维也纳之所以能成为音乐之都,不仅仅因为贝多芬、莫扎特等名家汇聚于此,更在于那里有无数双懂得聆听的耳朵。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从文字里获取真实的力量,纪实文学必然迎来更广阔的空间。
尾声
采访结束,王宏甲带笔者参观了他的书房。磨砂玻璃推拉门后,一整面墙的书整齐排列,书桌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草稿页,光标闪烁着,像未停的思考。他说自己虽然习惯用电脑写作,写坏了多台电脑,但不爱写微博、看短视频,得了空就带孙女去乡下,很多人沉湎于文学圈子,而他更倾心自己的农民圈子。
退休后,他很多时间都会到农村去,近几年,多数时间住在贾家庄村,这个小村子位于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他前一阵刚为贾家庄村编写的新书写好序,这是继前两年为村里另一本发展记录作序后,又一次参与其中。近段时间,因为有关南仁东的文章被选进教材,不少媒体想采访他,多被他婉拒了。“抛头露面不如多写几个字。”他指了指书桌一角的手稿,是《黄金十五岁》的修改稿。这本书将于近期出版,专为中学生而写,聚焦信息时代如何深度阅读。另一本已经完稿的《孔子大传》,他收集、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写新东西就得从头学,就像当初写南仁东,得先搞懂天文学的三大时代,如今写孔子,也得把《论语》的注释翻透”。
走出他的家,回望那栋安静的居民楼,突然读懂了他曾经说的那句话:“作家不是会写文章的人,而是懂人民、懂时代、懂责任的人。”王宏甲就是这样的作家——他把根深深扎进泥土,总能眺望到时代萌发的“尖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