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艺》2025年第2期|管弦:豆科植物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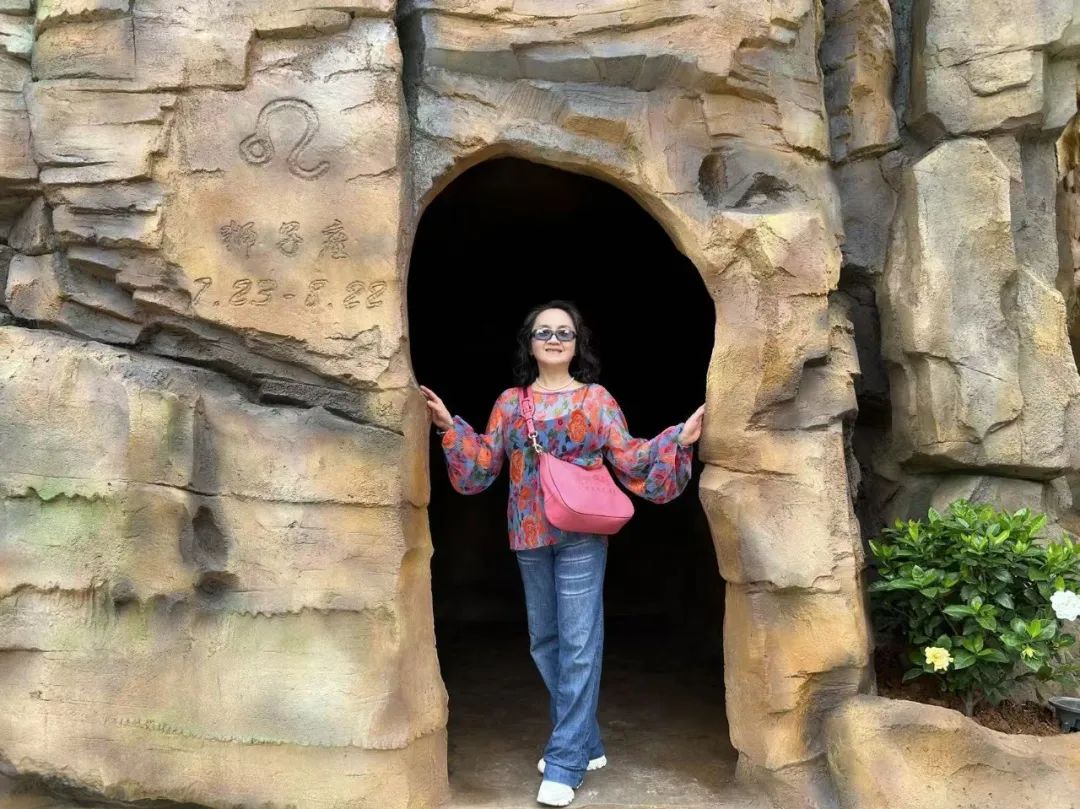
管弦,研究馆员、教授,《北京晚报》等报刊专栏作家,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文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央及地方报刊发表各类作品近四百万字,已出版《药草芬芳》《毒草芬芳》《开花的记忆》等6部著作,作品多次被“学习强国”和各级报刊、网站转载,入选精品集,获得各类奖项。
含羞草
人们的心中,大多对含羞草寄予了一些美好的情感,比如羞涩和爱情。
羞涩,这样一份纤细敏感的情怀,常常在细水长流中,小心翼翼地绽放光辉,宛若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低调,内敛,规矩。羞涩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最令人心动。
因此,含羞草又叫知羞草、怕羞草、怕丑草,好似豆蔻年华的女孩儿,情窦初开,纯净绽放。她真的是伴着爱情而来的。相传当年虞舜南巡,崩于仓梧,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遍寻湘江,终未寻见,便终日恸哭,泪尽滴血,血尽而死,遂为其神。后来,人们发现她们的精灵与虞舜的精灵“合二为一”,变成了低柔生长的含羞草。所以,含羞草有一个不常用的名字:望江南,大约是最能代表娥皇、女英那望穿秋水一般的爱情的。唐代诗人韦庄的《合欢》也记述了这段情谊:“虞舜南巡去不归,二妃相誓死江湄。空留万古得魂在,结作双葩合一枝。”
真是令人疼惜。
不过,在那令人心疼的情愫里,含羞草那一低头的温柔,那不胜凉风的娇羞,透露的信息却是拒绝。她拒绝人们随意去触碰她,那一碰即闭的清软,不容随便享受。作为豆科植物,含羞草属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含羞草性味甘、涩、寒,有小毒,她含有的含羞草碱是一种毒性氨基酸,结构与酪氨酸相似,其毒性作用的产生是由于抑制了利用酪氨酸的酶系统,或代替了某些重要蛋白质中的酪氨酸。人类误食含羞草碱,可致头发和眉毛稀疏并脱落等类似麻风病患者的面部症状以及白内障、呼吸道感染等病症的产生。其他动物食之,可致脱毛、生长停滞。孩童就更不能食用含羞草了,也不能用娇嫩的小手去拨弄她,否则,不但会出现上述症状,还会皮肤过敏。
所以,当含羞草出现在眼前时,就静静地观赏吧。一阵风儿吹过,她枝头上秀丽细密的小叶儿,更见风致了;淡红色的像小绒球一样的小花儿,也仿佛轻轻地扑上了我们的面颊,晕出绯红一片。含羞草是跟着爱情一起成长的,而爱情,是神圣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若是真的不舍含羞草,那就学会与她和平共处吧。要知道,大凡羞怯的,都特别敏感。敏感,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品质。敏感者,更能体会纤细入微的情感,更能关注他人的感受,更能接受外界的信息,从而更加善解人意、令人舒适。含羞草就是这样,对细微的变化特别敏锐,她也因此得名:感应草。她就像上天派到凡间的天使,能够感应天气变化。她的叶子开合速度的快慢,间接地反映了空气中的湿度大小,可以作为天气预报的参考。如果用工具触摸一下含羞草,她的叶子迅速闭合起来,张开时又很缓慢,说明天气会转晴;如果触摸含羞草时,她的叶子收缩得慢,下垂迟缓,甚至稍一闭合又重新张开,说明天气将由晴转阴或者快要下雨了。研究还发现,含羞草的叶子一般是白天张开、夜晚闭合,如果含羞草的叶子出现白天闭合、夜晚张开的现象,便可能是发生地震的先兆。据地震学家说,在强烈地震发生的几小时前,含羞草的叶子会突然萎缩,然后枯萎。
真是很奇妙啊。这貌似柔弱、看似低到尘埃的花草儿,实则早已高若天庭,可以通晓天地的语言。而她的这些特殊本领,也是适应外界环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当第一滴雨打着含羞草的叶子时,她立即将叶子闭合、使叶柄下垂,以躲避狂风暴雨的伤害。当第一次被动物稍稍触碰,她就马上合拢叶子,动物不会对她再产生兴趣。
就这样,含羞草宁心静气地修炼着,既保持独特的个性,又与大自然相融相和,慢慢磨砺出坚定安宁的特质。她用智慧帮助懂她、爱她、敬她的人,她会把自己安定心神、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利湿通络、和胃消积的功能发挥出来,用在失眠吐泻、小儿疳积、目赤肿痛、深部脓肿、咳嗽痰喘、风湿关节痛等症的治疗上。她还会贡献新鲜叶子,任专业人士捣烂外敷,去治疗跌打损伤。
能得到含羞草的指引和关怀,是多么幸福。如同穿过一个个安静恬淡的夜和万千岁月,终于牵到了心仪之人的手。深情相视,含羞一笑,那牵上的手,便永远不会再放开。
鸡母珠
鸡母珠的模样,真是让人过目不忘。
作为豆科相思子属缠绕性藤本植物,鸡母珠的2至5米长、分枝较多的茎通常缠绕在灌木等其他植物体上生长。她的花儿丛生于结节上,初开的时候是淡紫色的,慢慢会转为紫红色。种子,是鸡母珠最漂亮的部分,椭圆形的种子常常3至6枚一起,聚在一只只2.5至5公分长的长椭圆形荚果里,坚硬,光滑,除了白色种脐处有一块小小的黑斑之外,其余地方都是正宗的大红色,闪着明艳耀眼的光。
如此艳美的种子,让鸡母珠除此惯用称呼外,还被唤为美人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她为相思子、红豆。她由此被赋予了无限的深情。唐代诗人王维《相思》中“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就被说成跟她有关,有人说那诗中的“红豆”,就是她的种子。
实际上,《相思》中的红豆是海红豆的种子。海红豆高5至10米,属落叶小乔木,种子呈扁圆形或心形,颜色鲜红而亮丽,像红宝石一般。种子纯正的红色是由边缘向内部逐步加深的,中心还有一块心形区域更加艳丽红润,好像大心套小心、心心相印,宛如恋人们那一颗颗爱意满满的心。海红豆才更接近恋人那一份浓浓的相思。
鸡母珠不是《相思》中的红豆,从形象到气质,都不是。卿卿我我,心心念念,儿女情长,也不是鸡母珠的风格。鸡母珠虽然茎枝细弱,却强大霸气,她喜欢生长在开阔、向着阳光的河边、海滨、林中或荒地。她的生长速度很快,生命力旺盛,如果不加以控制,她甚至可以排挤并占据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成为该地的领主。
所以,再听说鸡母珠是世界上最有毒的植物之一,就一点都不用太惊讶了。她性味平、辛、苦,全株都有极强毒性,毒性最强的是种子,误食时会中毒,接触者皮肤有破损或种子破了外皮也会导致接触者中毒。种子含有鸡母珠毒蛋白,鸡母珠毒蛋白比蓖麻中含有的蓖麻毒蛋白更具致命性,它破坏细胞膜,阻止蛋白质的合成,让细胞很多重要职责都不能够完成。食入不到3微克的鸡母珠毒蛋白就会丧命,而1颗鸡母珠种子的含毒量就要大于3微克。误食鸡母珠种子后常常在数小时至一日内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胃肠绞痛、腹泻便血、惊厥无尿、瞳孔散大、呼吸困难、心力衰竭等症状,严重的呕吐和腹泻可导致脱水、酸中毒和休克,甚至出现黄疽、血尿等溶血现象,可能因呼吸衰竭而亡。尸检可见胃肠内有大面积溃疡及出血。
鸡母珠的形态特征,甚至还无意中符合古代一些人的朴素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太过艳丽的东西往往不太安全。例如姿态高雅、鸣声悠扬的丹顶鹤头上的那一抹鲜红,也被他们认为有毒,成为他们恐惧的根源。现代研究表明,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位并无毒性,丹顶鹤幼年时期是没有“丹顶”的,只有达到性成熟后,“丹顶”才会出现,这是成年丹顶鹤在体内激素作用下形成的“秃顶”,是皮肤的特殊颜色,为正常生理现象,类似公鸡那漂亮而鲜艳的鸡冠。
而鸡母珠,却真是美而有毒的代表。她的毒性完全不容小觑。她的种子外壳较硬,表面涂层弄破即有危险。生吞完整未破裂的种子时,不一定会造成立即的伤害,但即便如此,只要是不小心吞食了,还是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及时将种子取出。如果种子在体内不小心被损坏、被浸蚀等,那种危害都有可能致命。
所以,鸡母珠是不能内服的,哪怕是有严重的疥疮、顽癣、风痰、风湿骨痛等病症,需要用鸡母珠来治疗,也只能是外用。可以把她的根、藤、叶、子用专业的方法进行研末调敷、煎水洗、熬膏涂等,以达到通九窍、治心腹气、清热解毒、祛痰杀虫的目的。
现代还是有些爱美人士,抵挡不住鸡母珠的魅力,他们喜欢佩戴鸡母珠种子制成的项链、手串、脚链、戒指等饰品。鸡母珠制成的各种饰品,确实靓丽。拥有她,如同拥有了一份翩翩风采。可是,不是每一种风采都可以任意流连。要知道,佩戴她,基本上是与危险共舞;制造她,基本上是与危险相融。甚至,制造鸡母珠饰品的人面临的风险远远高于佩戴的人,在打眼、穿珠等处理环节中,如果不小心刺伤手指、损坏种皮,那制造者的生命,就有可能走向终结。
相比之下,古人对鸡母珠的运用就别有一番趣味了。他们用鸡母珠来治疗一些中了邪毒和蛊毒,以及产生各种幻听、幻视、幻觉的人。他们把鸡母珠和同样有毒的蓖麻子、巴豆、朱砂、蜡放在一起,加清水合捣,研成粉末,撒在中毒者周围,并燃柴火、放烟灰、画十字,取强毒联手、以毒制毒之意。据相关记载,这样的治疗竟然取得过非常好的效果。
想来,升腾的火光,飞舞的轻烟,跳跃其中的各种毒药,诡异奇幻的各式人群,营造出来的热热闹闹的治疗场景,竟像魔幻影片里出现的庞大镜头。鸡母珠身处其中,也显出了一份古怪精灵,仿佛沾染了魔力,瞬间滋生了抗衡和抵御的力量。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透过那层魔光,与鸡母珠遥遥相望,然后,默默远离。
皂 荚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真是喜欢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沉稳、生动、率真的描述。在这样的趣味里,皂荚树伴着菜畦、桑椹(葚)、石井栏,随着鸣蝉、黄蜂、云雀,跳跃出来,高高大大地,立在斑斓的色彩中。多么蓬勃,多么美。
皂荚树也的确是这样充满生机的。春天,她会吐出嫩绿的小叶芽儿,绿得透亮,嫩得欲滴。夏天,她细小的黄花刚刚开过,一串串翠绿的小皂荚就挂上枝头,繁茂得如同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秋天,她会暂时隐去绿意,枝间的刺更加棱角分明,紫黑油亮的皂荚也形如刀鞘,陪伴着里面随风哗哗作响的皂核,难怪她又名皂角、乌犀、悬刀,确实形象生动。冬天,她叶片飘零,而躯干依旧挺立,似剑出鞘,直冲九霄。只要不出意外,耐干旱、盐碱又抗污染的皂荚树活个六七百年是不成问题的。
也许正是生性活泼顽强、抵御邪毒的能力也强、自己也变得不可侵犯的缘故罢,作为豆科皂荚属落叶乔木,皂荚树的树皮、树叶和成熟果实皂荚及其豆荚、种子都是有毒的。她所含的有毒成分皂甙不易被胃肠吸收,一般不易发生吸收中毒,但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大剂量内服时会腐蚀消化道黏膜并被吸收,引起急性溶血性贫血。中毒时,初感咽干热痛、上腹饱胀及灼热感等,继而恶心呕吐、烦躁不安、面色苍白、头晕无力、四肢酸麻、腹痛腹泻、大便呈水样、黄疸等,严重者可发生脱水、休克、痉挛、谵妄、呼吸麻痹等,最后死亡。
只是,人们仿佛并不惧怕皂荚的毒性,山坡、林中、谷地、路边、庭院、宅旁,到处都有她陪伴人们的身影。在与皂荚朝夕相处之时,人们早已学会正确对待她。例如,知道她有别具一格的祛污功能,就常常把成熟饱满的她,捣碎取汁,变成天然环保的洗护用品:洗头,头发会油滑黑亮;洗澡,皮肤会清爽光滑;洗衣,衣服会洁净如初。有些乡村,还把皂荚作为男婚女嫁的吉祥物,放在新婚用的箱子里、被絮中,作为多子多孙的祝愿。男女结婚典礼前的焚香沐浴,澡盆里也常常放上皂荚。
医药学家们更是学会了小心而用心地对待她。
首先是选材,要选肥厚而没有被虫蛀过的。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说她“结实有三种:一种小如猪牙;一种长而肥厚,多脂而粘;一种长而瘦薄,枯燥不粘。以多脂者为佳。”南北朝刘宋时期医药学家雷斅也说:“凡使,要赤肥并不蛀者”然后就是要好好炮制了,雷斅说:“以新汲水浸一宿,用铜刀削去粗皮,以酥反复炙透,捶去子、弦用。每荚一两,用酥五钱。”元代医药学家王好古也说:“凡用有蜜灸、酥灸、绞汁、烧灰之异,各依方法。”
经过精心加工的皂荚,更是大有裨益。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说她可治“风痹死肌邪气,风头泪出,利九窍,杀精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她“通肺及大肠气,治咽喉痹塞,痰气喘咳,风疠疥癣”“其味辛而性燥,气浮而散。吹之导之,则通上下诸窍;服之,则治风湿痰喘肿满,杀虫;涂之,则散肿消毒,搜风治疮”。宋代医药学家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还记载过实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自春至秋,蕲、黄二郡人患急喉痹,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黄州推官潘昌言得黑龙膏方,救活数十人也。”黑龙膏就是用皂荚为主药熬成的膏。
甚至,那些悬梁自缢又还一息尚存的轻生者,也能得到皂荚强大而迅速的眷顾。把皂荚和细辛研成粉末吹入轻生者鼻内,轻生者便会打个喷嚏,苏醒过来。宋代学者钱竽在《海上方》中作诗写到这些时,竟是直白有趣的:“悬梁自缢听根源,急急扶来地上眠。皂角细辛吹鼻内,须臾魂魄自还原。”
起死回生,在性味辛、咸、温的皂荚这儿,真不是童话。
有时,站在皂荚树下,一阵风吹来,皂荚的细绒会钻进鼻孔,令人瞬间喷嚏连天。而体内气机,也在这不由自主的气息交换中,愈发通畅顺达了。情不自禁的笑容,让嘴角像月芽一般,上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