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故乡仍然是创作的永恒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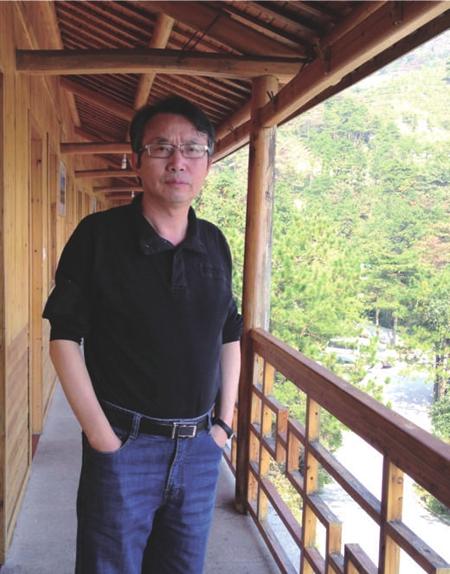
徐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5卷)》《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在水底思想》,长篇传记《张恨水传》等。
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徐迅出走半生,忘不掉的是故乡的山水和人,停不了的是书写故土的笔。
“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与故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亲情里深深浸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隐忍和希冀,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
诞生于乡野的作家梦:这场“梦”,一“做”就是40多年
20世纪60年代,徐迅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市余井镇。他的家乡坐落在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东麓,俊美的山川和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着这片土地,诞生了唐代“五老榜”诗人之一的曹松、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京剧鼻祖程长庚、现代作家张恨水等名人。
土生土长在乡村,徐迅的记忆里,家乡“大片的丘陵上有山、有水、有稻田,长满松树,也长满蒿子草,长满了庄稼,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泥土喷香”。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野,可读的书极其有限,徐迅至今仍记得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老师每天会在课余给学生读上一段小说《追穷寇》,“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类似于‘说书人’,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
后来,随着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阅读面的越发宽广,徐迅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读书、写作成了他的精神养料,文章也很快发表在了县文化馆的文学小报上。“那时报纸副刊多,散文发表快,这很能满足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就这样,他不停地读读写写、写写读读,一发不可收拾。
徐迅说,那时的自己犹如一只被“缪斯”之箭射中的小鹿,懵懵懂懂,不顾一切地跑上了文学这条充满艰辛和痛苦的崎岖小路。“再后来,随着作品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和介绍,当自己又成了一名文学刊物编辑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我曾经做的竟是一个绵长、幼稚而又艰辛的‘作家梦’。”
这场“梦”,一“做”就是40多年。当年那个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而兴奋得在田野上奔跑的少年,早已在文学的土壤上耕耘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去年在老家,徐迅意外翻出了几本十一二岁时读过的儿童文学作品,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留了自己当时的签名,那段初识文学,如饥似渴读书的记忆再次被唤起。“认真想来,我一直在成为作家的路上。”
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书写故乡的人和事。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人物传的编辑工作,那段日子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精致的文化关怀,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的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
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只身走入北京后,陌生的环境、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故乡感”。在《道是故乡即家乡》一文中,他曾写道:“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是实体,是具象的,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里面就有一种情怀,就有生命情感的外泄……‘故乡感’既有时间的距离,又有空间的距离。”
“其实鲁迅他们那一代作家笔下‘故乡’的写作,都有一种‘故乡感’驱使。这种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会让人把‘故乡’与‘家乡’两种情境区分开来。”徐迅说。自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算起,已过去30年,交通发展日新月异,记忆中熟悉的乡野也发生了变化。一次次乘着高铁返乡的路途中,他发现,原来的那种“故乡感”已逐渐消融。
“某种程度上说,写作正是一种‘陌生化’的发现和呈现。由于交通的便捷,信息的异常发达,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由此一来,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感’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故乡的‘陌生感’在减弱。”徐迅说。
尽管如此,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感觉’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在新的时代,这种消失了的‘故乡感’的故乡依然在那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
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
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编,也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其间笔耕不辍,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他早年写小说更多,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修养和才情,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质朴自然,且无法刻意创新、用心雕琢。
2019年,《徐迅散文年编》面世,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至今已出版《雪原无边》《皖河散记》《鲜亮的雨》《秋山响水》和《竹山可望》5卷。
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他有些“心怀忐忑,惴惴不安”,“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作品会有一种良莠不分、参差不齐之感,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的面前。”徐迅坦言,“好在,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随时随地而写,甚至想到就写,一挥而就”。“写散文对于我来说,全然是为了自己。相比较写小说而言,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
徐迅认为,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从内心出发。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最有力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徐迅说,“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却又是个体的、独特的、无法复制的,其中的‘微妙’无以言说。作为写作者,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只属于‘我’的独特性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