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访谈 | 孙孟媛:找点甜的东西,像蚂蚁一样背着往前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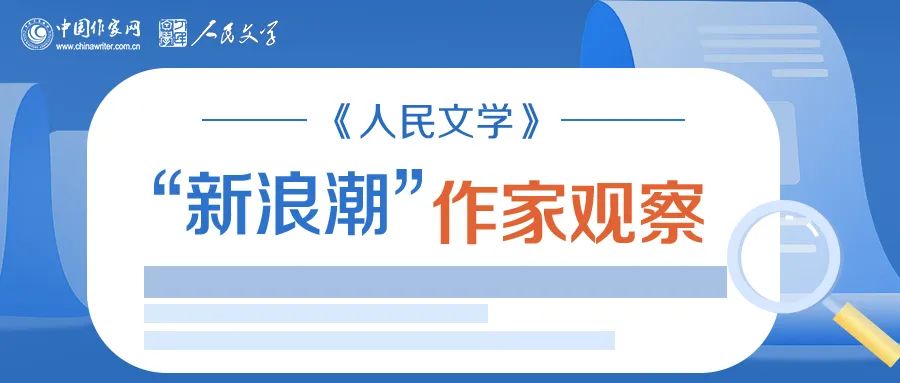
《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自开设以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杂志的品牌之一。此栏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今年,中国作家网继续与《人民文学》杂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观察专题,作家访谈和相关视频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各新媒体平台、《人民文学》杂志各媒体平台推出。自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澜、陈萨日娜、孙孟媛、刘康、周于旸、陈小手、路魆、夏立楠、庄凌、马林霄萝、丁甲,敬请关注。

孙孟媛,一九九六年生,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六届高研班学员。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山东文学》《雨花》等刊,曾获第六届“泰山文艺奖”。
闪电:带着力量和美感,劈开眼前的混沌
梁豪:孟媛你好。首先,我们或许得向远在新加坡的蚂蚁致意。是这些难缠、磨人的小家伙,给了当年在新留学的你相当的痛苦的同时,也赠以不无美妙的灵感,最终写成《蚂蚁爬行》。正是这篇小说,让我们结缘,见字如面。现在,又有了此刻的对话。身为写作者,我们在意文字在地域之间、人心之间的流动,更思考最终它们在我们心底留下了什么。小说到最后,蚂蚁爬行之时,电闪雷鸣之际,你想留给读者什么呢?
孙孟媛:《蚂蚁爬行》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有了比我想象中更多的读者。通过不同的途径,我得到了一些很有价值、令我惊喜的反馈。关于小说结局,有趣的是,有的朋友感性地希望闪电过后女主人公觉醒,选择离开男主人公,让这一两性关系分崩离析。很多朋友读出了临渊情感状态中的一种理性选择,一种于艰难中自洽的婚姻态度。不得不说,很开心小说能被读者朋友代入真情实感去阅读。小说的核心还是那个古老的问题:女性在婚姻、情感、社会关系中如何作出选择?在婚姻中妥协、与生活和解就表示女性失去独立的人格了吗?我的答案:否。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是,当人的精神从困惑中突围时,可跨越生活形态的禁锢,依旧拥有自由的人格。女主人公从渴望爱情到接受爱情已逝,明白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之后,一切都变得豁然了。
小说最后,在电闪雷鸣之前,有一场无声的细雨,它象征主人公内心的朦胧和潮湿。接着,闪电带着力量出现了,劈开了眼前的混沌。闪电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可以真的出现过,也可以是想象。结尾有关闪电的对话,其实是他们拥有过但后来失去的一种交流状态的再现。此处,我想留给读者的是我捕捉到的转瞬即逝、带着光亮的温情。借助这道闪电,我更想留给读者的是,我在写作中极力追求的那种有力度的美感。
梁豪:婚恋、性别、学历、就业,在较短的篇幅里,你借由异国他乡的一次试婚体验,将以上直指当下青年要害的重大议题给“爬行”了一遍。这是你有意为之吗?我想,至少不尽然,否则,它难以做到如此顺畅和自然,如同议题不再是议题,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以自身的生命情感为指引,遵循自我对文学创作的探索,于是,不觉然间,小说攀爬出了那些宏大而棘手的概念本身的片面和局限,直抵生活深处某种更为立体、幽微的真相——是我在自说自话吗?
孙孟媛:不是自说自话。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摸索。在最初的构思阶段,我设想的结局是女主人公拒绝妥协的生活,选择同男主人公分手,从中体现女性的勇敢和成长。但是这样写的作品很多,优秀的前辈已经把这种题材写得炉火纯青了。可以说,我在构思时“取巧”了,试图尝试不同的主题。但我很肯定,这不是一场生硬的主题挪动,而是我在结合社会现象和情感经验思考时,体察到的婚恋生活中的另一种真相。这篇小说既是女主人公与情感生活的一次博弈,也是我与以往写作经验的一次博弈。这个探索的过程令我激动。
目前,我不想追求先锋的叙事和奇崛的形式,我写作的出发点就是生活,写出生活的深刻性,通过生活的细节和从中生发的真挚情感一步步表达、阐述,而不是故事和形式。虽然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梁豪:老话讲,“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画极易失察、极难辨清的“今日之犬马”,难上加难。《蚂蚁爬行》之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正在于它以文学的范式触探着最前沿的社会动向,同时,带来了独属作者的感受与见地。作为编辑、读者,我期待遇见更多这样的作品。
孙孟媛:谢谢你的喜欢。这涉及一个大问题: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我的见解并不深厚。但有一点我很明确:写作者应该不断地动脑思考,用前沿的思想捕捉独特的时代要素。这是难题,但也是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我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围绕生活日常、男女情感展开的。这是我的舒适区,也像是个圈套。在这个圈套里,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将日常生活的触角伸向某种共同的人类经验,体悟时代、社会的“不变”与“变”。比如,这篇小说阐述的婚恋问题在文学作品中是古老的、恒久存在的,但是到了当下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中,问题指涉的社会现象发生了明显变化,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两性关系。
好的题材实在太难得、太值得珍惜了。能够遇到这样一个题材,我感到非常幸运。
白杨:没什么野心地立在路边生长
梁豪:跟很多新人从自己和身边写起不同,你的处子作《12路电车》,包括稍晚的《流言》,上手就是“战火里的青春”“一代人的怕与爱”。前者像老舍《四世同堂》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混合,按你创作谈所提,还有缘自《青春之歌》的某种启发;后者的字里行间则浮动着王安忆《长恨歌》、苏童《妻妾成群》的形影。此外,它们还隐约透出白先勇《台北人》的那份“暮霭沉沉楚天阔”。说你拥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或格局,想必是恰当的。当然,诚如王国维所讲:“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因此我更想说的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当中的叙述者跟真实的孙孟媛是有较远的距离的。这还挺耐人寻味。
孙孟媛:短篇《12路电车》和中篇《流言》是我最开始写的两篇小说,可以说是历史题材小说,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故事。我本科念的是中文系,你提到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读的。实话实说,我是在模仿这些经典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是我创作道路上基石一样的存在。正因为烙印太深了,一下笔就带着那种味道了。《12路电车》确实受到了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小说的启蒙。我试图追溯历史,写的是1934年到1949年发生在香港、上海两地的故事,不只写男女情感、女性成长,还有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家国情仇。写《流言》的时候,我刚看完《长恨歌》,就很自然地想写一篇有关老上海的小说,甚至忘记了灵感是怎么来的。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写作经历,两篇小说写完后,有段时间我一度认为自己只能写历史小说,还为此担心过。但是我把阅读的重点转移到当下文学现场后,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新的写作形态。所以,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实,我并没有在上海、香港两地居住生活的经历,小说中写到的民国时期的市井风气、城市景观等,都是我从书里读来的。那时,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没什么羁绊似的在历史的天空中自由地翩跹。那是我的感性写作阶段,现在的我逐步走向理性姿态的写作了。但我仍然珍惜那种青涩快乐的写作感觉。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试着再写一写这种题材,对它说,嗨,老朋友。
梁豪:“快乐”,多么珍贵的字眼。很多人不去凝视过往,首先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兴趣问题。假如钻研历史、发挥历史能让你感到开心,何乐不为?还有比快乐更好的写作向导吗?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如果我们的创作者出于未曾亲历抑或他人捷足先登而直觉地认定“眼前有景道不得”,这才值得好好反思。在这件事上,或许有必要搬出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的话:“传统是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东西。它不是可以继承的,如果你想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后继续做诗人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历史感不仅包括对过去的‘过去性’的感知,还包括对它的‘当下性’的感知。”每一代写作者面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遗产时,都应有一种建立在认知和敬畏之上的再造意识。历史是一代代人的回忆,回忆是一个个人的历史。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成了,我们能否真的在回望中有所发现,而非仅仅只是递补进入某个历史的唱诗班,为那重弹的老调献上自己稚嫩的和声。
孙孟媛:浮生若梦,快乐多么珍贵啊,我会呵护好从文学中找到快乐的心境。在我差不多四年的写作时间里,快乐的心境很明显发生了变化。最初历史题材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更多是一种“无知”的快乐,随着与小说的接触越来越深,现在的写作带来的是与痛苦交织的快乐。这种痛苦来源于不满意、思考打磨、怎么变得更好等等。但比起单纯的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快乐更能让我感到安心。就像知道无忧无虑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成年人必须像蚂蚁一样找点甜的东西,背着往前爬。
“我们能否真的在回望中有所发现,而非仅仅只是递补进入某个历史的唱诗班,为那重弹的老调献上自己稚嫩的和声。”这真是直击灵魂的一个问题。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点醒了我——小说创作的意义是什么?写作者是要追问文学给了自己什么,还是应该把追问的重点放在自己回馈了文学什么?能够深刻感知“过去性”和“当下性”的作家,一定在追问后者。
梁豪:从短篇小说《寻找白猫》开始,你转向对身边或自我际遇的打量,最明显的征兆,是小说里“我”的现身。尤其是小说《芬芳》,我认为它撬开了埋伏在板结的世俗日常里那些柔情似水、惊心动魄的时刻。总体而言,在迄今不多的创作里,你慎重、细致、耐烦,同时又堪称盛大地面对和打磨一个个具体人物的悲欢忧乐。将心比心,倾听、还原、追问人物真实的心跳,而不仅仅为了摆布,这很可贵。技巧上的进一步打磨,凭经验、靠总结,可以慢慢来。修辞立诚,路子走对了,比什么都重要;反过来,这又会助推你的故事和讲述日益枝繁叶茂。
孙孟媛:真情实感地写出人心的深度,是我看得很重的。希望以后能够不急不躁,照着这个路子再多写一写。
短篇《芬芳》是我目前创作的唯一有人物原型的作品。小说源于我的一段北漂生活经历。去新加坡读研究生之前,我在北京租房实习。合租室友是一对北漂多年的母女,她们租了其中的一间卧室。母亲五十多岁,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员;女儿二十多岁,在一家店铺当营业员。她们勤劳努力,认真对待生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想到她们,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寒冬街头上的白杨树,没什么野心地立在路边生长。现实是,那段时间我们相处时带着厚实的隔膜,现在也已经不联系了,但我衷心希望她们能过得好,人生熠熠生辉。
这段合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馈赠,让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有了牢固的支点。这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也在告诫我,多体验日常,多与人交流,观察生活的现象,感受生活的纵深。对生活的感受越深,我们的创造力就越蓬勃。也是因为合租的经历,我开始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空间问题。狭小的生存空间里所孕育的人性是多样化的,是可以碰撞迸发出火花的。《蚂蚁爬行》中也写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情节。
梁豪:现在常讲原子化的生活,但原子化的生活是有前提的,你得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就现实的局面,在大城市,要想实现、贯彻“理想”的原子化生活,并不容易,往往你得容忍他人——通常是陌生人——介入你的场域,挤占你的时间。在合租的空间里,纵然房门紧闭,甚至明知隔壁的租户不在,你在心理上也很难摆脱相互牵制的羁绊,因为门——大门、卧室门或不知道什么门——随时有可能被敲响或推开;更令人不安的是,动静兴许来自房东或中介。当然,这里面也潜藏了哪怕是短暂的彼此扶持的可能——原子之间的融合,可以发光、产生能量。此外,相比物理空间,作为人之生存的另一重要参数的精神空间的单调和苍白,或许同样值得我们留心。“当代人的生存空间”,我们的确关注得还不够,不够仔细,也不够透辟。
孙孟媛:时代变化太快了,我认为人适应时代的基础就是适应生存空间。比较以往,当代人的生存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现在很多人选择去海外生活,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一年往返多次。比如,大城市里很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城市的印象就是整日“跑路”,然后回到群租房休息。还有前段时间有新闻说,一些网约车司机为了节省房费,住在车里。再比如,拆迁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与居住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人的生存空间的复杂,往往指涉着精神空间的复杂,放在文学中有很多可以阐述的点,不过我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切口。
梁豪:我的感觉,你有一颗清澈的慈悲之心。小说里纵然烽火四起,战地的,或人心的,却总感觉并不真的狠得起来。那些烽火注定是要熄灭的,人终究是要圆满的。是这样吗?
孙孟媛: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圆满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可惜很难达到。目前,我的写作观是为小说中的人物在理想与现实、快乐与痛苦、自由与禁锢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本人可能潜意识里有着“中庸”思想,这反映在作品中了。比如,我不想在小说中暗自批判笔下的人物,我认为他们都有自身的逻辑,没有真正的谁对谁错。再比如,我关注女性主义写作,支持女性主义,但还不想在作品里呈现激烈的女权思想。
流星:微光在星月间划过,又回落我心
梁豪:从时间看,你小说里人物的命运多是起起落落地舒展开的,而非很多作家尤其在写短篇时惯用的“截面”,随之,背后时代的更迭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脉络;从空间看,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远东的大城往往是你铺展故事的主舞台。是因为璀璨、包容的都市更能承载和掩护人物摔打自身的命运吗?你的故乡山东,或者具体到滨州,似乎尚不在你的创作视阈内。
孙孟媛: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我的确有出于扩展叙事空间的目的。城市越大越具有包容性,人被淹没得越厉害,个体行为受到的指摘相对更少。像跨国试婚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大城市对此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人物命运能在更具弹性的叙事空间中展开。但我将小说的发生地设置在新加坡和北京,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自我学习、生活的经验。
你的第二个问题触及我的灵魂,它是我近期开始反思的重点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故乡还未出现。迟子建老师讲过,故乡是文学永恒的根。我好像还未找到我的根。想到此,总会生出一种飘浮之感。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故乡似乎不是自己离开的,而是被我藏了起来,藏在了内心最深处还挖不到的地方。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省内离家乡很远的地方读书,与家的距离、繁重的学业压力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衡状态。几乎是从那时开始,故乡在我的心里成为一种创伤,我渴望得到却无法得到的缥缈之物。我也试图回归,可能某一天,它会先以创伤叙事的形式来到我的作品里。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还是会回去。慢慢来吧。
梁豪:好像你最近迷上了门罗。从杨沫到艾丽丝·门罗,我开玩笑说你是在“养蛊”。或许,作家的确得在脑子里养那么一回蛊。在这个过程中,在跟林林总总的意志、思想、观念和修辞的纠缠中,慢慢挣脱出自己的态度、志趣和调性来。有什么最新的心得可以分享吗?
孙孟媛:“养蛊”这个词真有意思。杨沫是我在学生时代养的一个“小蛊”,《青春之歌》是我写女性成长小说的启蒙。现在,她对我的影响已经淡化,所以我称其为“小”。艾丽丝·门罗的作品我正在读,还有很多没读过,是正在摸索的一个“大蛊”。我实在是太爱她以不动声色的笔调抓住人物内心转瞬即逝的微妙感受的写法了。在这一方面写得很好,我也非常喜欢的作家还有张惠雯。她们的风格很对我的胃口。
最近的心得感悟是,要培养好的审美。小说不只是创造生活,还要提供审美价值。我认为作家风格的不同,本质上是审美经验的不同。好的小说总能提供一种艺术愉悦感,让读者脑海里像跳华尔兹一样旋转不停。
梁豪:在写作的这个阶段,对你而言的难题是什么?
孙孟媛:第一个难题是,人生阅历单调,缺少充分的生活体验。我很羡慕那些本职工作和文学有距离的写作者,比如医生、法官或者其他与民生服务有关的从业者,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得到一些素材。对我来说,获得素材的途径很狭小。第二个难题是,随着阅读量增大,认知提高,近期一直存在眼高手低的问题,很难对自己的作品满意。
梁豪:这两个问题也困扰过我,很难说现在就彻底摆脱了。但透过与人交流、自己琢磨,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第一点,须知,每种人生都是有所得而有所失的,难以处处尽意。看似朴素庸常的生活里,真就没有诱发好故事的机缘吗?我们缺的或许只是对某个人、某件事追究到底的意愿和毅力;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没有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热爱生活。好在,这是可以调动和激活的。另外,即便房间空空荡荡,即便生活枯燥乏味,作为某种征候的空与乏,不也挺值得盘一盘?何况我们理当拥有写作者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和想象力,甚至,竟而把持着多少殿堂级作家见所未见的电脑和手机。至于第二点,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自我生长、实现蜕变的必经之路。真正的写作,终归是有点难度的——如果不是很有难度。
孙孟媛:谢谢你给予的启发。我的理解是小说创作和生活经历的关系也是一种能量守恒,生活的独特性能够催发不同韵味的小说,可能枯燥乏味的生活能让写作者更有意识地发现生活的缝隙和隐秘之处。说到手机和电脑带来的大量信息,我倒想到了一位前辈的经验——当从网络上看到一些感兴趣的社会新闻时,最好不要只抱着“我了解了一件事”的心态,而应该尽力分析这种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像大树扎根一样摸索触及地面之下的泥土、水分和砂石。这也是小说写作发现素材的路子。
梁豪:私下交流时,你说自己“没有对文学疯狂过”。这是否也即你所谓“中庸”在起作用?你出身山东大学科班,后去南洋留学,毕业回到山东,在文学杂志当编辑。你的这部分经历跟我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我蛮能理解你这话的意思。在这里,可以更充分地展开谈谈吗?
孙孟媛:从出生到现在,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上学的时候,我对创作很感兴趣,第一篇小说《12路电车》的前一部分是大三的时候写的,但没有写完。没有写完的原因是有必读书目要读,有作业要做,要考试了。现在想来,我把被定义的哪个阶段要做哪件事看得太重了。但是在考研、找工作这样的大事面前,我们谁又能逃脱现实因素对人的控制呢?当了编辑之后,似乎一切变得稳定了,在周围创作氛围的感染下,我才真正开始写作。如果没有选择编辑这份职业,我可能就不会继续写作了。
把写作比喻成一次征途的话,一开始我是那个在远处瞭望,不敢抬脚出发的人。之后,走在阡陌纵横的小路上,周围是杂草、荆棘,还有比人高的玉米,我发觉身后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前行,直到把我推向大路。我站在大路的边缘,发现身后的那股力量转移到了前方,为了抓住它,我开始自觉地迈开双腿,步伐细碎。这时,我发现大路的风景真的不同,它新鲜、清晰、开阔。如果能跑起来,眼前的风景会变得更加灵动。但现在,我想的是慢慢地行走,好好地感受一下这条大路。
我对文学不疯狂,但神往。在我心里,文学并不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持续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而是像流星一样,带着微弱的光亮在星星和月亮间划过,又回落到我的心里。一瞬间,平淡的日子里突然生出一种隐秘的难以克制的情绪,让我激动、兴奋。这样的时刻,真好。正是我对文学的不疯狂心态,才让我有了松弛的写作状态,保持单纯的写作目的。
梁豪:不必疯狂,“恐怖情人”通常还挺可怕。但要爱,要厮守。或许是编辑的职业病,我总希望善感的人、会写的人,你大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但请别久久竟而真的停下创作的步履。就按照一定的节奏,不疾不徐地写下对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吧。
孙孟媛:感谢你的期待。有人期待是创作不倦的动力。很难下决心说,这辈子一定会写到老。但我想说,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