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不是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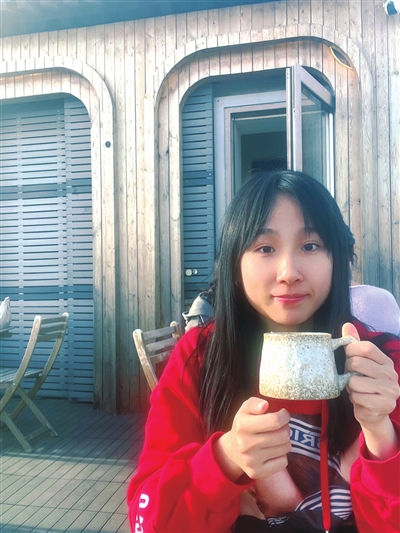
廖天琪,女。中国小说学会会员。10岁开始发表作品,曾获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沧慈》,另有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发表于《红豆》《鹿鸣》《天津文学》《海燕》《安徽文学》《解放军报》等多家报刊。
一
黎明时,飞机发动了,从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起飞,前往南疆阿拉尔。
飞机拔地而起的一刻,阳光突现,万道金光,洒满长长的跑道。
飞机披浴晨光,一路向南飞行。
机翼下方先是一片起伏的雪白,那是终年积雪不化的天山山脉。天山雄踞新疆中部,群山高大恢宏,气势卓伟,故名“天山”,意思是高耸的山峰抵达天际。天山山脉如同一架巨大的折叠式屏风,把新疆大地分成了南北两半,习惯上,人们把天山以南叫做南疆,天山以北叫做北疆。
飞机稍稍转了个弯,越过天山,一片浑黄跳入眼帘,紧接着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浑黄,那是沙漠、沙丘、戈壁组成的沙漠之海。这就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习惯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将目光投向舷窗外。窗外是已经非常熟悉的风景,机翼下方是曾经茫茫戈壁,每次看到这些情景,我心中都会感慨不已,继而生出沉甸甸的感觉。
北京有直飞阿拉尔的飞机,但是因为订票时间稍晚,我最终还是选择在乌鲁木齐转机,先是头一天半夜到达乌鲁木齐,第二天凌晨再直奔阿拉尔。如此一来,反而比直飞阿拉尔的行程提前3个小时到达学校。
飞机继续沿着沙漠之海向南飞行,满眼充斥着的都是沙海、戈壁,只是沙海、戈壁。沙海波涛起伏,戈壁一直延伸到天边,仿佛时间停止,地老天荒。就在你的视线仿佛凝固之际,倏然,一条银白的长带跳入眼帘,紧接着,银带两侧,绿光闪闪,大片绿洲如宝石翡翠呈现,这就是南疆的明珠之城阿拉尔。
阿拉尔机场小巧而简洁,它应该是全中国最精致的机场,在一大片无垠无碍的戈壁上,只有一幢孤零零的红色候机楼,一条长长的灰白色的跑道划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拉尔市区醒目的分界线。
由于来接的车已经提前在飞机入口等了许久,我下了飞机便一路小跑。好在机场不算绕,我很快就与来接的老师汇合,上了车,关上车门,车子一溜烟朝学校驶去。
此时,看了看手表,很好,时间完全来得及。
在几个月前,我接到了关于采访新疆建设者的任务。很多新疆的建设者都是我了解并且熟知的,但是这个人我完全不了解,也查不到有关她的任何资料。她没有任何荣誉,她同大多数默默无闻的新疆工作者一样,名不见经传,不为人所知。
二
2021年的央视春晚,一首《可可托海牧羊人》感动了无数的国人。
“可可托海没有海,
那是蓝色的白杉
晚归的牧牛步履悠闲
夕阳下的胡杨林多么耀眼
一边的大漠戈壁
一边是流水潺潺
额尔齐斯河静静流淌
憔悴旅人在月光下游荡
可可托海没有海
可是有我心爱的姑娘……”
现如今的可可托海已经被列为了5A级风景区,它地处美丽的峡谷之间,有山石、林地、湖泊等自然景色,带着当地独有的民族文化风情,成了许多爱旅游人士的游览胜地。
其实,在这里除了优美的风景盛地外,还有一座水电站——可可托海水电站。
可可托海水电站,是位于新疆富蕴县境内可可托海镇,它是我国垂直最深,设计最全的水电站。
在新疆,所有的建设都比内陆要难上无数倍。可可托海水电站也是一样,它拥有丰富的矿脉,其中三号矿脉是世界稀有矿脉,里面有80多种稀有金属,这些金属对于我国建造原子弹、氢弹等武器有重要帮助,它的丰富储量堪比一家地址博物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宝贵的矿产资源更是国家急需的,结合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该水电站的建设是至关重要,也是刻不容缓的。
三
夕阳沉醉。夕阳中的沙漠与胡杨树,构成了一幅经典的西域边疆图景。
到达塔里木大学时,正逢该校举行建校65周年庆祝活动。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校友回到学校。老同学相见格外亲热,大家拥抱,握手,坐下来聊天畅谈,有太多的话说不完。宣传部长陈蕾带着我穿过操场,在教学楼处见到了一位女士。
第一次见面时,她安静地坐在人群之外等着我们,我注意到她的穿着与其他的女性同学不同,身上的衣服款式和质地都不太讲究,好像是才从箱子底拿出来的。她皮肤黝黑,满面风霜。一看就是长期户外工作的。陈蕾向我介绍说,她是哈萨克族姑娘、塔大老校友库丽扎。
库丽扎毕业三十六年,一直在可可托海水电站工作。
采访库丽扎最开始有一点点障碍,因为她几乎很少谈自己。她说,比起那些无名的英雄,她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库丽扎是依米奇英雄之女。这使得她从出生起,就与别的孩子不同。
库丽扎说:“比缘分更加刻骨铭心的是使命。”
已经五十多岁的库丽扎是哈萨克族的孩子,半个世纪以来,她一直没有走出过新疆,却为新疆水电站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对她的不断了解,那些尘封在她记忆中的一段段故事不断揭开,在她的身上的一段让她、让塔大老师都潸然泪下的故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那是一段有关可可托海水电站的故事。可可托海水电站在新疆富蕴县境内可可托海镇西南10公里额尔齐斯河上游干流,曾经是我国唯一的最大最深的地下水电站。
关于该水电站的修建,当初参加过修建的技术人员说:“在新疆,不论是修建铁路、公路还是桥梁,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比内地难上无数倍。而其中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可可托海水电站。”
水电站位于可可托海镇10公里,这里是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伊雷木湖出水口,在建国初期,考虑到我国的国防建设以及相关保密原因,这座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下,在当时鲜为人知,许多人不知道更从未见过它的真面目。时至今日,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已经安全运行了几十年,它的神秘面纱也被逐渐揭开。
在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这里曾在冬天有零下57度的最低气温纪录,被称为“中国的寒极”。当时的修建条件异常艰苦且危险,在二十年中已经有数千名建设者为此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
可可托海拥有丰富的矿脉,其中三号矿脉是世界稀有矿脉,蕴藏着80多种稀有金属。这些稀有金属是国防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材料,可可托海的丰富储量可堪比一家地质博物馆。
1955年夏,国家电力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派出了侦察组到可可托海视察,当时的侦察组对可可托海上、下游河道和峡谷水利地势进行勘察。几个月后《新疆可可托海水电站勘察报告》便提交了上去。
1956年,这里开始建设水电站。
1958年的5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建设一师五团接受了修建水电站的任务。任务要求他们负责道路及水工工程的施工。因为工作内容的保密性,工程内容用代号“边疆某地水电站工程”代替。
1964年8月,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对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的设计图,新疆有色局接受可可托海矿务局局长王从义的建议,调集相关技术人员到水电站工作,与新疆有色局工程公司一起参与水电站的修建。当时,修建水电站的大多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同学们,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有色局,后来接到命令到了可可托海。
任务命令下达的时候,哈萨克族青年依米奇正在准备结婚。为了工作,他与妻子商议后,简单地举办了婚礼仪式,就奔赴新疆,投身到水电站建设当中。一年后,依米奇把妻子也接到了可可托海,但是居住地离工地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父亲依米奇的很多事情,库丽扎都是后来听母亲说的。
母亲说,那时候工地不分白天黑夜地赶工期,在天气好的夜里,远远地就看到,工地的位置灯火辉煌。父亲有时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工程进行得非常艰苦。山体都是坚硬的花岗岩,掏挖竖井非常困难。而且这里的天气异常寒冷。母亲说,父亲来自内陆,一开始并不适应如此寒冷的天气,他经常因为寒冷觉得骨头在嘶嘶的疼,甚至有时候还能听见手指活动时因为僵硬发出的声响。他只能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只露着两只眼睛,十个手指头干活,身上用棉布裹着一层又一层,即使是这样还是觉得冷。
库丽扎描述道:“他们每次进出工地,都要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前行,风雪漫天,道路也十分险峻,所有的设备、建筑材料,都要靠人工,蹚着齐腰深的冰雪,一步步从山道上扛进来。”
有一天,父亲突然回家了。父亲进了门就坐在地上,把头埋得低低的。他的样子很憔悴,身上的衣服因为泥土和汗水干了又湿,变成了一块一块硬硬的布片,像铠甲穿在身上,母亲要父亲换下衣服,父亲却只是低着头,母亲这才发现父亲在哭,他的声音从小到大,哭着哭着变成了嚎啕……
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一直搂着他,给他拍拍背。过了好一会,父亲抬起头来,红肿的眼睛看着母亲:“我们班长……没了……”
当时,依米奇他们班正在清理作业面,那天风很大,父亲穿得很厚,耳朵和脑袋也用毛巾包住了,他没听到山石松动后滚动的异响,是班长冲过来,大喊了一声:“快躲开——”同时,使劲推了他一把——他被推得摔倒在一旁,几乎同时,他看见几块山石从山上滚下来,其中一块砸中了班长,班长倒下了,头上身上都是血。
他们扑上去,抬起班长,他大哭着抱着班长的头,几个战士托着班长的身体,在满是砾石的山坡上跑,他们要把班长送医院。正好有一台运送材料的车子在附近,班长被抬上车,依米奇嘴里只一遍遍重复一句话:“拜托,别,拜托…。”
车还没到医院,班长就没了。依米奇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没得,那一瞬间,就仿佛整个世界都黑下来了,只有无尽凄惨的声音一遍一遍传来,又慢慢消失。
班长牺牲后,依米奇接替当了班长。
工程艰难却顽强地进行着。
他们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很难,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副食,只能靠春天的野韭和野葱。
因为水电站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必须要使用炸药炸开山石,才能够开掘下挖。依米奇是班长,放炮员的工作是班长必须要做的。点炮时,每次十个点,依米奇和其他放炮员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点完十个炮,然后快速跑开,跑到安全距离之外。
库丽扎的母亲对丈夫的工作一直非常担心,叮嘱丈夫在点炮后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跑到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外。母亲开始尽量节食,把食物省下来,存起来,等父亲回到家时,做给父亲吃。母亲希望父亲多吃一些东西,这样就能有较好的体力,在点炮时能够脚步更快地脱离危险区。母亲因此患上了浮肿病。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母亲的脚肿得站不起来。那时候,夫妻俩都不知道,这时候库丽扎母亲腹中已经怀了小小的库丽扎。
父亲依米奇说工地上因为粮食供应紧张,不少人体力下降。母亲实在担心的不行,她第一次认为自己很自私,但受不住担心,只能小心翼翼和丈夫说:“能不能把每次十个炸点的数量改成五个,哪怕多冲上去几次也行。”父亲依米奇接受了。
库丽扎说,父亲依米奇按照每次五个炸点的数量安排工作。但是那时候雷管和炸药的质量很低,加上气候严酷保存条件有限,有一些雷管的功效随着时间和温度在慢慢发生变化,受潮的雷管会延迟爆炸或者成为哑炮。而哑炮却是有很大危胁的,必须逐个清除。
那是依米奇最后一次点炮,和往常一样,裹得严严实实的依米奇熟练的拿着设备在已经勘测好的地方埋雷,又立刻熟练地跑开。
等了大概不到一分钟,五个炸点只炸响了三个,依米奇的同事们拉住他说:“别着急,也许因为冻住了反应慢,再等等。”
“这个天气,就连人都快冻僵了,更何况是机械设备,再等等。”
他们一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所有人都明白了,那两个炸点还是没有炸响。“瞎眼炮”必须排除掉。
又等了一会儿,大家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有位战士抄起工具说,他去看看。父亲大声说:“站住!我点的炮,我知道位置。我去!”
依米奇冲上前去,他脑海里只有一句话:要快,要快,要快!
原本是已经熟练到不能再熟练的技术,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他排雷,才只是刚刚走到炸点附近的位置,哑炮又响了……
山体倾倒下来的山石,把父亲依米奇完全埋掉了。
雪落无声,长风呜咽,世界再次暗了下来,对于依米奇是,对于眼睁睁看着他被埋掉的同事们是,对于库丽扎的母亲和未出生的小小库丽扎更是。
当时,为了绝对保密,修建水电站时牺牲的战士和民工,包括库丽扎的父亲在内,下葬时墓碑上不写名字,只写一个代号,也没有落款。
埋藏英雄的墓地,也无人知道。
依米奇埋在了那个付出生命的地方。那片墓碑中,有老红军、老八路还有一些是来自青海、江苏、湖北等全国各地的知青。
可可托海水电站,在当年国家非常困难时候为祖国的两弹一星工程铸就了钢筋铁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那些牺牲在工地一线的英雄们的故事,将永远被人民铭记。
父亲去世后几个月,库丽扎才出生。
库丽扎从来没有见过父亲。
考进塔里木大学,库丽扎选择的是水利和机电专业。
女孩子学这个专业的人不多。
毕业时,库丽扎选择了去可可托海水电站。她带着母亲一起,来到了她从小就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是父亲所在的地方。每天走到水电站的路上,库丽扎就觉得父亲就在身边。
“我一辈子都不要离开这里。”已经年近六旬的库丽扎说道。
可可托海水电站的生活区位于山间的一块小盆地之中。一长排整齐的红色砖石的房屋,在群山之中格外醒目。小区不大,一应设施倒是齐全,但毕竟远离城市。没有热闹,没有喧嚣,显得空寂而冷清。
这里唯有周边群山耸峙,碧空如洗,静默无声。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四
库丽扎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她回到了母亲的老家青海。她在那里长大、上学,生活。但是生活当中没有爸爸。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妈妈去,老师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我一开始太小,不吱声。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爸爸很伟大。我就留着眼泪和老师说,和同学说,和朋友说,甚至是上了大学以后和男朋友说,他们都在安慰我,甚至可怜我。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出来了,他们其实并不明白我心里的苦。活在和平、幸福的地方的他们,无法感同身受。”
库丽扎在大学时候谈过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山东男孩,个子高高的,说话很轻很轻,在同专业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成绩是可以比肩的。男孩子对她很好,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他们俩一起进步、学习,到了大三大四,他们开始讨论未来,男孩子说他们可以留在青海,也可以去山东,这两个地方都很适合发展,也适合定居。
库丽扎不同意,她说:“我们讨论过我想要回到新疆这件事。”
男孩子愣了愣,他没想到库丽扎会这么坚持。
“或者,我陪你一起回去看看,为你爸爸扫个墓,新疆那个地方太远了,离经济中心远,离我家也远……”
纠缠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和平分手了。
其实库丽扎的母亲也对孩子要回到新疆的事情表示反对,提到边疆,母亲总是难过的,更不愿意孩子去吃父亲吃过的苦,哪怕一点点她都舍不得。
即使是最亲近的母亲和男友的挽留,也没有改变库丽扎的想法。她走得很坚决,不听母亲的劝,和相恋几年的男朋友分手,还是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并且在新疆一待就是几十年。后来,她工作稳定后接母亲过来,就再没有离开过那儿。
我在后来执笔时候,对于库丽扎的经历也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再次打通了她的电话。这通长途电话中,我们聊到了许多关于她为什么因为未曾谋面的父亲,而依然决定再次回到新疆。
“我小时候没有爸爸,谁都看我是另类,没有人彻底理解这份感受。而挤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所有情绪,只有在回到新疆以后才能完整释放。只有这里的人才能深刻感触,明白我的爸爸走得多么快,明白我心里因为父女这辈子无缘见一面这件事有多痛。同样也明白,新疆有今天,有多难多难。”因此她后来下决心回到新疆,因为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坦然面对自己没有爸爸、爸爸是为了新疆建设牺牲了这件事。
“新疆的风里有爸爸的呼吸。我在嘴边轻轻叫一声,他好像能听见,好像在回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