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危机·拓展故乡·拷问灵魂——莫言研究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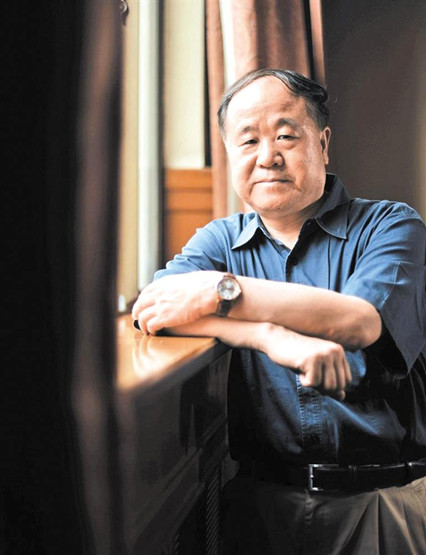
一、 曲折成长与认同危机
自鲁迅发端的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从乡村中走出来的有成就的作家很多。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从12岁到21岁,在乡村成长的曲折经历与认同危机。1967年,他读完小学五年级,就意外地失去了升入中学读书的权利,被排斥在校园和同龄人的世界之外。他成为生产队年龄最小的劳动者,过早地进入成人社会,年幼体弱,难以担当劳动的艰辛。在精神状态上,稚气未脱,混沌未开,也无法理解和融入成人社会。出身于上中农家庭,令莫言在乡村生活中遭受不公待遇,《枯河》中的少年小虎在玩耍中意外坠树砸伤支书家的小女儿,本来就被上中农成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和哥哥,对少不更事的小虎轮番殴打,害怕由此得罪村支书,以后的日子更加难过,就是现实的一个侧影。为此,少年莫言在劳动和生活中,不能不调动全部的感官和思维去感觉它承受它适应它,使出浑身解数。1960年代初的饥饿,在《铁孩儿》中得到精彩的描写,那些饥饿的孩子,肚皮薄如纸,可以直接看到他们青色的肠子在蠕动。莫言也说过,他给生产队放牛放羊,一个人躺在草地上,在孤独中感受大自然,全身心融化在田野里,还学会漫无边际的想象。这样,他的成长期的艰难和孤独就远远地超过许多同龄人,不同于那些中学毕业后回乡劳动几年的回乡青年和带着深刻的城市生活记忆插队到乡村的知识青年。与还乡人不同,莫言的整整20年乡土社会的在地性,他对于乡村生活的原始感受,是非常突出和全面的,而且是从孩子的角度进入,充满了内心的孤独,充满了丰盈嘈杂的感性,充满了喧嚣和不确定性。
西方著名儿童教育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把一个人的成长划分为八个不同的阶段,对其不同的心理特征予以分别的阐释。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莫言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很大的帮助。
埃里克森指出,一个人的青春前期(12~18岁),对于他的成长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容易产生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是进入成年期的短期准备阶段。青少年阶段可能是人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他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我是谁?”一个人从婴儿期到少年时期,他用了10余年的力量去确认自己的儿童身份,建立自我信任,但是,随着他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变化,他需要告别童年而进入青年时期,需要重新确认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要从受到家人和社会保护的孩子转变为独立的社会性的个体,在自我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建立新的信任和调谐,为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埃里克森探讨了同一性和早期经验的关系:正在生长和发展的青年人,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内部生理发育的革命,面临着摆在他们前头的成年人的使命,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自己的感觉相比较,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各种角色及早期培养的技能和当今职业的标准相联系这个问题……。所以,自我同一性的感觉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一个人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内在的恒常性和同一感 (心理上的自我),一旦这种同一性的自我感觉与一个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配时,那么,就表明一个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如果年轻人不以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那他们就会以角色混乱来离开这个阶段。角色混乱是以不能选择生活角色为特征的,这样就无限制地延长了心理的合法延续期。如果儿童感到环境试图对允许他把下一阶段整合在他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彻底地剥夺,那么,儿童就会以野兽突然被迫捍卫其生命般地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进行抵抗。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如果没有同一性的意识就没有生存的感觉。
顺着埃里克森的思路,我们可以继续向前延伸。如果莫言能够和同龄人一道,一起升入中学读书,然后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回到乡村生活,就会有一个“同龄人共同体”,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同病相怜,相濡与沫,有利于青春期过渡的顺利完成。莫言呢,小小年纪,被学校和小伙伴抛弃,又很难融入劳动世界与成人社会,他就需要独自面对这样的认同难题,产生同一性混乱和认同危机,生命的和心理的复杂体验远远胜过同龄人。这才是他感受到生命之孤独的深层蕴含。最典型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小小年纪来到公社的水利工地,和成年人一道劳动和生活,无论是菊子姑娘对他的关爱,还是小铁匠对他的戏弄,他都没有能力去表达感恩或者加以拒绝,对铁匠炉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也只能是在场的旁观者,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令人感到无奈的是,在成人眼中完全可以用常识解释清楚的一只被炉火映照得美轮美奂的红萝卜,小黑孩竟然会认为这就是萝卜本身自带的神奇光芒,于是才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小黑孩到萝卜地里去找这只红萝卜,把满地的萝卜都拔了出来。然后被作为破坏生产队菜地的作案者抓了起来遭受残酷惩罚!还有,在小说《牛》中,那个胡言乱语强作解人的放牛少年,一心想要证明他可以参与成人社会的生活,却一再遭到成年人的排斥和打压;成人社会对这样的劣行当然难逃其咎,放牛少年“我”的懵懂无知,也着实可笑。
在认同危机的更大范围内,就中国大陆和乡村社会生活而言,这一时段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段,风云跌宕、风潮起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体制、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变化频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更加剧了少年莫言的认知难度和认同危机。少年莫言失去了升入中学的机会,这让他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令他刻骨铭心,痛苦万分。这样的成长的痛苦,后来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丰厚资源。功成名就之后的莫言却说,当年他一个人赶着牛羊走过学校墙外,听到同伴们的读书声,顿觉满腹凄凉。他宁愿没有后来的种种成就,而愿意有一个正常的少年时代。诚哉斯言。
二、坚守乡土与拓展乡土
坚守乡土非常不易。很多乡土作家写到后来要么转换写作题材,要么变得重复自我。莫言的写作却花样翻新、源源不绝。他在坚守乡土的同时又拓展乡土,使得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日渐丰富和充实起来。
现实故乡和追忆故乡是诸多乡土文学作家共有的情怀;莫言还有自己的独创性,他的想象力极强,故事充满想象性。他描写的故乡,突破了现实的疆域,通过想象故乡,拓展故乡,让莫言多了一副描写故乡的笔墨,也避免了一味铺叙、平面横推的惯性写作。而情感的复杂交叠则拓展了莫言的故乡风景。
为了更好地说明莫言拓展故乡的方式,让我们对山东作家的两大“重镇”——莫言和张炜,做一个简明的对比:
莫言和张炜都是书写地处胶东半岛的家乡之风貌的著名作家,都是齐文化和蒲松龄的坚定守护者,都对故乡故土一往情深,作品中都融入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并在2011年一起荣获茅盾文学奖。但是两个人描绘乡土的方式各有不同。莫言一方面把发生于异地异乡的故事移到他熟悉的高密东北乡,如《天堂蒜薹之歌》。故事取材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1987年,山东某县的众多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到了收获季节蒜薹却全部滞销、丰收成灾,县政府有关官员却对此不加理睬,对他们当初的号召动员无法做到善始善终。忧心如焚的农民于是自发聚集起来,包围、冲击县政府,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莫言从一张《大众日报》的报道获知此事,激发起他为农民鸣不平争权利的强烈情感,遂放下手头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短短35天即创作出这部作品。莫言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高密东北乡,把自己熟悉的乡亲们写了进去,把自家四叔因为遭遇车祸死亡却没有得到公正赔偿的故事也编织进小说中,甚至还在作品中设置了一个现役军官,在法庭上为被捕的农民做辩护人。可以说这是把莫言自己也写进了作品中,他写这部小说就是要为这些农民进行申辩。一方面,他借用活跃的想象力为高密东北乡文学领地增添了许多现实的乡土所没有的形貌和风俗,不但将现实中阙如的沙漠和山体、异乡异国迎接新年的乡俗划归本乡本土所有,还可以像《会唱歌的墙》那样去虚拟一面在风中发出神奇声响的酒瓶子垒成的墙壁。极而言之,正如莫言在和学者王尧的对话中所说,“我是把淮海战役挪到了高密东北乡来打,这也是我提出的用小说拓展故乡的一次实践。淮海战役当然是发生在苏北的,但我在写的时候,那淮海战役的战场就在我们高密东北乡的荒原上,母亲推着车子,带着孩子,跟随着人群逃亡的那段艰难历程,实际上也是他们人生旅途的一个缩影。”
张炜的创作方式则是田野调查式的。他几次在胶东半岛行走考察,备尝艰辛。如论者所言,“1988年春天,张炜开始准备写作《你在高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胶东半岛,开始长达22年的旅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你在高原·我的田园》与1995年《你在高原·家族》出版时,都有一个副题:《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此后,《你在高原》的单行本都有此副题。2010年,10卷本《你在高原》准备出版时,张炜原定加上“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的副题,但出版社认为不够大气,并最终说服了张炜而删去。但张炜依然在序言中郑重其事地交代这就是一部“地质工作者的手记”。因为为了写作这部作品,张炜进行了一名地质工作者般的漫长行走,而做一名地质工作者,正是张炜童年的一个理想和情结,也是他写作此书的初衷。
从这一点展开去,又会对乡土文学的建构有什么样的启示?
这种超越有限故乡的努力,不但是在故事和人物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拓展中,也拓展了自己的思想界面,建立了高密东北乡——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缩影——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深刻显现这样的递进关系。
莫言这样说:
每个人都有故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故乡显得尤为重要。我21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家乡,21岁到黄县去当兵,在黄县待了4年,黄县离高密也不算远。25年的山东生活足以让一个人形成完整的性格。故乡的生活成为我小说中最主要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另外,我觉得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具有充分的历史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现代中国的风云画卷。在这片土地上,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急骤变化的时代命题和多重现代性的交叠,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巨大转型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涌现出众多极具戏剧性的人物,发生了讲不完的乡村故事。在众多作品的先后承接和交汇中,莫言将现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如《檀香刑》,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红高粱》,从土地改革以来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迁如《生死疲劳》,到计划生育制度的乡村投影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生态的影响如《蛙》,都浓缩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而始自清末民初、终于1990年代、时空跨度最大、人物和事件最为繁杂的《丰乳肥臀》,则是这些作品的经纬交织中最重要的一环。
三、地域、中国、世界:人类灵魂的揭示与拷问
如何将高密东北乡的中国故事接通世界各国的读者心灵,打动人类共同的情感,在30余年的创作中,从自发到自觉,莫言对于拷问灵魂的命题的思考日渐清晰。在切入现实的神髓的同时,牢记文学对人性和人类灵魂的揭示与拷问的终极使命。莫言说过,小说是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展现和拷问人的灵魂是文学的最高追求。因此,在处理历史风云或者展现现实矛盾的时候,莫言都是盯着人物落墨,从有限的历史进入无限的心灵,从具象的世界开掘出形而上的精神。
《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生死传奇,由个人的偶发行为上升为“红高粱精神”,映照出后辈子孙的孱弱无能和“种的退化”。《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为了求证自己的清白,向历史讨回公道,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甘愿忍受地狱里的种种酷刑,拒绝遗忘,拒绝饮用可以忘却前世今生一切烦恼的孟婆汤,游地狱、下油锅,接受六道轮回的荒诞惩罚;这已经足以“泣鬼神而惊天地”。但是莫言的笔触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仇恨与宽恕这一人类感性与理性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间折冲樽俎,迫使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实现自我超越,释除狭隘的一己私仇,从而进入新的精神境界,也正好对应了“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知足,身心自在”的佛家偈语。在至高的境界上,即便是拥有百分之百正义性的西门闹,因为其过于执著和焦虑,也会成为一种“贪欲”“执念”,才会被阎王爷反复诘问其是否将怨恨消除,以决定是否可以让他重返人间。西门闹的苦难格外沉重,但是其拯救之途又是如此奇特,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血刃仇敌,没有得到他念兹在兹的判定他一生清白、没有伤天害理行为的证明,而是最终对最沉重的往事、个人的心结,展现出宽恕和释然。或许这才是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当中那些错综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的超越吧。
在《蛙》和《我们的荆轲》中,莫言的自我反省是非常明晰的。《我们的荆轲》从最初的创意,到“我就是荆轲”的认领,使作品切入了新的深度。文学场也是名利场,久在文坛厮混,不但是看到了许多名利之徒的赤裸裸的表演,也时时会反躬自问写作的目的何在,尤其是在创作成就达到一定的高度,得到来自各方面的热烈肯定,赢得海内外的诸多奖项和荣誉称号之后。这样的自我拷问,转移到荆轲身上,就变成了对荆轲刺秦王的动机的不妥协的严厉追问。赵女作为荆轲内心世界的发掘者和追问者(同时也是荆轲自我拷问的精神投影),对荆轲提出的一个个自我辩护的理由进行严厉的几乎不可抗拒的驳斥,戳穿其自我美化的假象。否定了一个个外在的标签化的目的预设之后,终于接近了问题的核心。虽然说,荆轲最终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此时此刻,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为重要——正因为莫言和他笔下的荆轲都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于是,有心的观众和读者就会顺着莫言和荆轲的思路继续延伸继续追问下去,在这追问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荆轲的位置上,无法回避这样的灵魂之问。
诚如学者刘再复所言:“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了他的故乡,他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看到文革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被教条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发。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莫言的创作,正是基于历史记忆、社会现实与个人经验,又超越形似与单纯写实,作家强大的灵魂活力,实现了艺术对生活的改造和升华,就像一苗炉火,把那个不起眼的小萝卜照耀的美轮美奂,就像一泡骚尿,将普通的高粱酒点化为名世佳酿。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