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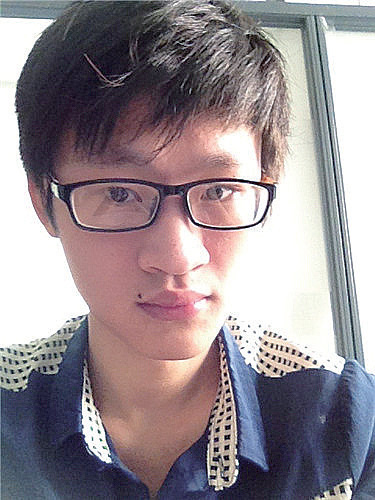
王陌书:1997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我们》《随四季》《现代神话》与短篇小说集《玩乐时间》。在《麻辣》《小说界》《文艺风赏》《作品》等杂志上发表过诗歌与短篇小说。首届掌阅文学大赛短篇小说组二等奖获得者。
周四下午,工作结束,洗去手上的油污后,肖马出现在两条马路相交的地方,为的是联想到史前的巨型蜻蜓。刚刚一架民用直升机掠过地面并根据凹凸的建筑物改变的影子让他想起这点。他直视飞机的时候不得不以手抵住前额防止刺眼,飞机下垂的绳索上系着一个巨大的在火烧云下反光的十字架,若是它摇晃的话,也许会对全城的人进行催眠,就像心理医生手中的一块挂表。这里没有人信教,无论飞机悬挂的是十字架,还是其他标志,都不会引起人们朝飞机的方向致意。面对着一栋八层公寓的肖马自然也不会。
肖马置身于公寓的阴影下,没有影子,他刚刚抵达又即将离去,向前盯着一个方向,三楼阳台上的一个少女。
眼前的公寓让他联想到魔方,每一层楼都可以通过空空荡荡的视野看到一排房间,重新刷漆的墙壁及塑料水管,不难联想到光亮的地板与长霉的天花板多么单调。若可以切开公寓,那么可以看到的就不再是沉默的水泥外壳,而是众多私人生活互相重叠的影像。那样的话,他得像从纷纷而下的落叶中确定一片自己喜欢的落叶那样,从众多的家庭中确定自己喜欢的人物。
阳台都是镂空的,有如古代的屏风让人浮想联翩,当有人走过时其不断闪现的两腿有如拨过琴弦的手指。肖马将双手插进口袋,其中一只手握住从汽车修理厂带出来的螺帽。置身于都市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天空会比以往狭窄,若不小心的话,随时会被社会当作一枚无用的螺帽。
个人过于渺小了啊。在三楼阳台上那个穿连衣裙的少女目视前方,她没有穿鞋,踮起赤脚似乎在展望未来。她面前有几盆盆栽,由于过于活泼的动作差点让一个种有芦荟的小铁盒坠落。肖马几乎要跑过去伸手接住了,他是个相信巧合的年轻人。
这时,远处的篮球场上,一个不被看好的家伙投出了一个完美的三分球,球场上所有的目光集中于比太阳还要醒目的一点上。而在顶空,一只氧气不充足的氢气球刚刚上升,视力2.0的人可以看到上面系着一只正在挣扎的甲虫。那根维系直升机与十字架的绳索此时断裂,那个巨型十字架砸在这栋公寓的屋顶上,仿佛试图树立起一座无名墓碑。他将这些巧合与她联系起来,他想说的是,一切只是偶然。
那巨大的声响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她侧枕于放在护栏上的手背上,仿佛自己正在没有楼梯的高塔上等待什么,又苦恼于自己没有可以垂至地面的长发,她仿佛生活在童话之中。肖马因为她对环境的无动于衷而感动,他仰起面孔对她喊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等下去,直至你的头发长到可以让我攀爬为止。”
她远眺这天边灿烂的火烧云,也许是无暇顾及楼下的陌生男子,也许是反感他脏兮兮的样子,直至肖马悻悻离开她也没有看他。
许多天之后的周二上午,无所事事的肖马再次路过陈旧的公寓,这时正在下雨,尽管没有雨伞他却在那里驻足停留了一会。在雨中,公寓就像古代城堡一样孤立,那是一种形而上的孤立,接近它乃至进入去搭电梯固然可以,但每走近一步感觉上却疏远了一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寓就是一把巨大而固定的雨伞。雨可以斜入阳台上,那些盆栽似乎即将倾倒但又始终没有。对于肖马而言一切都没有改变,因为在三楼的阳台后面,一个似乎刚刚睡醒的少女倚在窄门边,门帘被压在她手下,似乎还要一会儿才能完成从梦到现实的过渡。她木然地欣赏着雨景,姿势比圆规还固定,肖马不禁担心这样下去的话玫瑰会在她身边发芽,毕竟她似乎也是蔷薇科的生物。
似乎她靠近了雨,手伸着露出锁骨的衣领,她的肤色很白,不过让人联想到的不是骨而是雪,在雨天这格外令人感慨。她纤细的手指触碰了那只有芦荟的铁盒,然后伸出屋檐想要掬住一些雨水。她看见了肖马正在看她,先是羞涩地退后然后又担心地上前。对肖马比画手势,大概是问他需不需要雨伞,肖马摇了摇头。
不知为何肖马感到眼前的景象与之前有所出入,不是因为雨的关系。她刚刚睡醒,估计床铺的凹陷还没有恢复,或许她没有意识到睡醒之前与睡眠之后的区别,现在的她只知道要梳理头发。
屋檐下悬挂的风铃正在摇晃,肖马撩下了正在淌水的发梢,完全不顾湿漉漉的自己说:“你应当重新睡下,直到有人吻你才可以醒来。在你的手指上被纺车刺伤的伤口还在吗?你若吮吸它不知道还会不会流血。”
她微笑不语,熟练地比画他看不懂的手势,既像是拒绝什么又像是答应什么。肖马无奈地耸耸肩,像步下舞台一样离开。
半个月后的周六清晨,肖马在公寓下看了看新买的手表,确定在工作开始前有时间停留,他的新工作就是一边看表一边记录当时的气温。那个风铃静止着,站在阳台上背对外面的少女静止着,伫立在马路上的肖马也静止着,这一切就像几个有误差的时钟终于在一个时刻指向同一个方向,下一次是在几天、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后了。
少女的转身比芭蕾舞演员还流畅,她穿着牛仔裤配白色衬衫,背面转向正面的瞬间那飘动的发丝让人觉得稍显仓促。她肯定不擅长奔跑,三楼狭长的走廊上暂时只有她一个人,她的眼神让人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与无可奈何。倘若此处有画板的话,肖马定然会放弃工作对她进行素描,现在他对手中没有握着铅笔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失落。
那些盆栽已经被撤走了,目前上面摆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一只手拿着一个苹果的她应该正准备读它。肖马看着她还没有吃的鲜红色苹果,不禁提醒道:“请不要被色彩诱惑而食用苹果,那是嫉妒者所献上的有毒物,不然的话,得让这个时代过时的透明水晶棺材来保存你的美丽。”
“你是谁?”她首先发觉我的是听觉而非视觉。她耳蜗的形状非常漂亮。她说:“第三次路过这里的行人。”她将苹果放在阳台上,略微探出身躯:“你看远处的东西,一切都显得渺小吧,所以人从大厦顶端俯瞰风景才会有一种成就感。然而我无论走在哪里都不会那样。”未满20岁的肖马说:“不管怎么说,那的确有些遗憾,不过,若是不会感动那也就不会失落。”
“也许。”她忽然起跳,侧坐在阳台上,动作依旧有如芭蕾一样完美,那本书被触碰一下以致于坠落,在空中宛若一只鸽子。她故意将身躯倾向外面:“若是距离死亡仅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仍旧像我这样轻佻,想必死神先生也会恼火的吧。抱歉了,可不可以帮我把书捡上来?麻烦你了。”
肖马已经拾起了那本书说道:“当然,你还是不要这样轻佻吧,太危险了。”他没有问为什么这本小说是盲文小说。
对肖马而言,这是第三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尽管这多多少少都有他刻意为之的必然。每天都得奔波的生活中,他潜意识地在期待一段插曲,可以改变生活的插曲。他腋下夹着那本书步入公寓大堂然后徘徊在花岗岩地板上,他盯着手表精确地犹豫一分钟后选择爬螺旋形的楼梯,而不是搭刚刚降到一楼的电梯。
他不愿置身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所处的孤独空间,每次看到电梯门关上他想到的不是缓缓合上的纸扇而是缓缓合上盖板的棺材。好几次他遇见这种情况时,都有给里面的人献一束告别的鲜花的冲动。对他而言,乘坐电梯每升到一层楼,都能看见一排排空空荡荡的房间,墙壁上留着搬走的家具和拆卸的管道的痕迹,空空的地板和长霉的天花板。那太像电影《闪灵》中小男孩遇见两个小女孩的场景。
他匆匆地踏响几级台阶后又停下,这比按下几个琴键后又停下更令人愕然。困惑与不解袭击了他,就像用高尔夫球棍击中后脑勺一样干脆利落。他流鼻血了,于是仰起面孔直视天窗,可以看见一闪而过的向下的脚踝。在脑海中他没有关于少女的明确印象,三次偶然或必然的相遇,有如他生活之书中插着的三片树叶标本。他没有记住对方的声音笑貌,哪怕一次也没有过。
当鼻孔不再流血后他继续往上走。也许是一个少女对他由陌生到认识乃至熟悉,肖马也希望这样。也许是一个少女对他不屑另一个少女对他没有感觉,还有一个少女对他抱有好感,肖马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况,就像接受萤火虫出现又消失一样。毕竟生活可轻可重。
沿着螺旋的楼梯向上,四周没有窗户,经过天窗过滤的阳光中灰尘飞舞,对于走上走下的人来说楼梯都是让人离开的建筑,没有谁会想到要留下。楼梯是另一种形态的井,四周实际上是密封的,相当单调的空间里搏斗、偶遇、相爱的可能性加大了。在肖马步上楼梯时我正步下楼梯,我喜欢几个人同时踏响台阶的声音。
几层楼之上,一根羽毛自上而下地飘落,也许是谁在模仿伽利略的实验吧,在那一刻,我、肖马及羽毛在同一个高度相逢,刹那之后又各自分离,谁也来不及把握想要把握的事物。从下往上数的第39级台阶上我跟肖马擦肩而过,他继续往上而我继续往下。
肖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我也是,乃至于只是一个视角的你也是。
在三楼的走廊上肖马站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外,目光却不能直接穿过室内的鱼缸穿过透明的门帘,直至阳台上侧坐着的白衬衫少女——她旁边依旧放着那个苹果。因为在二者之间还有两个少女,她们对他的到来没有任何表示,一个正坐在沙发上吃冰淇淋,另一个依靠在墙上沉默着——她的上方是一幅由于脱落了一枚钉子而畸斜着的油画。
他步入房间,突兀地置身于三个女孩之间,他说:“你好,你的书我拿上来了。”阳台上的白衬衫女孩跳下护栏再走入室内,她总是要触摸东西来确定什么,她闪烁着动人或过于天真的眸子说:“可以继续发出声音吗?不然我无法判断你的位置。”
“说实话,之前我无法分辨你们谁是谁,当然现在是容易区别的。也许我认识别人依据的不是眼睛,而是直觉。”他立在原地不动,直至那个女孩从他手中接过那本书,她说:“不,这是因为你关心自己而不是别人,吸引你的不是我,而是我身上与你相似的那一部分。”她短暂地触碰了他一下又马上疏远他,他不得不靠近,因为感觉自己的灵魂被触碰了,他说:“能否自我介绍一下呢。”
她感受到他的气息于是后退,她闭上又睁开眼睛:“我分合眼睑并不能看见两个世界,我生活在黑暗里,因而显得无所顾虑的活泼。我是个盲人,对于我而言你是声音,是气息,是我触碰到的固体,不要期待我回报你黑色调之外的情感。”
“哦。”我向后退去,若是无视那些类似障碍物的摆设,他与她们之间就不会那么曲折?我问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淇淋的女孩:“你看见了什么?”
她以手抚摸自己的耳蜗再摇摇头,暗示自己什么也听不见,她以女生独有的高音说道:“我的耳蜗坏掉啦,或者说我的耳朵在某种意义上被杀死了,就像原本透明的冰块在阳光下彻底透明。”我以食指轻触上唇暗示她小声点,她满不在乎地嘟一下嘴,而我则很不容易地让她明白了我的问题。
“看着电视机,就像看着沉默的鱼缸。”她说。
他不再对她说话,又不甘陷入沉默与徘徊之中,毕竟能待在这里的时间有限。他有意地闯入了这个空间却无意面对眼下的情况,他无法处在三个女生的交集所在扮演一个足够有魅力的角色,相反,他处在被大家忽视的死角徒劳无益地盯着手表。她用手托着下巴说:“我什么也听不见,因此无法对你的誓言、谎言、称赞、自白产生应有的类似乐器的共鸣。抱歉,并不是我无动于衷而是我无能为力,我一直生活在天然的密室里。”
肖马对吃冰淇淋的女孩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让自己离开椅子显得自然,不那么仓促。他一直往后退去,中间还被椅子绊了一下,直至自己也倚靠在墙上——也就是另一个女孩旁边,距离近到了可以耳语的程度。她穿着蓝色连衣裙,从之前开始就没有造成任何动静,和她在墙的背景下站在一起仿佛构成了一幅静态的水彩画。
从任何角度看这间公寓都会得出如下判断——干净、流露出一种冷色调,几个出没在其间的女生使这里的寂静异常动人……只是无法用一种方式对她们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肖马将视线移向女孩时,女孩却将视线移向另一边,肖马看着她的侧面说:“假如,我是一个逃犯你会告发我吗?”
她认真地摇了摇头,非常流利地对他比画手语,肖马大概懂得了意思——不会,我不会对任何人提起。并非出于我对你的好感,而是由于我对一切事情持沉默态度。我就像一块石头。
“这只是一个玩笑。”肖马对她的辫子吹了口气,然后敲了敲墙壁:“起码可以让你不那么像月神的雕像,呼吸比屏气要好。”
也许是比画手势不能完全说明自己的意思吧,她有些慌乱。她不能说话,深刻地懂得没有声音的境遇。她就像一个谜需要别人来猜测,却不能为自己用语言解释些什么。也许这可以吸引众多好奇者,但是置身于迷惑之中的她却无法自信,真的,她憧憬的不是爱情,而是一声折返的自己的回音。她用双手握住肖马的手将其放在自己的左乳房上,他一阵愕然,不是因为那绷得紧紧的、富有弹性的尖状物,而是她平静而稳定的心跳。
那就是她的声音,有着指尖划过竖琴的旋律。
肖马条件反射地拿开手,虽然迟疑了一会儿,但那已经是他反应的最快速度。他匆匆地与所有人保持距离,似乎有类似丝绸的柔软物滑过这个空间,他才能有如骑上回旋木马般周旋于三个少女之间。她们似乎平行地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盲女、哑女、聋女,对肖马而言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矛盾。她们的残疾就如维纳斯的断臂,反而是一种遗憾美,在肖马看来,与其视她们为自己希求的异性不如视她们为艺术品。
他感觉自己正置身于到处是玻璃橱窗的博物馆。他的目光穿过鱼缸穿过门帘直至阳台护栏上的苹果,穿白衬衫的盲女正坐在餐桌边用手指读那本盲文书,他对她说:“现在我就站在你眼前,你看到了关于我的什么了?”
她抬起头时略微挪动了椅子,神情淡然地停止翻页,似乎此情此景本身就是一本书。她说:“你是黑色的,让人觉得冷,寂静。也许我只有在拥抱你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肖马用茶几上的纸写了一行字给吃冰淇淋的女孩:“之前我一直在你身边,你听见了关于我的什么?”而她在纸上写下回答他的话:“你可以让我想象将一只海螺置于耳畔的情景,可你不可以让我想象跟你在一起的情景。我害怕伏在你赤裸的胸膛上,耳朵像听诊器一样抵住那里却听不见心跳的感觉。我只能听见你的沉默。还有,我所写下的文字是无声无息的、静悄悄的。”
站立起来后肖马有点晕眩,应该是之前流鼻血的缘故,他像圆规一样转向穿蓝色连衣裙的女孩,颓然地问道:“虽然这是第二次见面,可你能否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我?”她笑了,仿佛有人正在给她照相,她以食指轻触嘴唇表示无语。她走近肖马吻了他一下,那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同情。
肖马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三个女孩之间他觉得有些眼花缭乱,似乎这个空间本身就是万花筒在交错色彩,而肖马关于她们的记忆碎片也重叠出错误的印象。他来到阳台拿走了那个苹果,同时以俯瞰的视角观察自己两次停留的位置——他知道此刻那里空无一人。再次经过室内时他说出类似告别的话语:“无论晴天雨天,在我眼中你们都不是互相平行的个体。我为你们所倾倒,我想将你们看作一个人,一个起初对我不屑之后接受我的幼稚最终允许我步上楼梯的少女。伫立于此你们的模样在我脑海中发生重叠,也就是一个既能聆听也能欣赏、还会倾诉的姑娘。
“当然也可能完全相反,即一个既不能聆听我的讲述也不能欣赏我创作的绘画,还只能对我保持沉默的姑娘。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可能。前者象征活泼的生命后者象征忧郁的死亡,那么三次路过这座公寓并且将你们视作一个人的我,究竟爱上了生还死?”
穿白衬衫的女孩、穿蓝色连衣裙的女孩、吃冰淇淋的女孩在那一刻同时在乎他,就像钟表上的时针、分针、秒针重叠在12点。她们是围绕沉默旋转的。肖马手中拿着苹果一步步退出房间:“打扰了,再见。”
他一言不发地步下楼梯时将拿苹果的手伸出护栏,然后非常自然地放开,苹果径直坠落,直至被正在步上楼梯的我伸手接住。肖马已经迟到了,可他并不在乎这个,在实际上密封的楼梯上沿台阶而下像是在弹钢琴,而沿台阶而上像是在玩多米诺骨牌。在整个台阶上我与肖马擦肩而过,我将那在神话中象征欲望的苹果交还给他。我们面面相觑却没有交谈,毕竟两个未满20岁的男人之间无话可说。我继续往上而他继续往下,彼此对对方而言只是背影。

王陌书的小说拥有极具辨识度的遣词造句方式,此外,他所选取的意象是如此夺目。重叠是一道谜语,光影、人格、思维,哲学意义浓厚。我丧失了发问的权力,仅仅辨析,就要耗费巨额的精力。小说美学从来是不拘一格的,枯索、敦实、新奇抑或怪异,能与自身美学原则发生共鸣的,就是好小说。王陌书的出现,绝对是“90后”小说创作者中的一道亮眼光线。
点评
他提供一种观看式的镜筒,一端是善于联想的思维,一端是事与物的材料。阅读他的读者,不是观看新的材料,而是观看某种个人化的新的联想结晶。他反许多他目力所及与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手段,隐喻也好,解构童话也好,随性使用,却不愿娴熟演练,因为新鲜和美是联想结晶的生命,而力量不是。这种写作仍符合好词好句的模式,有时会逃不脱冗余、饶舌、巴洛克式的琳琅。所以,我读陌书的小说,很像看蜜蜂又为蜂巢泌出一个六边形。我似乎在等待蜜蜂认知六边形和蜂巢的那一天,但抽象和凝结早就是一切源起时的事,不见得好与新鲜。
——魏 傩
王陌书在不长的篇幅中结构出一个层次丰富的世界,可以看出他在试图寻找新的道路,他书写一种境况,一种“幻想的实现”(拉康)。主人公肖马是观察者“我”的镜像:“我”在对肖马进行观察、想象和幻想的过程中建构着自己。小说的许多细节值得玩味,少女形象塑造得十分轻巧,像透明气团在微风中飘浮,更有趣的是由一个少女到三个少女,或者可以说一个少女分裂成三个迥然的人格分身,和她们进行有关爱与美以及生死的讨论,也是肖马短时间内认识自己的过程。苹果这个意象的增入,让小说有了想象空间:诱惑亚当夏娃的苹果?白雪公主吞下的毒苹果?这些都显得旖旎美妙。然而,小说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被有些强硬地植入人物对话中,痕迹过于明显,留白很多,使得小说虚实稍有失衡。
——宋阿曼


